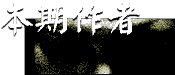不分行黑陶
下文中提问者为橄榄树编辑严韵,答问者为黑陶。
1.第一次读你的东西好像是〈私人金陵〉,当时很深刻地留下了一个“都市性”的印象--即使你后来发表在「现场」上的〈春天汹涌〉、〈绿昼〉等都是直接描写乡土的,我想到你的作品时仍然总感觉是充满城市意象的。所以后来听你说出生在“山脉、丘陵、平原和湖水杂置,景色清美又物产丰饶”的“烟火小镇”、双亲是劳作繁重的“中国最底层的百姓”,不知怎么地感到颇为意外……。你自己觉得城市以及乡村/乡土的概念是如何影响你(和你的书写)?
答:就我而言,16岁是个分界。16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乡村,即那个被夹挤在江、浙、皖三省之间,属农业和手工艺(陶业)性质的烟火小镇;16岁以后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工作、成家、生女,居留于中国东部沪宁线上的中等商业城市。但离开家乡并不意味着与家乡割绝联系,我仍频繁地从目前的谋生地回到太湖边上的老家,去探望那里的亲人。个人的这种状况,使我有机会能够较为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百姓两种典型的生活形式--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真正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而这种感受,可以肯定地讲,是一般的旅游者(城市人到乡村旅游或乡村人到城市旅游)所无法获得的。进入城市已有十多个年头,但似乎始终无法取得认同,在城市巨大的楼厦阴影和迷宫幻彩般的“超市”间走停,我更多地感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或曰“窥视者”,我并不是属于其中的一员。承载人类的大地,本质上是乡村/乡土性质,而一座座表面斑斓甜蜜的城市,实际是伤疤,大地上累累散布的疼痛伤疤。--这种理解甚至不是思索所致,几乎直接来自个人的生理反应,而且,这种生理反应那么深地“渗”进了我的“书写”:文字涉及乡村时,整个人清爽、愉悦、满足;而笔(手触键盘)一进入城市,内心就焦灼、紧张、郁闷、倾斜……
2.再放到一个比较不抽象、比较清楚地域性的角度来说,文学上你所崇敬、所慕想承继的南方传统,这个南方对你而言是个什么样的南方?
答:博尔赫斯的一句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布诺斯艾利斯并不代表它的名字所隐含的地理习惯;它是我的家园,是熟悉的邻人,还有与他们在一起的,我对于爱、痛苦和忧愁的体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年版序)同样,在此我要说明,“南方”只是我的一个私人概念,它与我的生存、生命、血液、情感和思想紧密联系,与严格的地理学命名则无关。如果一定要指出我的私人“南方”的地域范围,那么可以这样说,我所出生的那个充满烧窑火焰和茂盛农作物的“烟火小镇”是它的核心,扩展开去,它的疆域包括广阔、灵美的吴越楚诸地。这个“南方”范围,其实很大一部份就是“江南”,但是,我是如此厌恶“江南”这个指称。“江南”一词,也是一个原本美丽而遭受蹂躏的典型,现在它所充斥的,是流行的媚俗、纤巧、轻笑和强烈的“杏花春雨”式的风尘女性色彩……,真实的地域精神,已被完全遮盖。所以,我不言“江南”而称“南方”。我追寻、说出并倾心热爱的,是这片土地上他们不知但确实存在的另一种美,南方的异美--激烈、灵异、博邃、深情。如下的具体元素构成我的“南方”王国:充沛雪白的河流、大海、灵幻茁壮的植物、吹可断发的青铜剑器、烫血、星辰和大地的神话、强大而高蹈的灵魂、无穷无尽的想象力、火焰和泥土的手工艺、夜晚旺盛生长的汉字诗篇……。在这个王国里,我拥有我私认的连绵文学师长:屈原、庄子(尽管他出生于秦岭淮河这条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北,但我愿意奉他为我的南方文学的前辈)、李白、苏东坡、李贽、徐渭、黄仲则、龚自珍、鲁迅、毛泽东、沈从文、废名……,--从他们身上,我索要并正在获得我个人所需要的启示、灵感和朝前走的方向。
3.你提到过去的作品多半是诗歌,但如今觉得(散文的)“不分行文字”更能让你的表达淋漓奔畅;你也说到散文是一个“被涂脏”的形式,可以感觉你对此一文体有着一些反省和--我想可以说是--抱负。对于你目前“在写作方式和精神内涵上,仍然仰仗诗歌的滋养和支持”的不分行文字,是否多谈谈?
答:我目前的不分行文字的写作--按内心的奢想--实际是一种寻找,我想通过个人的这种写作,最终寻找到我的散文,一种自由、尊严、饱满的真正散文。貌似繁荣的当代汉语散文实质虚弱不堪,饰有闪耀油彩的伪文、劣作、赝品触目皆是……
4.拼贴式的文字似乎是你作品中一个常见/重要的手法,我想这跟你所追求的“四个度”--精度、速度、密度、信度--亦有不少关联。也谈谈这一点(或说两点)吧!
答:拼贴,即有选择地将若干事件/图景组合在一起,这其实是最为常见、常用的一种写作手法。我只不过是能大胆省略过渡(以加快文章“速度”),让拼贴效果相对强烈地显露出来。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想在有限的文章空间内,包容尽可能多的“资讯”,也就是增加文章的“密度”。另一方面,这种相对客观的事件/图景的有机并置,也往往使整篇作品能够超越作者一己的狭隘,进而表现出更为广泛的意义,给不同读者以不同的玩味空间。我很喜欢马克·吕布拍的照片,无论是他的巴黎题材还是中国题材,那些凝定了的冷静客观画面(实则是经由主观精心选择),真可谓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它们只是呈示,尽量客观地呈示,而意义则由观者自思。呈示而不去评说,特别是在涉及都市题材时,我经常视之为一条原则。在〈倾斜并且尖锐的阴影〉这篇文章中,有一节我就用文字复制、拼贴了一条我上下班都要经过的僻街--健康路。除了录下整条街鳞次栉比的店名、若干广告文字(间或有对某些门面的简略描写)外,再无其它内容。我觉得,将这条街尽量客观地呈示出来已经足够,至于如此呈示的“意义”,我想不去饶舌是最为合适、明智的选择。
5.又,你在谈“精度”的时候提到“可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叙写,眼是图景,鼻是气息,舌是味道,耳是声音,手是触觉,脑是幻象”。然而比方说以你惯常密度如此之大的笔调,那些几如 Van Gogh 画作中浓厚涂叠的油彩一般被描写的大量感官经验有时反而会倾向只剩下(只被感觉到)“文字”这个面向(dimension),而非可以强烈地勾动甚至直捣感官。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我现在只想听从内心的驱使和召唤:这样写我感到舒服、满意。当然,理智地考虑,我也会认为我现在的这种“笔调”也许只是暂时性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许我最终也会“归于平淡”。但是,没办法,现在的我热爱“绚烂”,热爱莽撞的冲击力,热爱“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式的语言运动。尽管我觉得自己的文章既不晦涩,也不玄虚,它们都是我生存、感受的真实表现,但身边常有朋友说我的东西难读,“不是朋友就不会读我的东西”,确乎,这些东西在外面也少有“市场”(说到这方面,我对《橄榄树》心存一份感激)。然而,我还是想顽固坚持。美国作家梅勒曾经的自信在暗中给我某种坚持的力量:“任何为自己闯一条漫长的创作道路的优秀作家,都必须具备一种品格,在不被接受时比较能顶得住,这才能产生艺术。”乡贤徐悲鸿先生也教导我:在艺术上,重要的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6.连着在「现场」上看到你的读书笔记,那么谈谈你的阅读吧--不管是严肃的、作为文学理念与创作养分的阅读,还是轻松的、作为生活经验及心智享受的阅读。
答:我越来越感觉到阅读对我来说的重要性。生活和阅读,几乎可视为是一个人创作的两大源头。阅读可以帮我找到朋友(尽管也许相隔百年千年、万水千山),可以使我免做井底之蛙,可以让我拥有宽广背景,可以帮我建立坐标,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我目前较多阅读的是:1.中国古代文(哲)学(偏重于读“说了什么”);2.外国文学、文论(偏重于读“怎么说”);3.有关民间及地方性资料的读物。平等交流、能入能出--这是我具体阅读时的态度。
7.在我们日前为此访谈预作暖身的电邮往返中,你简短的自我介绍包括了一句“有一女儿(刚满四个月)”令我忍不住特别注意--比方说我们一般介绍自己时大约不会提到“有身高一七二的情人一名”或“有两只一岁半多的猫”之类的(虽然后者我搞不好会说,哈哈);在〈甜蜜屈服〉里也有相当篇幅关于你妻子生产过程以及女儿出生后某些(相关、不相关)情节的描述。A.女儿的到来在你的人生里是个具有什么样意涵的事件?B.如果要你对二十年后的她说些话,你会说什么?
答:女儿曹悦童的到来是我人生的重要事件。我没有考虑过抽象的意义,她直接带给我的,首先是好多全新的体验,如无端的紧张、发自内心的新鲜喜悦、牵挂、责任感、自言自语编童话的能力的突然出现(对着她)等等;其次,就是在家时的清静时间消失大半,她哇哇大哭时我再也不可能安坐,要逗她,给她换尿布,每天抱她洗澡(她特别喜欢)……20年后,我还是会这样对她说:健康、快乐、自信、宽容。
(2000.5)■〔寄自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