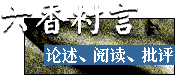·朱也旷·
我为什么认为 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重要
本该无声无息地走过1998年的中 国文坛倏忽变得热闹起来,这回不是由于 “万家诉讼”,而是由于南京作家朱文的 固执的提问。提问是通过向一些青年作家 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的。朱文给问卷取了 一个革命性的名称,《断裂:一份问卷》 ,问题共有十三个,除了最后一个是开玩 笑外,其余的十二个均涉及形成当今文学 秩序的方方面面。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针对 海德格尔、罗兰·巴特、福科等国外思想 家的:“你认为这些思想权威或理论权威 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我对此的回答是 “对写作影响不大”,但在后面又接了一 句“我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有必要 ,假如他也包括在开列的名单中”。后来 在一次聚会上,有个朋友突然问我为什么 这样认为,当时我列举了两三条理由,夜 里想想,又觉得不止这几条。现整理如下 ,供对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回答感兴趣的 读者参考。1.想跟朱文开个玩笑。不知为什么,在 越严肃的场合,我开玩笑的冲动也越强烈 。
2.排除可能的误解。朱文在问题中开列 了一串当今有影响的外国学派与思想家的 名单,但我并不认为他拒绝任何外来影响 。尽管他本人声称不怎么读书,但据一位 了解他的朋友说,这家伙有一屋子书,我 想,这一屋子书肯定不全是“线装书”, 我也不认为一个买了那么多翻译书籍的人 会完全不受它们影响。所以,我认为必须 在肯定性的答案中包括至少一个外国名字 。
3.显示自己懂点儿物理学,其实是一知 半解,顶多也是七窍通了六窍。不过既然 不懂装懂、自我吹嘘的事情在文坛大有先 例可寻,我也不必对自己过于严苛。
4.尽管对牛顿晚年转向神学研究一事, 爱因斯坦认为这是这位世界伟人的一个缺 点,但在许多场合下,爱因斯坦都提到了 “宗教感情”一词。不仅是一般性地提一 提,有时竟是长篇大论。这个词与上帝和 教堂没有直接的关系,在给其青年时代的 好友索洛文的信中,他写道,他之所以用 这个词,是因为没有找到更好的词。这位 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最深邃的理性和最灿 烂的美”的科学家却认为:“宗教感情是 科学研究最强烈、最高尚的动机。”他还 说:“在这种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 会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它是坚守 于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发源地上的基 本感情”。
对于重视眼前成功的中国作家,我认 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不能肯定当代作 家中是否有这种具有“宗教感情”的人, 但我知道古代有这样的人,譬如曹雪芹。
5.爱因斯坦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 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
无独有偶,据古斯塔夫·雅努施记载 ,卡夫卡也曾讲过类似的话。当时,雅努 施与卡夫卡正在参观一座方济各教堂-- 雪中圣玛利亚教堂。雅努施讲了这个名称 的出处,卡夫卡说,他原先只知道这个教 堂在15世纪是激进的胡斯派的活动中心 ,由此引发了一段反对奇迹与暴力的议论 。雅努施问,那么怎样做才正确?这才是 对的,卡夫卡不假思索地说,祈祷。他一 边说,一边指了指跪在小祭坛前的一位老 年妇女,然后拉着雅努施的胳膊出了教堂 ,来到前院。这时卡夫卡又说,祈祷,艺 术,科学研究,是从同一火源升起的三股 不同的火焰。
6.由于惧怕纳粹德国造出原子弹来,一 些科学家建议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让 美国抢先制造原子弹。但早在1940年 9月,爱因斯坦就认为,这是他“一生中 最令人痛心的回忆”。到了1945年, 他更担心美国政府会用原子弹去轰炸别的 国家。广岛、长崎悲剧发生后,爱因斯坦 痛苦地承认:“是的,我揿了按钮。”
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库兹涅佐夫认为 ,原子弹事件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爱因斯 坦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事,他对世界上存 在的一切罪恶都具有一种个人责任感。对 于写作越来越个人化的中国作家,“爱因 斯坦的痛苦”也许不无启示。不过需要声 明的是,在此我并不想借机宣传什么“文 以载道”的古训。
7.我之所以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 重要,是因为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当我在街头散步时,随便经过一个书摊 ,都可以见到大量的关于算命、风水、气 功、占星术、预测大师及某个法国大预言 家的书籍;我之所以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 文学很重要,是因为目前成为畅销书作家 的是柯云路,而不是阿西莫夫;我之所以 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重要,是因为 我曾看到某气功师(事后)预言火箭落地 的报导上了一家读者很爱看的报纸,且堂 而皇之地登在显著的位置上;我之所以认 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重要,是因为我 亲耳听到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话出自某些 拥有高级职称(副教授以上)的人的口中 ;我之所以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重 要,是因为有那么多先前被称为“灵魂工 程师”的人对理性与科学持不屑甚至蔑视 的态度,他们把凝聚着千百年来人类智慧 与汗水的东西看得过于简单,把其中的毛 病又看得过于严重。中国的理性传统从来 都是薄弱的,一贯独善其身的赛先生一旦 到了我们的熔炉里,便很容易与两种土产 结合起来:一种是权力(政治化的科学) ,另一种是迷信(带妖气的科学)。海德 格尔等人的上半身是不易移栽成活的,容 易移栽成活并繁荣昌盛的是他们的下半身 及其帮厨--蒙昧主义。
8.从二十年代起,爱因斯坦与玻尔领导 的哥本哈根学派就量子力学问题展开了激 烈的论战。在第五次索尔维会议上,爱因 斯坦提出一个理论实验,“刁难”之甚, 令玻尔和他的助手们通宵无法成眠。当他 无法挑出量子力学本身的毛病时,便转而 攻击其哲学背景。“海森堡-玻尔的绥靖 哲学(或宗教?)给信徒提供了安眠的软 枕,”他在给哥本哈根学派的成员薛定谔 的信中如是说。然而爱因斯坦与玻尔在私 下里却保持着至诚的友谊。玻尔后来曾这 样评论:
他为量子力学做了多少事啊!在物理 学向前迈出看似必然的每一步中,他都找 出了矛盾,而这些矛盾恰恰成了物理学前 进的动力。在每一个新的阶段,爱因斯坦 都向科学发出了号召,没有这些号召,量 力物理学的发展势必久久延迟下去。
我在一本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上 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存在“两个文坛 ”,一个公开的文坛,一个私下的文坛; 在公开的文坛,文章都是四平八稳式的, 类似于温开水;在私下的文坛(多半是在 友朋间,饭桌旁),时而倒能听到一些真 知灼见。到了九十年代,结果又怎样呢? 在私下的文坛有没有真知灼见,我不知道 ,但在公开的文坛,庸俗吹捧、云缭雾绕 、比温开水还糟糕的文章是随处可见的。 于是便有了争论或论战,这当然是好事, 总比波澜灭绝的一潭死水强一些,但令人 遗憾的是,不少争论和论战除了造成增熵 与增仇的后果外,没有其他功效,更构不 成什么前进的动力。
9.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凯泽尔为其 写了一本传记,在序言中,爱因斯坦坦率 地指出了被贤婿所遮蔽的部分:“被作者 忽视的,也许是我性格中的非理性的、自 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乎疯狂的那些方面 。”
10.1955年3月15日,爱因斯坦 的终生挚友贝索病逝于日内瓦。3月21 日,爱因斯坦在给贝索亲属的信中,写下 了如下一段话:
现在,他又比我先行一步,离开了这 个奇怪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对 于我们笃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 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尽管这种幻觉有时还很顽固。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美、最深刻、最 感人的悼词之一,它是用两种金属融合成 的合金,一种金属是最幽邃的智性,一种 金属是最深厚的感情。我之所以认为爱因 斯坦对中国文学很重要,是因为在我们的 文学中,这样的合金太少见了,或者说是 几乎没有,所谓的大散文通常也不过是小 智小慧与小家碧玉两者的合金。
它还使我联想起孔子临终前与子贡的 那场凄怆的见面,尽管两者之间有着昭然 的差异。司马迁笔下的那一幕场景深深地 打动了我,使我对其真实性彻底丧失了怀 疑,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对耶酥在客西 马尼花园的祈祷不予置疑一样。
兴许,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为自 己写悼词。4月18日,爱因斯坦病逝于 普林斯顿。
一年前,爱因斯坦曾与贝索在信中讨 论过“时间箭头”的问题。爱因斯坦指出 ,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中均不存在所谓的 时间箭头(在牛顿的经典力学中当然也不 存在),亦即基本的物理方程式均不提供 过去和未来的区别。这段悼词也许源于他 们之间的这次讨论。
后来,我又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时 间简史》,另一本是《时间之箭》。我似 乎又多了一些关于时间的知识。
有一阵子,这段话不那么使我感动了 ,我甚至以为那不过是一位大物理学家的 机智与幽默罢了。但不久我便发现这是一 种假象。我还发现,我所拥有的关于时间 的物理知识是多余的,顶多也不过是一架 维特根斯坦的梯子:一旦爬上屋顶,就必 须把它抽掉。
这太奇怪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这 个奇怪的世界。
11.有趣的是,当我不无荒唐地鼓吹“ 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学很重要”时,却又在 一本参考书的末尾发现了这样一句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我的东西比任何一位 思想家都要多。”这句话竟也出自爱因斯 坦之口。
12.爱因斯坦的品德和热忱,哪怕只要 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作家、中国的知 识分子中,我们的文学就会有一个比较光 明的未来。
13.最后,对于本文可能导致的误解, 我们可以用一位美国女诗人的话来消毒: 在科学出没的地方,文学就会隐形匿迹。 这位女诗人就是被人称为艾默斯特修女的 狄金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