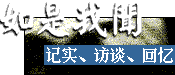沙門:請問《黑白條紋襯衫》和《李小多分果果》〔見《橄欖樹》一九九九年八月期--編者注〕你更喜歡哪篇?或者說,自認為哪篇寫得更好?
巴喬:我對《李小多分果果》更滿意些。
沙門:《黑白》中你用了層層剝筍式的逆推結構來揭開懸念,從手法上來講很先進,但內容卻異常簡單,你怎樣看待形式和內容?你認為僅僅靠高妙的敘述手段就能構成一篇好的小說嗎?
巴喬:《黑白》的結構顯然是有意為之的,其實也說不上新鮮。剛寫完還算興奮,可突然地想起:張弛的《不膩齋》、《與范哥犯葛》(記不太清了,好像是這兩篇)似乎是類似結構。沮喪是可想而知的,是否潛意識受了他的影響也未可知。
我們總是遇到這樣的情況,提起筆,冒出的卻是別人的東西,而尚不自知呢。作為我最初的想法,“逆推”是一個方面,各章節之間的“勾連”也是我的經營。
還有,嘗試著用一種“簡潔”的敘述、“少年血”等等都是我動筆前的想法,不知現在做得怎樣。也許正因為考慮得太多,以及“逆推”的必然後果,《黑白》一文預設的意味似乎很濃,這也正是我對它不太滿意的原因。其實我倒不覺得《黑白》的內容簡單,事件可能小了點,惟其“小”,少年時對暴力莫名的崇拜便更有了探究的必要。也許是功力有限,文章沒有充盈起來,讓人看出“薄”來,但這卻絕對不是字數的原因(兩千字)。至於形式與內容,太多人說過了,好比穿鞋,大兩碼固然不跟腳,削足適靴更要不得,吃排檔時趿拖鞋,結婚時我是定要西裝革履的。敘述於小說來講當然十分重要,其實小說也無非兩點:“講個什麼故事”、“怎麼講”。單田芳的評書人人愛聽,倘若我登台開口,不嚇死嚇跑十之八九那才怪呢。另外,你要讓單田芳去講“星球大戰”,估計也能嚇跑個五六成。
沙門:《李小多》中你設計了一個具有迷惑性的角色混亂,讓人弄不清“我”到底是成人還是幼童。以我的理解你是用這種方法來獲得一種新的性感,如同人們做愛時變換交合體位一樣,你說是這樣嗎?或者還有什麼更深的用意?
巴喬:《李小多》中的“我”應是個成人,但你所說的未必不是一種解讀的方法。
其實這篇小說的產生很偶然,那時我還在電視台幹活,有一天想做一個專題:“世紀末的童謠”,收集一些古怪好玩的兒歌,串連起來,不著一詞。“李小多”便是一盒幼兒歌帶其中一首。這個節目後來流產了,這篇小說倒寫成了。是“李小多”給我找到了視角,敘述的基調也便在“分果果”中確定了。開頭我制造了一些敘事的遮蔽,以後則注重於情緒的表達。有兩處遺憾的地方:一是寫到“老軍醫”時我因事外出一周,回來後先前的感覺怎麼也找不到了,因此草草收場。
第二點是別人指出的,“我”的形象似乎是“半痴不癲”的,但究竟是個透心亮的無業青年,作為敘事的迷霧可以籠罩全文,但具體場景處理應兼顧事理。如與幼兒園園長的對話,語氣可以是童稚痴呆的,但問話本身應合乎常理。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沙門:你受哪位作家影響最大?
巴喬:影響過我的作家實在太多了。
我最初寫小說的動機十分簡單,因為蘇童。蘇童與我是校友,小學校友。在他到北師讀書後的第三年,我成了一名小學一年級學生。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我看到了他那些“香椿樹街”小說。我幾乎沒有考慮就喜歡上了它們,因為它們與我實在是太熟悉了。那條香椿樹街我每天都要經過(我家便在香椿樹街橫向的另一條街上),作為童年記憶和當時生活的絕大部分,我為能從《城北地帶》裡找出每個能與現實對應的地方而感到興奮。而那篇蘇童自稱對他影響深遠的《桑園留念》裡的故事發生地──“桑園裡”,至今還住著我一位小學同班同學。
我因此發現了小說是一個多奇妙的東西啊,而寫小說又是件多麼有趣的事啊。
當然,我正式寫小說始於兩年前,而似乎知道了一點小說是怎麼回事則在去年冬天。或許,將來這個時間還會修正,如果我繼續寫下去的話。但至少,閱讀的興趣和寫作的最直接動因卻是蘇童給我的。去年夏天,我第一次見到蘇童。
那天正好下雨,我站在江蘇電視台的大門口,蘇童剃著板刷,好象是和王幹一塊到的,我覺得,他比我想象中的可要胖多了。
還有,范小青於我有類似的影響,我稱她為“范老師”。而汪曾祺和廢名使我對“語言”有了概念,韓東朱文讓我看到一種“力量的寫作”,王安憶則常令我突生幻滅之感:你還寫什麼小說啊?!
影響我的外國作家當然也有很多,因閱讀與感悟均有限,還是不談為好。
附上一篇短文〔見附錄--編者注〕,是篇“創作談”,或許能表達我對真正好作家的由衷的尊崇之意。
沙門:巴喬,你說你辭職在家寫作,我心裡一下就出現高更和 Sherwood
Anderson 的名字,很想知道:是什麼促使你毅然做出這樣的決定?又是什麼使這樣的舉動可能呢?我想這一定會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事實上我已暗暗受了你的啟發,心裡籌劃著將來如何在掙到一點錢後停業一年專心寫作呢--不能全神貫注於自己熱愛的事情實在是一件太辛苦的事!
巴喬:其實也沒有什麼,一種個人的選擇而已。我原先在電視台幹,待遇在我們那應算是不錯的,可它留給我自己的時間卻越來越少,你知道,寫作總得有一定的時間保障,當我苦於腦子裡有想法卻沒時間動筆或情緒來時卻被外在的東西阻隔間斷得四分五裂時,我想,還是歇下來吧。我的《離開南京的日子》一文裡有這樣一段話,多少傳達了自己一些這方面的想法:“那不正是我想要的一種狀態嗎。一份時間充裕的工作,一種鬆散的關系……”它們都符合我對“工作”的要求--如果我非要工作的話。我覺得還是有份工作的好,它至少能給我基本的生活保障,那樣我寫作的心態就會更平和些,可我也知道這樣的工作可遇而不可求--誰會願意養個閑人呢。你要吃飯,你就得幹活,這是天經地義的。來南京前,我對原來的單位頗有微詞,我本以為可以得到理解和聲援,可有個朋友卻並不給我面子。他說:“單位給你發工資,你倒總想呆在家裡寫東西,從道義上講,這也說不過去啊!”我覺得他講得有道理,簡直可以說是醍醐灌頂,它徹底扭轉了我對生活的許多看法。我辭職,不是單位給了我什麼壓迫,我更不能以受害者或是叛逆者的形象自我標榜,那將是很無恥的。我辭職,僅僅是我個人的選擇,它僅僅說明了我的無能(因為不是跳槽--我也無槽可跳),我無能到不想工作,我無能到只想著寫作……”七月初,我遞交了辭呈,單位挽留了一下,八月批了下來。我的辭職理由是“喪失工作熱情”,這也算是原因之一吧。辭職後面臨的經濟壓力還是挺大的,因為不懂得節省,而電話費卻因上網和與外地朋友的聯絡而直線上升,我還要抽煙,間或還得請次酒,我目前的稿費還不足以負擔這些,基本上在靠積蓄維持。辭職後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興奮點少了。請注意,我說的不是所謂“資源”,而是“興奮點”。寫作當然是需要興奮點的,但我目前成天呆在家裡,面對的除了電腦便是書籍,使我產生寫作沖動的“點”越來越少了,這是我原先沒有預料到的。蘇州畢竟不比北京或南京,沒有一撥相同狀況與想法的朋友(就我接觸而言,辭職居家寫作的在蘇州可能也就我一個吧),白天我常常會找不到出門的理由,朋友們都要上班,我出去幹嘛呢?事實上,辭職後我的生活反倒比以前規律多了,熬夜也少了,是的,熬夜幹嘛呢?明天不多的是時間嗎?……再過一階段吧,等我的經濟不足以維持目前的生活狀況或“興奮點”的困擾加劇的話,我可能會出去找工作。
同樣,我也不覺得這是種值得自憐的妥協,看到吳承駿的一段話,我覺得他說得沒錯:“對我來說,我覺得辭職是為當時的情形所迫,而重新找工作同樣的也是為目前的情形所迫。這兩者在時間上是錯開的。它們僅對各自發生的那個時刻負責,而它們本身決不是互為因果。”沙兄,如果你將來也打算居家寫作的話,經濟一頭當然會考慮到,有關“興奮點”確實也該有預見。不過,北京不比蘇州這小地方,可能會是另一種情形。
不管怎麼說,做自己喜歡的事總不會太苦的。
沙門:嗯,你的情況對我很有啟發。經濟倒在其次,你說的“興奮點”的問題確實值得考慮。海德格爾說“煩”乃生存之本,佛家說“煩惱即是菩提”,生活的不如意也許正是創作的源泉,離了這個源泉,給自己布置一個安靜隔絕的“巢穴”,反而寫不出東西來,也是完全可能的。不過我想如果一個比較成熟的作家,
有需要長時間勞動才能完成的寫作計劃者,還是必須全力以赴吧?希望你能走出低潮,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