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方﹒
回答幾個問題
〔編者注:今年一月間,沈方先生通過網 絡接受了本刊的採訪。提問者為祥子〕問: 首先謝謝你把詩 稿投給《橄欖樹》。《橄欖樹》一直得到 許多作者的支持。讓我們從你在《橄欖樹 》發表的一些詩聊起如何?
答: 八十年代風起雲湧的詩歌運動,可 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產生了不少傑 出的詩人,從 北 島、多多到 韓 東、於堅、西川等人都寫出了著名的 詩歌。至於詩歌運動的意義,目前還眾說 紛紜。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八十 年代,詩人們比較全面地進行了探索。因 此,才有了九十年代更接近於詩歌本身的 漢語詩歌的寫作。
我也是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我是一 個笨拙的人,或者說是一個起點不高的人 。我既回避“旗號”、“主義,又遠離高 深的詩歌理論。參加過詩歌小組之類,始 終是“哈雷慧星”式的漫遊者。我早期的 詩歌(正確地說是一些幼稚的習作),至 今看來令人慚愧。這是“悔其少作”的通 病。當然這也是一種積累。
進入九十年代以後,由於一些客觀原 因,我似乎離開了詩歌。但是,詩歌是這 樣一種東西,一旦傳染就無法根除。如同 一個人的臉,終其一生不能改變。而現實 不可能是完美的,就象羅伯特﹒勃萊在聽 眾不歡迎他的朗誦時,情急之中喊叫的: “你們一走出去,現實就不會是你們所想 象的那樣!”。於是我又開始寫詩,而且 出於簡單的想法,我寫得比較平靜。
詩歌成了我抵擋現實、保存自我的巢 穴。也可以說,我是在模仿葉芝建築一座 塔樓,讓精神有一個生存的居所。既放棄 了登高呼號,又消除了試圖“藏之名山” 的奢望。所謂“時代號角”也好,邊緣性 的“個人寫作”也好。我以為我是有距離 的。我傾向於認為,詩歌是對生存狀態的 的關懷。這些年來,我寫下的詩歌,大多 是自言自語式和虛擬交談式的。而且,我 不大投稿,偶爾試試也往往令人失望。不 客氣地說,我的詩歌無非是孤獨狀態下的 自我慰藉。我以為,我應該坦率。我發表 在《橄欖樹》上的詩,基本是這樣。
另外我也應該承認,以《橄欖樹》為 代表的網絡雜志,現在成了我的興奮點。 在耗費時日的漫遊中,就象發現了島嶼, 我找到了新的交流。投稿需要勇氣,而發 送一個電子郵件有一種神秘的快樂。相對 來說,比較親切。
問: 什麼是邊緣性的 “個人寫作”?能具體談談這種寫作態度 和你的創作的距離嗎?
答: 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可以 說是一個方向,也可以說是一種態度。在 一個商業社會,歸根到底,人是經濟的動 物。文學藝術,更具體地說詩歌,不可能 處在社會的中心位置,始終處在社會的邊 緣。“時代號角”式的救國救民的政治性 寫作,在現實面前無疑是蒼白軟弱的。
處在邊緣的文學藝術,在強調精英品 格和獨特審美的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另一 個方面。“個人寫作”是一種傾向,詩歌 在其中很容易成為個人角度的智力遊戲和 學院式的高超技巧。當然,一個寫作的詩 人,在他全部的寫作中,很難避免滑入這 種傾向。抽掉了情感的詩歌,或者說在消 解了日常生活的詩情之後,剩下的就是文 字了。感動消失了,有的是理解、分析。 出於對詩人們的尊重,我不想指出具體的 詩人。比如下面這首詩:“土撥鼠在挖土 /有人問/土裡有什麼/土撥鼠說:土裡 有土”,連分析都很難展開,“此中有深 意”?有沒有,只能猜測了。也許可以說 這是最簡單的詩,就是說“土裡有土”, 而我總覺得心裡不踏實。
這個觀點可能有失偏頗,在詩歌史上 ,不排除有些詩人構築的詩歌世界,主要 是哲學的、理性的。但是,這些詩人是區 別於“個人寫作”的。我認為“個人寫作 ”是危險的。如果進一步說,完全個人性 的感情私語,也不會有普遍意義。我說的 距離是,我願意接受世俗化的傾向,主張 在日常生活中獲得日常詩情。不過,我有 時侯不免會懷疑自己,這樣把握是出於藏 拙的目的?我想和祥子先生探討一下這個 問題。這裡要說明的是,“詩情”與通常 意義上的詩意,是有區別的,其重心是在 “情”上。完全脫離現實是不可能的,詩 人本身就是現實生活的一個矛盾體。這不 僅是一個審美的傾向問題,而且也是一個 有關詩歌本身的問題。我們可以這樣認為 搖滾歌詞這一類現代民謠,確實是一個重 要的現代詩歌文本。
問: 讓我還是保持一 個採訪者的角色比較好,否則這篇東西就 太大了。:)我只是想很快地表明兩個個 人的觀點:(一)文學閱讀必然是一種猜 測的過程。是文本和個別讀者的經驗相交 流的結果。一句話脫離了日常的使用環境 ,它的含義就不可能確定。(二)而這可 變的含義,和這句話的形式有關,和讀者 的期待,經驗/知識有關,卻和作者的創 作態度、意旨沒有什麼關系,除非我們有 意研究作者的本意。作者本意和作品的含 義不是同一概念。
新作者在自信確定之前總是怕被劃入 一個群體,因此在言語中常常強調寫作中 個人的成份。但每一位作者都受益(或受 害)於其他人的寫作,尤其是同時代的人 。寫作總是對已有文本的一種反應/反駁 。我想,作者的創作心態之所以成為這麼 大的話題可能更多地和寫作者的社會地位 在最近幾十年的激變有關。
讓我們回到你在《橄欖樹》上發表的 詩這個更有意義的話題上來吧。你在《橄 欖樹》九八年年終的長詩增刊上發表的 《天堂的舞蹈》有許多你過去在《橄 欖樹》上發的短詩的句子,和我們現在發 的你的一組詩在音韻和情感色彩上都有明 顯的不同。你是否也有自覺?能不能說說 這些詩的創作過程?
答: 祥子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一個寫 作者,不可能離開閱讀,他也就無法逃避 其他人寫作的影響。甚至在有的時侯,還 很難排除模仿的痕跡。我要再說的是,保 持寫作個性,不等於邊緣性的“個人寫作 ”,重要的是要尋找共性,或者也可說是 感情的共鳴。文學與猜謎式的文字,有根 本的區別。在智性的樂趣之外,還應該有 點別的東西。
還是來回答祥子先生的問題吧。要解 釋清楚自己的詩是困難的,而且在事實上 是不可能的。更會有這樣的情況,寫作前 或者寫作起始的意圖,往往與最終的結果 相悖。可以說會產生一種反叛。好在問題 不是這樣提出。先說說我的寫詩習慣,通 常的情況下,我寫在一個筆記本上。我至 今無法在電腦上直接寫作詩歌。寫詩的時 侯,多數是零星的業余時間。也有可能是 在上班用的工作筆記後面,一頁一頁往前 寫。因此,我的詩大部份是短詩。
我幾乎不寫長詩,《天堂的舞蹈》是 個迄今為止的唯一一個例外。那是在19 96年下半年,我連續在一個筆記本上寫 了《天堂的舞蹈》的雛形,是一些沒有題 目,只有數字編號的篇章。整個篇幅比現 在的狀態要長得多。而且那時也沒有《天 堂的舞蹈》這個題目。
現在來看,這屬於一個人被拋入商業 時代後的迷惘。後來就放在那裡沒有去動 ,一直到1997年底、1998年初這 段時期,才突然想到了題目,好象是找到 了一條線,刪去大約三分之一,整理成現 在這個樣子。
在這期間,我從中提出某些章節,寫 成幾首獨立的短詩。這些短詩脫離了原來 的氛圍,變成了另外一種存在。這是有些 句子相同相近的原因,這也可說是寫作變 化的樂趣。至於現在這組詩,寫作時間要 晚一些,我也感到有比較明顯的變化。我 自覺,這組詩比《天堂的舞蹈》要清醒一 些。這既可說是,從一個時期進入了另一 個時期,也可說我還是一個不夠成熟的人 。當然,不變是相對的,甚至可能會有自 相矛盾。
問: 我很喜歡現在的 這批(包括登在 去 年十二月期的那首)的節奏。很幹淨 ,顯得對要說的東西和敘說方式很有信心 。不過就是這樣有內容指向、語言也直指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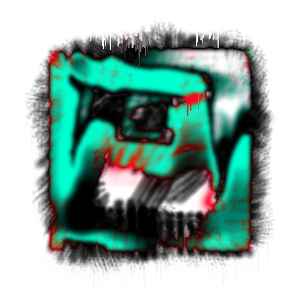 心
有打擊力量的詩,目前的讀者也不是很多
。我們估計了一下在《橄欖樹》的讀者中
大約有三分之一是讀詩的,我想這在目前
較大型的綜合性文學刊物中也許已是算比
例較大的。因之而生的問題之一,從寫作
的角度去看,就是尚在寫詩的人較少有機
會受到其他作者新創作的刺激。你能在這
一年把過去的詩進行整理,並能寫出一些
不同的詩,是偶然而然還是有些其他外在
的契機?
心
有打擊力量的詩,目前的讀者也不是很多
。我們估計了一下在《橄欖樹》的讀者中
大約有三分之一是讀詩的,我想這在目前
較大型的綜合性文學刊物中也許已是算比
例較大的。因之而生的問題之一,從寫作
的角度去看,就是尚在寫詩的人較少有機
會受到其他作者新創作的刺激。你能在這
一年把過去的詩進行整理,並能寫出一些
不同的詩,是偶然而然還是有些其他外在
的契機?答: 先來說一點題外的話。最近獲悉, 安徽的《詩歌報月刊》面臨停刊。去年1 1月,在江蘇張家港參加詩會的76位詩 人聯名致信安徽省有關部門,希望能讓《 詩歌報》生存下去,但看來還是前途渺茫 。年末年初,國內純文學刊物的生存,成 了一個熱門話題。文學期刊的停刊、消失 似乎成了一個趨勢。上海《文學報》一篇 文章提到,旅居德國的作家龍應台說,“ 目前內地文學期刊的‘沒落’也許是一個 新階段的啟始。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裡,應 該會有各種風貌的文學刊物,雅的俗的, 軟的硬的,俏皮的嚴肅的。唯一不可能有 “雅俗共賞”的刊物。”
現在這個時期,可以視為文學的整合 期,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在某種程度 上,是寫作者或者說國內的文壇造成了現 在這個局面。一般來說,詩歌的讀者就是 一個詩作者,或者是一個潛在的詩作者。 純粹意義上的讀者向來不多,一首詩倘若 能抓住這一類讀者,必定是傑出的詩。當 然汪國真的那些詩另當別論,但這個現象 同樣值得我們思考,僅僅看作是媚俗恐過 於簡單。現在的情況是,舊的詩歌被讀者 唾棄了,而新的詩歌卻放棄了讀者。遺憾 的是,我們有好多詩,不僅失去了純粹意 義上的讀者,同時也把作為詩作者的讀者 弄得疲憊不堪。
如果來點“實話實說”,坦率地說, 我也不太讀現在刊物上的詩。不是我不願 意讀,我覺得我還沒有到不讀“過世不到 二十年的作家的書”那種高度。我還是很 願意借鑒同時代詩人的。使我經常放棄這 種努力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好多詩實在不 知所雲,或者是讀了以後讓人無動於衷; 二是刊物上的詩太多,好詩和庸詩、爛詩 混在一起,魚目混珠,實在沒有閑功夫去 尋找好詩。過去有一句話:“寫出一首好 詩是名詩人,寫出十首好詩是大詩人”。 寫一首好詩果然不容易,但要讀到一首好 詩也並非是易事。我以為對詩歌的甄別和 評論日益成為重要的事情。同樣遺憾的是 ,有不少評論總是熱衷於炒作和推出自己 的理論體系,起不到對讀者的導向作用。
在這種狀態下,寫詩的人要“挺住” ,只有依靠他自己的“內力”。不過說是 “內力”還過於機械,還屬於技術層面。 只有把詩當作了生活方式的人,才有可能 “挺住”,並寫出好詩來。詩歌首先是一 種生存形式,是一種脫離了現實、超越了 現實的生活。試圖從一種理念出發,在現 實中尋找詩歌,必然是笨拙的,同時也是 偽善的。那樣的詩,不過是偶然的機遇, 是零碎的片斷而已。詩歌存在於詩歌世界 之中。龐德說過,大詩人的詩不可能每一 首都是好詩。龐德的話可以這樣理解,一 個詩人生話在他的詩歌世界裡,詩歌從那 裡象植物一樣生長出來,但是不可能每一 種植物都開出花朵。
當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一些詩,或者是 說是一些詩句的時侯,我不可避免也無可 奈何地把它們當作是個人的日記和交談的 記錄。在一般的情況下,寫過之後要過了 一段時間,我才有可能重新翻動筆記本, 往往在這時侯就會有新的發現。這時侯也 就是詩歌最終成形的時刻,在此同時,新 的感覺、新的寫作沖動也就產生了。需要 說明的是,在語言方面比較傾向於明白、 重量和力度,追求那種脫口而出的感覺。 當然,對於讀者來說,這種想法可能依然 是一廂情願的徒勞。白居易的《賣炭翁》 不可能是寫給那位生活中的賣炭翁看的。 石壕村的老漢,也不會讀杜甫的《石壕吏 》。白居易和杜甫同樣,無非是寫出了他 們內心的良知。徹底地說,太多的想法對 寫作者是多余的。
問: 在我問最後一個 問題之前,讓我先謝謝你這麼認真耐心地 解釋你的看法。這中間我的機子還爆了一 次,要你重寄答案。但再好性子的人也是 有限的。希望我們能在《橄欖樹》上不斷 地讀到你的新的文字。
我個人對“挺住”的信心一向不足。 我總覺得“幸福感”、“享受”、“娛樂 ”等等更可靠一些。吳晨駿在這期的 【編者短語】中在談到為什麼大家堅 持做《橄欖樹》這件沒“好處”的事時提 到“理想主義”。我們有許多編制者的確 是這樣的一些今天極難得的有理想的優秀 人物,我能和他們一起同事是一個福氣。 但就我自己來說,一些做得比較長的事多 是些謀生必需或自己喜歡的事情。你是否 覺得在今天的環境壓迫下,特別是生活的 壓力,寫作本身的樂趣已不足以支持作者 寫下去了?如果是,你覺得像《橄欖樹》 這樣的民間刊物又能做一些什麼支持作者 的事?
答: 現在很少有機會,能在我附近找一 個朋友比較純粹地談論詩歌。這樣一次網 絡訪談,其實是愉快的事情,同時也是我 有興趣做的事情。
詩歌畢竟是形而上學,不可能有什麼 實用性。尤其不可能帶來金錢。在這個問 題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所謂“英雄 所見略同”吧。要“挺住”不能依靠刻意 的企圖,還得出於一種本能才行。理想主 義的努力非常值得尊敬,而單純的理想主 義恐怕靠不住,理想往往容易破滅。一個 人終其一生,鮮有實現理想,幾乎沒有。 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人都會以悲劇來收 場。世上的喜劇,要麼是鬧劇,要麼是笑 中有淚。也許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客觀上,寫作者確實需要一個環境。 沒有生存空間和必要的激勵,寫作者無法 存在。這個環境也必然有好或壞、充分或 不夠之區別。我想順便在這裡提一下,吳 晨駿他們在南京發起的作家問卷以及由此 引起的討論,我以為在客觀上起到了開拓 寫作空間的作用。有人斥之為狷狂,這恰 恰說明了這些人的虛弱。國內的文壇,實 在是需要一些有力的刺激。
作為詩人這一個體,既不能脫離環境 ,又不能完全依賴於環境。對文學史我缺 乏研究,但是常識告訴我,曾經出現了大 作家和經典著作的歷史時期,也不是文學 佔主導地位的時期。唐詩所處的歷史環境 ,詩在那時侯首先是做官的“敲門磚”。 “寫作本身的樂趣”對寫作者來說,比環 境更重要。寫作的樂趣對有的人起作用, 對有的人就不一定起作用。具體地說,寫 作者必須始終處於“有感而發”的狀態, 才有可能一直寫下去。
至於文學刊物,我首先要強調,從文 學角度看不應該有民間或官方之分。客觀 現實是,許多官方刊物,盡管還有經濟支 持,也無法避免式微趨勢。刊物的存在和 作用,是在作者和讀者之間,也許讀者比 作者更重要。作者還可以不考慮讀者,刊 物如果不考慮那就只能是笑話了。刊物一 方面是作者的聚集中心,另一方面對作者 必然會產生影響。《橄欖樹》這樣的刊物 ,是一個新的文學載體,更有發展空間。 《橄欖樹》能聚集一批作者,同時又擁有 一批讀者。這就是對作者的支持。再說具 體,我就是外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