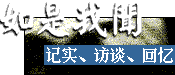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熊晉仁﹒
枯守最後的詩 意
應該走出來,走進大地,獨 自一人,被擊啞,即使只有一次。--狄蘭﹒托馬斯
一、直面昏暗
上海是一個不夜城。燈火輝煌的上海 的夜晚,阿鐘固執地思考著他一生的主題 --昏暗。對阿鐘來說,這個主題不是堂 ﹒吉訶德假想的敵人--風車,而是他必 得每日痛苦地遭遇的現實,也是他必得每 日與之周旋、扭鬥的功課。
人是不習慣黑暗的(睡覺和偷情是一 種例外),因此人總是習慣地崇拜太陽。 太陽總是要沉落的,於是月光也常常贏得 人們的讚賞。夜晚的光明是不保險的,天 空不會老是湛藍湛藍的,因此燈光和錢幣 的光芒便出奇地可愛而動人,它們是不會 背叛人的;如果你有生活在文明城市的幸 運,並且有許多錢的話。那麼,科技崇拜 和拜金主義有什麼奇怪的呢?雖說這種光 芒總是會顯得昏黃,但它們不會太刺眼的 ,至少它們不象太陽那樣容易欺騙或灼傷 人的信任。
阿鐘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以將近八年的時間寫一部詩,不是歌 德《浮士德》那樣的浩卷長篇,而是《昏 暗 我一生的主題》這樣不算很長的詩稿 ,而且他絕不放棄對“昏暗”的“執著” ,這就很驚人,很怕人了。到底為什麼、 為了什麼這樣痴迷,而不象追星族那樣瀟 洒走一回呢?請我們走進他的“詩--思 ”的密林。或許,走出來的我們就不會再 驚訝於他的枯守寂坐了。
阿鐘對他生活於其間的這個城市、這 個世界是疏離的,他忍受著也悲憫著:“ 人群的碎葉被風吹刮著”,“目光遲鈍的 民眾如同泡沫/潮湧過我舉起的酒杯”。 他問:“這個世界還要繼續腐爛下去嗎/ 我還要繼續來這裡等候黑夜把我侵吞”?
人們總是會“從他們的目光裡打量苦 難的日子/他們指著天空冥想他們的往日 溫馨”,這個苦難的世界被慰藉了,被麻 木地容忍了。日子是變得容易了,但苦難 總是如影隨形。敏感的詩人們拒絕這種安 慰,於是他們問天、問地、問自己,靈魂 盈滿苦汁,生活變得艱難。“在這個墳墓 一樣的世界上/平淡無奇的日子追隨著我 們的蹤跡/面對這條坎坷泥濘的小路/我 的靈魂是不自由的”,“我會死得多麼悲 慘/因為我已經把微笑忘掉了”。詩人是 不甘於這種命運的,他們要詰問,要反抗 。他們試圖以“幻象”(葉芝意義上的) 的力量來點化“荒涼的歲月塵土”,“尋 找真情”,“讓靈魂象太陽一樣重新升起 ”。
阿鐘有一種幽靈般跳出來“看”的特 質:看世界、看自己,絕不虛飾矯情,讓 生活就象生活本身那樣呈現,讓生命就如 生命本身那樣感受和言說。生生死死的慘 像,自己的慘像,“虫蟻的世界/它們無 聲地搬弄歲月”,而詩人居然幻想極樂, 對這個世界這是一種“冒犯”,對自己則 是苛刻。由於光天化日下的世界慘不忍睹 ,阿鐘喜歡傍晚、夜晚的“看”,這時的 浪漫情調或許會舒解一下憤懣和絕情。“ 誰來感化我……我是一堆不會發芽的枯枝 /在幹澀的面孔中浸泡”,長期在昏暗的 時光中“看”昏暗,昏暗便會浸漫你,好 象你及這個世界本來如此。這是一個可怕 的深淵,魯迅的絕望(所幸沒有絕情)是 深有意味的,也是必須警惕的。“通向人 性秘密的路途上/我無數次感到沉痛和困 惑”,但自由和愛情是詩人的宿命,所以 象波德萊爾那樣洞曉地獄三昧的詩人還是 禁不住要忘情忘思於小孩的純真少女的柔 情和老婦人的質朴。阿鐘說“我要和你一 起/用歌聲把我焚燒/用歌聲把我祭獻” ,這個“你”是他的女神,是他的作為女 神影像的女人,“盡管情人會失去,愛卻 不會;盡管人身自由會喪失,良心和思想 的自由卻不會。而死亡也不得統治萬物” (狄蘭﹒托馬斯詩句)。如果沒有對於愛 情的痴迷,我想,瘋狂或自殺就是詩人的 定命。
在昏暗的天空下,人們害怕真誠的交 往--與別人、與自己的內心、與夢境、 與上帝,但“哪裡有危險,拯救之力就在 哪裡生長”(荷爾德林),所以阿鐘就是 要毫無保留地“看”,“看到那些苦苦掙 紮的生靈……沒有歸宿感”,看到“我已 如此脆弱”,而生命是應該崇高的,是應 該超越於枯枝敗葉之上的。“什麼東西是 我向往的/巴羅克式的建築風格/巴羅克 式的處世風格”。這是阿鐘的古典情懷, 是他枯守的最後詩意,“為伊消得人憔悴 ”啊,有哪一位詩人是腦滿腸肥的呢?有 哪一位詩人是如魚得水般存在於這個世界 的呢?
二、走過荒涼,走出虛無
“英雄沒落了/人沒落了”,這是“ 上帝死了”(尼採所謂賢哲的“上帝”- -一種本體論虛設)的可怕結果。如果一 切崇高的價值之源、價值理想再找不到依 憑,沉入泥沼、墮進深淵便是不可避免的 。
“廣場上我聽見人民在哭泣”,“僅 僅一次歌唱/假象變得莊嚴”,“一座破 舊屋子的周圍/正在繁殖著某種涼意/某 種渴望被表達的‘非存在’”,“我回到 冬天/風雪的掩蔽所/孤零零的戰車後面 /尋找骸骨存放的洞穴”,“在世界的盡 頭,了望沒有邊緣的黑夜”。這就是我們 生活的現實,面對它“要麼屈辱/要麼不 屈辱”,這是阿鐘對人的“階級”分析。
唯物論是人類的一種疾病,這種疾病 的晚期症狀便是“虛無主義”,機器的暴 政和物欲的囚禁是唯物論的人類一手制造 的。諸神已經消隱,現代的人們已經很難 找到駐足之地。但希望就存在於“詩-- 思”的不斷追問之中。
“混亂無序的世界/那個無時不在的 作者現在哪/他用人群偽裝自己他現在哪 ”。詩人透過夢幻、直覺和迷狂的精神體 驗,撩開了“摩耶”(這個世界)的面紗 ,因此詩人相信原始的生命河流還在我們 不知曉處奔流,而“純淨如水的天空啊/ 純淨如水的詩篇/純淨如水的生之夢幻/ 純淨如水的旋律……”就不僅僅是幻想, 只有重新擁有它們,詩人的屈辱、囂張、 自虐、挑戰才是有盼望的,而不是“西西 弗斯”的輪回。
“是誰/讓我面對這個世界/是誰讓 我醜陋的笑聲/象死亡一樣/在這黑色的 國土上/傳揚”?面對這個世界及我們自 己,詩人發現了“無辜”的深不可測,發 現“在這個光明的歲月裡/無聲的狂暴” 。
這個絕望的囚徒
正在生病
這個危險的罪犯
正在等待日出
是誰讓我面對這個世界
作為目擊者
是誰讓我昏暗地了此一生
作為目擊者,同時也是參與者的詩人 並沒有絕望,一個還在“等待日出”的人 是不會絕望的,他相信“海洋在上升/偉 大的人格在上升”,鮮花將在黎明前由內 部綻放。
三、“我要你們用自己的手去撕碎你們的 光榮”
--阿鐘對於這個世界 的宣示
無辜的人類的罪惡,這好象是一個悖 論,就如宿命論者其實擁有自由意志,只 是表面上說不通而已。一個崇高的宿命論 者在他洞悉了自己的命運時,他也就可以 自由地決定拒絕還是順從此命運;而如果 命運不能被知悉,而只是好象有所謂定命 ,那麼你就無法為你自己的墮落(假如你 說這是命運)進行有效的辯護。
“我們阿諛,塑造了我們的青皮光棍 ;我們奉承,繁殖了鱷魚成群”(葉甫圖 申科詩句),馬克思說有幾流的人民就有 幾流的政府。不是什麼魔法,就是我們自 己把這個世界搞得如此無法安居的。因此 ,阿鐘的宣示是拒絕溫情和媚俗的“獅吼 ”,他不要人們的廉價安慰,也不要廉價 地安慰人們。這樣,阿鐘的詩句就有了“ 冷兵器”的特點。它們戳痛你、撕裂你, 背對著你甚至咒詛你。這是一種“熱腸冷 眼”的自覺和對於詩人天命的勇敢擔當, 他要“自絕於大眾”之外,雖然他打心眼 裡熱愛著人民(他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啊) 。
我是忠誠的
在反叛中我保持著忠誠
在田野中我看著神靈的影子
基於這樣的認識,阿鐘放膽地使用他 的“冷兵器”。阿鐘的“冷兵器”首先是 針對自己的,是他的自我解救的不二法門 ,這應該說是“殘酷”而公正的:
我要看著你們和我撕殺
我要看著你們把我打敗
我要月光照耀這片戰場
……
我要你們拒絕我
我要你們的眼淚白流
把你們的同情留給自己吧
你們,博學的混蛋
……
從昏暗的曖昧的泥沼中拯拔出來,從 現世的意義上說是流浪,是自我放逐,若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種漂泊實是一種歸 家的旅程。詩人永遠在回家的路上,這是 最重要的,至於荷爾德林說的“詩意地安 居”則只能說是一種幸運,一個理想。
四、在“詩--思”的路上
一說到思想,我們就會想到邏輯、理 性、辯証法,好象思想是亞裡士多德、羅 素這樣一些人的專利。在理性主義丟醜之 後的今天(這是由康德、休謨、卡爾﹒波 普等哲學家敏銳發現的),人類越來越感 覺到一種“無告”的焦灼,生活的意義、 價值越來越曖昧不明,科學主義的、功利 主義的樂觀安慰不了那些心靈敏銳的人, “誰來感化我/誰來注意春天給我的動搖 ”。那麼我們就會問,是不是有一種迥異 於理性主義者那樣的“思”?假如有這種 “思”的話,它能不能澄明我們生活的昏 暗、瑣碎、荒誕,它能不能引導我們走向 尊嚴意義的生存?
深入到文化史的內部,我們會發現有 一種特別的“思”,它還沒有引起更多人 的關注和重視,它還沒有被很好地知道, 這就是人們通常因夢幻、直覺、情緒而窺 到的難以言表的“思”,而且是一直被詩 人們自覺學習和實踐著的。這裡我所說的 是廣義上的詩人,因此我把這種“思”稱 為“詩人的思”、“詩性的思”,簡稱“ 詩--思”。
詩在本源上是與歌不可分的,古代的 詩人在本質上都是行吟詩人。詩,從漢語 的結構上可看出其源始意義,它是語言中 的菁華,是語言中的語言,是人與存在( 可說是神秘的超越世界)溝通的橋樑。這 樣,我們可以說優秀的詩歌便是存在的呢 喃。一般人,由於生存的緊迫性和功利的 壓迫性,很難聽到存在的呢喃;詩人們由 於與存在的親近而傳達出了存在的聲音, 它是內在於生命的也是超越於一般聲音的 。優秀詩歌的普及,則是因為生命的感同 身受,雖然對多數人仍然是模糊的,詩人 正好使他們發現了一線光,發現了生命更 本源更宏大的秘密深淵。
由於詩人們的敏銳的天性,他們都會 感受到彌爾頓《失樂園》所描述的那種揪 心的痛苦。當詩人們覺悟到被拋出的命運 後,流浪--歸家的尖銳性就進入了“詩 --思”。如果詩人不窺見存在的秘密, 哪怕只是深刻的一瞬,詩人不會有被拋出 、被遺忘的痛苦,但沒有這種痛苦,則就 是“錯認他鄉是故鄉”的非詩人了,因此 可說詩人注定是痛苦地走在“詩--思” 的路上。漫漫漂泊路是昏暗的,已經沒有 了存在的澄明;走出昏暗的可能仿佛存在 ,但道路是不可知的;諸神隱退了,只留 下詩人莫名的“天問”。
面對此世的生存,時間是一個巨大而 可怕的問題,阿鐘感嘆“我/僅僅是被遺 漏掉的一段/日歷”。孔子曾有“逝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的無奈,佛陀則發現了 “無常、苦、空”的時間鐵律。如何面對 時間的嚴酷性呢?詩人不只對落花流水傷 感,詩人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安慰這種傷感 的力量。另一個同樣嚴酷的事實是空間的 冰冷、障隔和廣漠,“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白居易詩句),詩人 獨憔悴啊。“在我夢想和真實的往昔之間 /在我把鮮艷的故事編纂起來的時候/我 只是你們的一個故人”,一個故人,每天 的生命真實。可以說阿鐘八年來的“詩思 ”具體而整體地呈現在他的《昏暗 我一 生的主題》之中,他的“詩--思”的內 在結構和生命關懷正好是圍繞著以上兩個 主題展開的。
回憶和想像是超越時空嚴酷性的一種 力量,它們並非是虛幻的,而是實際地內 在地支持著詩人的漂泊。而幻像和神秘的 生命體驗則更加堅定地引導著詩人歸家的 掙紮。詩人之走向神秘主義可以說是命中 注定。西方中古時期的隱修士,其著作每 每是以詩化語言寫就,他們在描述神秘體 驗時則以非常感性化的愛情語言表達,這 可從另一方面佐証詩人的神秘主義傾向和 泛愛情結。昏暗的漂泊之路是阿鐘一生的 主題,但還有一種更加隱秘的主題,我稱 之為“愛情”,首先是對存在的愛,對“ 人詩意地安居”的執著。
有一種時間,還沒有被我們充分認識 ;有一種世界,在我們的思維所可及的境 界之外。這是阿鐘切膚般感受到的,他這 類的詩人一生都會耽於如此的“詩--思 ”,詩性的體驗--沉醉、迷狂、孤獨導 致某種程度的結結巴巴甚至啞默。當人被 一種奇異的境像震住時,結結巴巴是必然 的,所以阿鐘的這部詩與口若懸河的那類 語詞渲泄迥異;人聲嘈雜,存在就會喑啞 ,對他來說,傾聽莊生所謂“天籟”是第 一位的,而寫作主要就是這種傾聽的傳達 。存在的呢喃與詩人的言說之間總是存在 著一種張力,真正的詩歌技巧只有充滿了 這種張力才有意義。我們時代制作的詩歌 太多了,被這種詩歌毒害的人也太多了, 這是一個偽詩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 阿鐘的這部詩是有真正的抵抗意味的,這 部詩是他的八年抗戰的一部精神實錄。
別爾嘉耶夫把時間分為三類:一是自 然時間--宇宙時間,例如地球、月亮與 太陽的運動周期作為地球人類的時間標準 ;二是社會--歷史時間,例如以社會事 件指稱歷史時期;三是生命--存在時間 ,例如詩人說永恆即是小孩燦爛微笑的一 瞬,這是還不為很多人感知的時間。古人 說“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這對無 體驗者無法言明。對於生命--存在時間 ,絕大多數詩人都有深刻的覺知,我們讀 許多詩人的自傳不難發現很多例証,這種 覺知一般出現在馬斯洛所謂“高峰體驗” 之時或迷狂之時,阿鐘則試圖自覺地進行 某種修持。他的精神體驗有一種細膩、感 性的風格,這種風格在他為紀念他的朋友 、圓明園藝術家周瞻弘的一組詩中有充分 的表現。由於這種努力,他的很多詩句很 有些《奧義書》的神秘意蘊。《奧義書》 反復申明的“動中之動者”、“存在中的 菁華”,根本也是一種特別的“詩--思 ”努力所致的存在的呢喃或生命的妙音。
在“詩--思”的路上,是孤寂的、 危險的,一切理性的安慰和功利的算計無 效了,仿佛進入了昏黑的隧道,但舍此無 從找到歸途。所以荷爾德林說:“哪裡有 危險/拯救之力就在哪裡生長”,這是存 在的意蘊,也是存在之愛的奧秘。
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重要的不是廉價 真理的自明,而是不可遏制的沖破時空壁 障的生命激情,在充滿自由精神的歌哭中 ,詩人會迎來他的一次“存在的花開”( 奧修語)。首要的前提是能象小孩那樣敢 於要天上的星星:
我要我的靈魂之淚
我要我的水中之水
我要我的血中之血
我要我的石中之石
我要我的肉中之靈
西方諺語說需要創造力量。阿鐘所需 要的,我想也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那麼還 需要的就是互相鼓勵著闖這個需要的“飛 地”,而不是吆喝著上同一條路。
注:引文除注明出處外,均引自阿鐘的長 詩 《昏暗 我一生 的主題》。
(1997.7.18-28,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