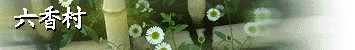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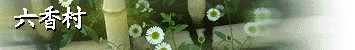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
| |
1990年的4月上海的《萌芽》杂志通知我到上海去领1989年的《萌芽》文学奖。
这件事让我喜出望外。要知道这是1990年!在这之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告诉我已经取消了《陌生世界》出书的选题。1989年第4期《芙蓉》杂志虽然发行了几十万册。至今在图书馆里是找不到这期杂志的。因为邮政发行比个体书商发行来得慢,来不及到图书馆就销毁了。去年我又重新翻看了这部小说,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触犯“上面”的地方。最多也就是写了“人性”。我在被禁的名单中,我的《陌生世界》也在被禁名单中。这个名单是下发到各个出版单位的。他们不知道?就像Y来找我,执意要把这部小说弄成电影一样?!Y想把这部小说弄成电影是一个梦想,无论怎么改,都没有逃脱被“枪毙”的命运。枪毙的理由,因为主题太灰暗:不是“主旋律”。现在回想起来我对Y兄的好感大多来自他对我这部小说的肯定。那会儿文学圈子里很多人,包括一些老师辈的人都抓住这部小说,说我的坏话。他们甚至能背出这部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其实我和“圈子”里的人是不太往来的。他们是国家供养的专业作家,就是不是专业,也是作协某某杂志社的编辑,准专业。我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x老师是一位1957年因诗被打成右派的老诗人,(他原来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1987年“清污”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因为出版了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一书被解散才到文艺社的)他到一个青年创作会议上去组稿,很激动地写信给我:你们江苏的作家为什么要讲你的坏话?当然关于《陌生世界》的。平时我和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意识到了我和他们是两类人。意识到文学圈内在的险恶。也正是这个“险恶”,诱惑我要在这条路上顽强地走下去。我是B型血,天生具有叛逆的基因。
1999年5月,我到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因“邀请”去上海。第一次在1988年秋。是去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文学剧本创作会议。我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越轨年龄》去的。(这部小说1988由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上次住在永福路52号。会议上放映了好几部内部电影,其中有《半夜守门人》和《第三段情》。《第三段情》是一部探讨人性中最深沉的一面“性爱”的作品,一部小制作的B类片。如果论级别的话可能算三级。就是现在电影院也不敢放映这样的电影。散场后他们问我:你看懂了没有?因为在那次会议上我是最年轻的作者。我说:懂了。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震撼!我第一次知道我们还可以这么描写生活!这几部电影对我后来的写作是有影响的。
这次是在文艺会堂报到,离永福路不远。但是颁奖会没有在上海召开,而是在无锡太湖的小山疗养院。据说毛爷爷在世的时候,到无锡来就住在这里。我和上海作家唐颍住一间房间。周佩红是我这篇获奖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见到了当时《萌芽》的主编曹阳和俞天白。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把《陌生世界》的二审编辑L兄也请来了。我的书稿就是他签发的。他因为这件事倒了霉,之后他被调离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芙蓉》杂志。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聚会。我是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参加的第一次文学活动,我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活动。他们都知道我的《陌生世界》被禁。但,还是指定了我代表获奖作者发言。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理所当然地激昂陈词把所有的压抑在心里将近一年的话都说了出来,我的发言赢得了掌声。这是1990年的5月!
有人对我说:你真胆大。不是胆大,我只说了我想说的话。我没有错!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说那些“表面”的话。没有必要去“媚”某一些说法,和某一些人。没有必要用“纯文学”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无法把文学和这样的生存环境割裂开来,我无法不去描写我所看到的生活、和我感受到的生活。痛苦的生命和扭曲的人性。无法不去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我不惧怕“政治”。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和“政治”靠得很近的家庭。我的父母是五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马列主义研究生班”的同班同学。他们那个班的人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1957年的时候,他们这一届的同学里有五分之四的人被划了“右派”,在“文革”的时候,几乎一网打尽。我童年的记忆中1976年之前,我的父母大多数的时候在各自学校的“五·七”农场劳动,我父亲隔离审查的时候,白天在食堂拉煤车,晚上还写“交待”,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赤着膊拉着煤车在大街上走,他拉着沉重的煤车渐渐而去的背影,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成了永远的定格。那些当了“右派”的叔叔伯伯的命运就更惨。20年呀!一个人最珍贵的年轻时代以及事业爱情家庭全部幻灭!我问过一位伯伯:你后悔过吗?他长叹了一声说:“不后悔。因为我没有错!”
时过十年,我感谢上海的老师和朋友,他们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了快乐的时光.何止是几天?这几天给了我后来10的勇气.我对上海抱有好感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然在这之前1984年的时候,我的一篇短小说<梅雨霏霏>获得青春文学奖的消息也是上海的<解放日报>最先转载的.那时我还一个文学青年.
从无锡回到上海,我去上海文学看了姚育明.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是她责编的.还拜访了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周介人老师.
快乐的聚会是短暂的。五月过去就是六月,之后一有一段很长的孤独和沉闷的日子在等待着我。(未完,待续)
◆加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