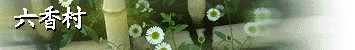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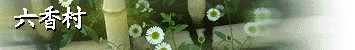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
| |
林昭被密杀前后
(山东) 张元勋
作者简介 张元勋,祖籍江苏,生于一九三三年,五四年考入北京
大学中文系,五六年与同系女生林昭一道参与编辑校园文艺刊物《红楼》
,五七年因主编学生刊物《广场》划为「极右派」被捕判刑八年,六五年
刑满留队管制劳动。六六年五月前往上海以「未婚夫」名义探望狱中的林
昭(林昭六八年四月被秘密处决)。文革开始再被投入劳改。结婚生子。
七七年解除监管,七九年获平反,宣告无罪。安置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任
教,九0任教授,九四年退休。
------------------------------------
一九五七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一千五百人因「反右扩大化」而
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
之间亡命了之,二十二年后,又把这「扩大化」了的一千五百人无一例外
地平反,也就是说北大「扩大化」已扩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四
十一年来,我们全年级竟有近十位同窗英年早逝,而我不会忘记的还有几
位因反右而被枪杀的冤魂:
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被杀在一九五八年。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
选,一九六六年夏自河北省某劳改农场逃出后不久被抓获。化学系的学生
张锡琨,企图越狱而被处死,时间是文革一九七七年。他的遗体由他妹妹
领走,掩埋于四川盆地。而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一九五四级女学生林昭之死
,则是被密杀及灭尸更被掩盖得毫无踪迹。
北大文艺校刊《红楼》热情的女编辑
林昭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投稿用的笔名。我第一次与她交往,
是在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她正在翻阅著的一大堆线装书,我看出那是《
毛诗郑笺》,后来我们从图书馆出来,在南阁、北阁旁的逶迤小路上,她
边走边对我说读过《风.七月》。记得系主任游国恩先生很注意林昭的勤
学与多思,多少次游先生的学术讲演,都即席发挥,没写讲稿,事后都是
根据林昭的记录整理存文的。
一九五六年的秋天,北大党委决定创办一个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名
为《红楼》。编委会阵容如下:
主编:乐黛云先生 副主编:康式昭、张锺
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
编辑工作往往挤在林昭的,在文科女生宿舍二十七斋二楼宿舍里。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可容纳
八千人的大小餐厅,早就打扫得乾乾净净,大餐厅的中心放著一个直径两
米的大花盆,栽著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弥漫著茉莉、玫瑰的芬
芳!「迎接伟大的一九五七年」金色大字悬挂在主席台上,北大的儿女们
的脸上都蒸腾著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
,嘴唇是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有若黑色。林昭也在
这「无忧之境」里飞翔。
午夜十一时三十分,我们敬爱的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
导来到迎接新年的会堂,登台贺年,舞曲骤停,八千骄子静立。当午夜的
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沸腾了,如群山在笑!这八千子弟高
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马老的习惯用语:「兄弟我!」刚一出口,他的话便被海涛般的掌声
所淹没,这位慈祥、正直、爱国、渊博的长者,他又何曾料到这样坦率、
真诚、融洽、无虑的聚会,以后竟不会再有了!再过五个月,一场史无前
例的「引蛇出洞」之战,会令这八千骄子之中竟有一千五百人中计罹难,
有如林昭这样正直、热忱、赤诚、爱国的青年死于枪杀,更不用详说那一
支被逮捕、被开除、被流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
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衰颓孤苦
。
《红楼》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元旦之晨出版,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
会的大餐厅门前,摆满了《红楼》创刊号,男女生们便围购如堵,林昭与
《红楼》编辑部的发行组组长李鑫一起在那里忙碌著,创刊号的封面上是
一幅木刻图案,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
字。第二页是林庚先生的《红楼》:
红楼你响过五四的钟声
你啊是新诗摇篮旁的心
为什么今天不放声歌唱
让青年越过越觉得年青
《红楼》第二期三月一日出版,责任编辑是林昭和我,直到今天,那
期的二校清样,还收藏在我的书厨里,上面留著林昭校对的手迹。她在《
编后记》里写道:「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
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
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
,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红楼》的第三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拿出
佳作,五月四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很遗憾的是:这期发行了一万册
,今日竟片纸不存!而这期的组诗经过朗诵的艺术处理,成为一出动人的
大型诗朗诵表演,于五月四日的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
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
数千北大儿女在这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一直到夜深,
余烬渐熄。我与林昭离开这里时,晨光熹微,已是五月五日的早晨,星期
日,整个校园静得像己入梦,静极了!
反右运动令她陷入深刻的内心矛盾
五月十九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红楼编辑部春游颐和园,参
加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
锺、林昭和我,林昭带著一个120照相机,拍了许多照片,后来我们每
人都洗印了,但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还夹在我的一册旧书里,
成为《红楼》编委会唯一的一张合影纪念。
那天的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外墙上出现了大字报:《是时候了
》。大字报,红色的纸,在至今知名于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所
有的墙壁上皆糊满,与那春潮带雨般的诗的风、诗的雨并至。酿成了一九
五七年的红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五月十九日这个在北大校史中占有耀眼一页的重要的日子,我们走向
了离散:不仅仅是这个青春群体崩溃了、瓦解了,更重要的是心灵碎裂了
,冰解了!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宣布
开除我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我与李任参加了「右派」刊物《
广场》编委会,我又是那个刊物的主编,真可谓「罪莫大焉」!在那个「
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指出我与李任之罪。连林昭也在这个会上
对我进行了批判,她的话,也如其他编委的话一样,既有当时应付的言语
,也有情动于衷的肺腑之怒,但有一句,我难以忘怀,她说:「我有受骗
的感觉!」│「受骗」,似乎不仅仅是「右派言论」,也包括以往我与她
的交往。林昭是非常爱我们的国家、爱共产党的,解放前,那时她才十五
六岁,就为苏州地下党跑腿、捎信。解放后,尤其是考入北京大学后,她
写了许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文,在校内外的各
种刊物上络绎问世,她惊讶我这样的友人竟是反革命份子!于是说出了发
自内心的痛苦:「我有受骗的感觉!」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距离她被杀
还有两年,我在上海监狱探望她的时候,她还向我提起那次发言,她说:
「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红楼》一共出了三期,再往后怎样了?我已经忘却。因为自一九五
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后,我就与《红楼》无关了!一幅漫画的标题是:「
极右派份子张元勋、李任被清除出《红楼》编辑部!」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
」正在进行,发言者轮流跳上饭厅的餐桌,而我正是他们猛烈攻击的焦点
。正当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著
倚昵多姿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却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顿时
令嘈杂的男声悄然停止: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
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来说吧,他不是
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
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
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甚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
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著!……」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
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
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功夫
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
从那个黑夜: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的那个黑夜,她开始义无反顾
背起了那命运的十字架,走上了一条穷途。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的
迷茫夜色中向我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
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监管中和林昭暗通心曲
从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利,甚么话不说,甚么文也不写,每日仍在那
尘封似铁、霉味袭人的善本书库里静读。那天次日,后来也当了右派的张
玲同学问我:「林昭昨夜喝了多少酒?」我愕然了!她说:「她还醉著,
枕头上全是红色的酒!」据说她一直僵卧两天才坐起来,在桌上的一张破
纸上写了十二个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
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的诗句。她发言的次日,便有一个人写了一
张大字报,题名《致林昭同志》,她开始被置于「左」的火力之下,宣告
了林昭的厄运的开始。
同样是这个「写手」,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诗,如下:
向左!向左!!向左!!! 共和国的公民,
我们守住每一个窗口,举起我们的枪口:向右!向右!!向右!!!
还是这个「写手」,又是张大字报诗,题为:《是甚么时候了?》是
针对我来的。但林昭却是沉默了!她开始在她的班里被批斗。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之后,「右派」已被明判为敌人,学生宿舍楼十
六斋的北墙上写著一排白色大字:「一切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宣
告北京大学反右派运动的开始。这时我已处于被监管状态。有一天,我竟
意外地遇见了林昭,原来她也没走,一直独自躲在宿舍里读线装书,并无
人监管。她告诉我:八月间要到中国青年报社实习,有机会可去找她,实
习完回上海。并留下电话号码。真是喜出望外!没有料到:在这被监管、
被隔离的灰色的七月里,竟得到与林昭会晤的更多机会。
监管并不严,我常到东单十三条中国青年报社去与林昭见面。校内十
八斋东门外有一个电话亭,内设外线电话,免费使用,我几乎每天都要与
林昭通话,她如无事,便约我进城会晤,每次约在下午,回校则已是午夜
。
林昭八月中旬实习结束,即将返沪,临行前的晚上,约我见面,我又
到十三条西口等她,她如约而至,我们一同步行到什刹海,其时天色己黑
,夏日昼长,天才黑即近八点半,这次什刹海的星夜荡舟,今天看来已可
称得上「空前绝后」之举,已是永远失去了的历史。记得她告诉我:编辑
部转来一部长篇小说手稿,题为《青春之歌》,女主角也姓林,也是北大
女学生,也是在学生运动中遭受波折。她说她刚刚看,稿子还要讨论。
林昭离京而去,不再来信,直到中秋节后,竟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又
是意外,信中只言暑期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
,并写诗一首如下: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知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她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而我却还盲目乐观,以为批也批了,
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有了点轻松之感。我给她回
了一封短信,也写了几句诗,聊表思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反右」未歇,全校各系班组在向纵深搜求而挖、
划、批、斗,「右派份子」已成为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
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份子」却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于众目
睽睽之下,随时会被凌辱刁难,而这类行为尤以当时刚刚考进北大的一九
五七级新生最甚!他们没赶上暑期前的反右派斗争,却都有「打落水狗」
的勇敢与兴致,我几次从餐厅走回宿舍的路上,便被这些素不相识的少年
认出堵截,踢掉我手中的搪瓷碗「饿死你这个反革命份子!」而后用脚把
饭碗跺扁,大骂而去。
一九五七年冬,海淀大街的诀别之夜
十二月的一天,偶遇张志华。这个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右派」份子,
也是由于被聘为《广场》编委而身罹于祸的。他告诉我:「林昭回来了!
」于是我希望在校园内也能够遇见她,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十二月二
十一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地从南门走到海淀。在新华书店看书时,
无意地一抬头之间,竟看见林昭也在斜对面看著我!她围著白毛线编织的
长围巾,连头都包著,又戴著口罩,只露著一双眼睛。此时,围在这书刊
展销柜台周围的全是北大学生,我料不会有人认识她,但认识我者确是不
乏其人。林昭转身走出书店,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当然漆黑,
我则随之前行,脚下坎坷,胡同很长,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西
郊收割完的稻田,一片平阔的旷野,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
况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做好被捕的准备!」她说:「你记住
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
:「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
」并也叫我讲清我的青岛家庭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
记于心中。
如此绸缪是准备著一次不测的离散,这预见其实四天之后,即一九五
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我被秘密逮捕,更证明了其必要与正确。那两个
地址乃深深地、暗暗地埋藏在我的记忆里,埋藏了八年,八年之后,已是
一九六六年之初,我从监狱走进劳改农场之后,这心中的暗暗地牢记了八
年的地址终于化作一种「寻觅的程序」,与住于上海的林昭的母亲许宪民
先生取得了联系,但那时林昭已于六年前被捕入狱,而且判为有期徒刑二
十年。
终于夜深,北京海淀西郊的冬夜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
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再多虑
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万籁俱寂,一
片漆黑,但大约百米之外,便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中关村的东西大路
由此通往颐和园方向,在一盏路灯下,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
,我看到她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著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
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到北海医院去体检,星期
三之后再见面。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各自而去。今天想,才
知道一个故事从这儿真正地结束了!
一九六○年划为右派留校劳动
三天之后,即十二月二十五日之清晨,我被传至校办二楼之办公室,
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释放」。按照毛泽
东的「杀、关、管、放」专政守则,我仍留在劳改队继续改造。可以请假
回家探亲,每年只准一次。我终于确定一九六六年的四月底或五月初到上
海探望林昭。我深知探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林昭母亲许宪民
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后接林母信告:「此计
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走向阔别太久的人间之路,从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
阔别九载的青岛,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
人,那是我大嫂;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未休,「一贬再黜」地在山东
的一个穷僻的小城中学教书。他右耳早聩,唯仗左耳偏听人间真假言语。
他现在早已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作为弟弟,我带给他的唯一的「贡献」
,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的屈辱的人生!
他告诉我:「一九六0年的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
,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
管,你正被押,唯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恐中有诈,要求她一张照片。
信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
学医,『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
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夹在里面的那张一寸照片,背面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独自问卢山。
正因为是一本旧日历,当年的抄家才幸免于火,而其他的书皆被付之
一炬,包括那夹在书中的两封林昭的信!他还说,林昭第二封信曾提出要
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考虑她来此处不安全,未表同意,从此,她从此
不再来信。大哥为此内疚。
其实,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更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林昭母亲许宪民告诉我,当逮捕了像我这一类的「极右份子」以后,北
大开始了大规模的处理「右派」行动,林昭由于她那句「组织性与良心的
矛盾」以及与我来往较多,而划作「右派」,她陷在悲愤之中,不吃、不
睡,终日泪流满面,她说她的心在流血!终于在一个夜里吞服大量的安眠
药,被发现,及时抢救,没有死成。于是被认定她在对抗,「态度恶劣」
!宣布加重对她的处分:劳教三年。
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
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
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
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
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奏效,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
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
◆加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