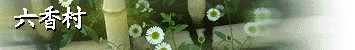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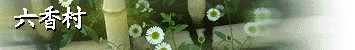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
| |
------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社会批判
--------------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为人类的解放过程给出了一个历史哲学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批判理解作尼采对于那盲目乐观主义和前进信仰的批判的继续,--作为“那苏格拉底式的”的无限扩张的产物的盲目乐观主义和前进信仰。
借助于那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人达到了对于自然的统治。在最终理性成为了人用来统治自然的工具。那本来要将人类引向自由的运作过程,现在却渴望“非自由”,因为在人要取得对于自然的绝对统治的同时,人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这运作过程不再运作于将人类从人对物质关系的盲目依赖之中解放来,相反,它自身成为了一种控制和压迫的工具。在知识上的进步于是导致了更进一步的不自由。它一步步地以理性的名义将那些单独的、特别的、个体的东西全部割削掉。于是形成一种垄断:“认识”的合法名字叫做“那科学的”;哲学成为了对于科学的游戏规则的表述。这样,思想被纯粹的观察、分类和运算取代;那被清洗去了所有陌生物的世界成为了纯粹的“事态们的组合”(“Die Welt ist die Gesamtheit der Tatsache...”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我们能够看见启蒙的理论性的彻底破产。那本来要将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的东西自身堕落于神话,--那关于“事件”的神话。在启蒙所具的理念(诸如自由、公正和人本)成为社会性的实践之前,启蒙自己已经开始消灭起这些理念了。
这样,我们能够在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启蒙之辩证法”中看见一种当代版本的尼采式批判,--那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于那“由苏格拉底式的理论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批判。在尼采呼唤那神话中悲剧的英雄时,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则指出了奥德修斯的智慧中的象征--人通过将自己搞成“没有人”来保存自己(注脚:奥德修斯被巨人Polyphem俘获,巨人问奥德修斯的名字,奥德修斯说“我的名字叫‘没有人’”。后来奥德修斯搞瞎了巨人的眼睛,于是巨人大喊,求救于同类:“没有人伤害了我”。其它巨人听见叫喊后想,既然是没有人伤害了他,那么他平安无恙,我们不用去帮他了。作为“没有人”、作为一种乌有,奥德修斯得以维持自己的生命),人类对于自身的维持建立在将自己虚无化之上。而比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于理性崇拜和娱乐文化(完成了退化的的歌剧文化)蔑视,我们也能够在“启蒙之辩证法”中阅读到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
正如尼采,阿多诺对艺术也有着极高的估价。“美学理论”是阿多诺的最后的巨著。阿多诺分析了,在哲学之外,艺术是“那坍塌的世界”之中唯一继续站立着的领域。阿多诺特别关注现代艺术(比如,卡夫卡和贝克特),并且试图借助于本真艺术对于“不可知”的有意识追求来把握那荒诞和否定的东西。就象哲学一样,艺术被视作同时是和社会相对立和相联系的。在一个“无邪”已经不再存在的世界之中,哲学和艺术应当是以一种极端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不合作。作为真理的家园,艺术对于阿多诺来说总是社会的对立面:在它有着区分不同于经验现实及其社会性作用关系的特征的同时,它也参与于这个经验现实。艺术是同时自律的和社会事实(fait social)的。艺术的这两种实在总是相互覆盖和对立着,而从不直接地相互同一。那决定性的标准在于,艺术作品是否能够将那来自经验现实的实在取入自身而在艺术自身的媒介中将之转化,以至艺术自身的形式语言成为那对于本来是隐藏着的社会化的本质的表达。
〔我自己的对于“自然-人-文化”的理解也是得到了阿多诺的启发而得出的。这里,联系到尼采对于超人的呼唤,我也给出一个短小的描述--如果人们把阿玻罗理解为“文化的神”,而把巴库斯(狄欧奈苏斯)视作“自然(前文化)的神”,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巴库斯没有阿玻罗的化身,那么它就迷失在浑沌之中,这样,人就是自然的奴隶,因此就有了“西伦Silen的民间智慧”;而当那阿玻罗的被从那狄欧奈苏斯的那里割裂开,当巴库斯不再隐身于那阿玻罗的背后,这时,那阿玻罗的就变得僵化,于是人就迷失为文化的奴隶(比如说,被传统奴役),因此人开始有了末日恐惧。只有在这两个神在人身上达成和谐的时候,人才是健康的,而能够因此创造价值,创造他的文化的内容而使得文化得以发展。
在现代社会,人应当成为文化的主人。阿多诺认为,人的文化、人的社会因为人对于自然的统治而成为了“第二自然”。我能够看见从前亚里士多德赋予自然的那种“目的论”被人逐步地赋予了文化,而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文化这样获取了它的自身目的。从前人类处在自然的“暴政”之下,而为了将自己从自然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人开始了启蒙,开始积累自己的文化;然而启蒙节目却并非象人在预先想象的那样理性,人刚刚脱离自然的“暴政”,便马上陷入文化的“暴政”。阿多诺的概念是“人对于自然的统治”,而我宁可将这个概念改写为“人的文化对于内在和外在自然的统治”(内在自然,亦即,人的本性);而现代人的可悲正是在于他成为了自己的文化的奴隶。让我们为此而呼唤查拉图斯特拉:最高的顶点上是生命意志;超人和谐于自身的人格而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超人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文化的奴隶。因此,不仅仅是在尼采的时代,也同样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超人的人格。这便是我将在文本的最后谈及尼采的“超人”概念的原因了。〕
--------
洞察中国当代的中西文化之争
---------------
在尼采之前的时代的欧洲要么是那乐观的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人通过理性能够达到一切;要么是那悲观的罗曼蒂克者,他们在心灵流放之中寻找逃避并且追求那原始时代的或者东方的精神。而在我们的时代,同样有着那些一心想将一种“立法者”的身份赋予“那科学的”的新实证主义者,和那流浪在新时代的关于“本原传统”或者“东方传统”的梦想中的新罗曼蒂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能够将解释学和社会批判看作是一种对于那两类新形式的乐观和悲观主义的反击。
我所阅读的关于现代西方或者东方的文化理解或者艺术理解的书籍并不多,而通过翻译和介绍,我大致地了解到这些西方的思潮是怎样被歪曲和没有被歪曲地涌进中国的,--它们被翻译,并且绝大部分被曲解和误读。可能翻译者和介绍者们在作出他们的努力时怀着一个好的愿望,因为人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些西方的思想来推翻那僵化了的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权威。然而,一个没有得到解放的主观是无法真正对那些进口的文化“货品”进行正确的使用的。而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曾经使得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知识领域得到蓬勃发展;之后在中国出现的共产主义信仰崩溃则为中国带来了一种可口可乐文化和新权威主义的混合物,--这个怪胎恰恰是盲目实证主义破产之后的必然产物。在西方世界试图借助于诸如阿多诺、本杰明、德里达、福科、荣格等等的理论的启示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的同时,这些理论也进入了中国,通过意识形态化的误读而被用于强化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通过对于尼采美学观点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所有“被误读的西方思想”的泛滥进行回击。
如果我们把尼采的狄欧奈苏斯和阿玻罗视作文化发展的两种本质驱动力,那么,我们在以这种解释来观察中国文化史的时候能够看见,事实上中国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狄欧奈苏斯的元素),在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主流的民族正教之后,已经完全被从中国的文化之中割除出去了(所以在中国两千年的文化史中没有出现过任何真正的人文发展)。因此在中国只剩下了僵化的教条;也是因此那中国本土的道家和移民到中国的佛家只能存在于儒家给出的许可之下,并不得不接受相当一部分儒家教义来使得自己在中国文化中的存在“合法化”,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其他文化形式只能在中国社会中以一种亚文化的方式生存。当然,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中国文化史,真正引起我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文化现象。
在共产主义思想和其他西方思潮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文化核心是一种僵化的权威主义,而这种权威主义恰恰是移植共产主义化身的理想土壤。然后,共产主义进入了中国并且马上在中国僵化为权威主义--一种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所以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其实是一种披着西方科学主义外衣而具备中国民族灵魂的权威主义。在这种权威主义之下人们受教而不思考。而在之后,共产主义在中国失去了信用,于是人们在“寻根”或者“重归传统”的口号之下开始抛弃那西式的(共产主义)外衣;然而西方可口可乐文化却马上和中国的权威主义汇成一体,同时,中国当局为了维护那崩溃了的权威,在接收西方文化中的垃圾部分(金元文化、麦当劳可口可乐文化等等)却有着抵制西方文化中的人文启蒙部分的需要,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马上重新填补了那塌陷的权威的位置;而中国主流文化用来抵制人文启蒙的工具则恰恰是这些被曲解和误读了(乃至某些无须歪曲的)的同样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后现代”理论。一些西方的现代罗曼蒂克理论可以完全地成为中国和新加坡的新权威主义社会制度的狡辩理论,比如说,人们能够使用那完整版本的communitarianism来为那旧的传统的“东方价值”作辩护;人们也能够使用那被误读的福科来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作辩护;人们也能够使用那被曲解了的荣格来抵制现代社会。在人们把西方的启蒙批判理解为反启蒙而囫囵吞枣地把西方的新蒙昧主义(communitarianism可以理解为一种后现代的新蒙昧主义)引进中国的时候,难免使得这本身处于价值虚无主义状态的中国思想领域更深地陷入灾难性的智力混乱。
也许人们会将这些现象视作纯粹的政治统治术而不值得将之作为哲学批判的对象。然而,既然这些现象已经骚扰了我们太久而我自己又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将之认真对待,虽然西方人可能会认为不值得化功夫来回击这些蛊惑性的东西。这里,我并不想展开论题来论证这些理论,诸如尼采的、法兰克福学派或者荣格的理论,是不是真理;我的努力在于指出那许多源自这些理论而被用于东方意识形态辩护的概念在事实上是被歪曲了的。
在荣格那里有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概念,然而到了那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使用荣格理论的人们那里,这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内涵被曲解为民族的“集体意识”,或者那表面的民族传统,因而荣格的心理学成为了那用来“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有力武器”;而在事实上,荣格的本原的集体潜意识可以是一种创造性的驱动力,但是那作为意识形态的所谓的“民族集体意识”或者传统则是僵化的准则,是一种腐朽的影形表象。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费耶阿本德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发现了“‘西方思想’远远不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唯一顶峰”(注脚: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但是这并不就意味了我们因此而去把那种腐朽的东西视作“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唯一顶峰”。
阿多诺批判了科学成为一种统治和精神立法的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了我们就因此而应当让那旧有的、无根据的习俗重新成为决定一切的权威。从这种意义上看,这里所谈及的就不仅仅是“人一生只能作一次处女”的问题,而且也牵涉到关于那刺激生命的驱动力是否具有活力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尼采:生存的原始源泉是那藏身于所有(可能的)影形表象背面的原始现实,而不是某一种陈旧的被否定了的影形表象;就是说,“新的”或者“现代的”启蒙后的文化表象(诸如科学)不是世界的本质真相,而那“陈旧的”或者古老的文化表象(诸如图腾和宗教等)则更不是世界的本质真相,--世界的本质真相是一切表象背面的原始本真;神话的精神是那将神话中的戏剧性故事驱向观众的驱动力,而不是对于神话中故事内容的信仰,这就是说,那对于原始价值的盲目迷信并不比现代盲目的进步信仰更可取。宣告“科学宗教”的破产并不意味了我们必须重新钻回那些陈旧的宗教;通过现代的方式无法解决现代的社会冲突并不意味了我们必须找回那些传统、那些腐朽了的陈旧价值来欺骗我们自己。尼采的超人为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人不应当成为那由人创造出的价值的奴隶;在价值崩溃的时候,以更陈腐的虚假价值来代替陈腐的虚假价值是徒劳的。这时人的工作应当是创造性工作,而那超人的精神通过自我超越而为自己创造出那能够让我们在之中找到新价值的文化。
所以,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的关键在于,我们既不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奴隶,也不应当成为西方进口文化的奴隶,我们应当是文化的主人。我们应当为我们自己创造更新的文化。
摘自京不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
京不特
------------------
但是他们终于把王一梁送去了劳改农场。
摘自王一梁母亲二零零零年四月三十日的信:
“现在天气日渐热起来,他所穿的衣被都是冬天的,当时在看守所,我每星期六送去一些食品。原以为去了大丰,就可接见,因此热天的衣服被子都没送去。再说已三个月了,他的日用品牙膏肥皂也该用光了,他身上又无分文。劳教是改造思想……人要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冬天要穿御寒的衣被,夏天要穿凉快的衣物,三个月后正值高温之下,刚去的三天是严寒,不让我们送衣被,现在快夏天了,又不叫我们送东西……总不能坐视到七月底,那怕争取只送东西不见人。请大家想想办法托托人……
看来他的命运是如此安排,我们都没法拯救他。现在只有好好改造,接受教育……现在只好认命,还抱一些幻想能提早释放,前阶段的幻想我彻底消灭了,请那些朋友也就算了,就等待二年……”
------------------
◆加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