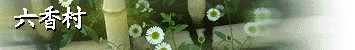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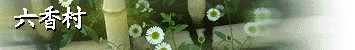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
| |
摘自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京不特给友人信:
对于文化(或者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晦涩东西我总是持猜疑的态度的。过去在读一些哲学书的时候,常常为自己不懂得许多术语的含义而感到难过,——因为我在术语方面的无知我常常在阅读上无法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断定,理解许多术语的含义对于那会在书中读到这些术语的人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一点点开始地理解了这些哲学术语含义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我和人们谈话的时候,人的基本常识告诉我:如果我想告诉对方我是怎么想的话,就应当使用对方能够听得懂的词汇。如果对方对我所说的内容一知半解的话,我所进行的“思想交流”就是一个不很成功的交流;如果对方彻底听不懂,那么,这交流就是彻底的失败。而我表达自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失败的交流,于是,如果谈话的对方不懂哲学术语(这并不意味了我比他更聪明或者博学),那么我就不该使用术语,即使是迫不得已非用不可,我也必须把所用术语的定义说明白。否则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表达能力的人(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表达能力的写作者)。但是,术语不是坏事,它为那些理解术语的人们相互间的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如说,哲学术语在哲学系里是人们以直接的途径最省略地得出结论时所使用地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为了避免之后的繁复和费时间,人们在之先学会了(乃至定义了)这些术语。对于使用这些术语来交流的人们,术语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意义上的晦涩,因为这些术语对于思想交流的双方都是在含义上很清晰的概念。但是,如果是一篇写给“不懂术语的读者”看的文章,如果作者在文章里既使用大量读者不懂的术语,又拒绝对术语意义给出解释,那就是不可取的。但,还有一种“晦涩”,它是使我对写作晦涩的人有猜疑的根本原因。有一次我读了一篇用很多佛教术语写的一篇关于东方文化的文章,我仔细读了之后,发现这些术语在文章中的完全不再具有他们本来的含义,这样一来,不仅是不懂这些术语的人看不懂他的文章,就是懂术语的人也不知道他想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作者就是在写一篇让读者摸不到头脑的文章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自己知道不知道这些术语的意义呢?
这里有一个幽默。“一个亚洲的旅行者对他的同胞说:我从欧洲听了一个很动人的神话,它有着你从来体味到过的那种伟大和美好,你不听它的话,你在知识上根本长进不了。同胞答:那么叙述它。旅行者说:不行,我不能用亚洲的语言来讲述,因为这个神话是被人用印欧语系中的语言来传诵的,亚洲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出它的神韵来。同胞说:那么,你用英语叙述吧。旅行者说:不行,英语不是你的母语,用英语对你讲的话,你根本理解不了它的神韵。同胞答:那么就算了,就不讲吧。旅行者说:所以我说你不长进呢,你居然放弃得到一个精英可能给予你指点;你一定要听;除了英语,你还懂什么语言?同胞答:德语、法语、俄语和希腊语。旅行者问:你不懂拉丁语么?同胞答:不懂。旅行者说:那么,我就用拉丁语对你叙述吧。”
批评是说理的文体;如果在说理的文体中不知所云,文体的意义就没有了,那么批评能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说:“这些诗歌很wettntr。”有人这时问我:“wettntr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而我回答“wettntr就是指rtntetwn。”这样,从无意义到无意义,昏过去!
------------------
------------------
------------------
但是他们终于把王一梁送去了劳改农场。
摘自王一梁母亲二零零零年四月三十日的信:
“现在天气日渐热起来,他所穿的衣被都是冬天的,当时在看守所,我每星期六送去一些食品。原以为去了大丰,就可接见,因此热天的衣服被子都没送去。再说已三个月了,他的日用品牙膏肥皂也该用光了,他身上又无分文。劳教是改造思想……人要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冬天要穿御寒的衣被,夏天要穿凉快的衣物,三个月后正值高温之下,刚去的三天是严寒,不让我们送衣被,现在快夏天了,又不叫我们送东西……总不能坐视到七月底,那怕争取只送东西不见人。请大家想想办法托托人……
看来他的命运是如此安排,我们都没法拯救他。现在只有好好改造,接受教育……现在只好认命,还抱一些幻想能提早释放,前阶段的幻想我彻底消灭了,请那些朋友也就算了,就等待二年……”
------------------
◆加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