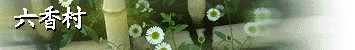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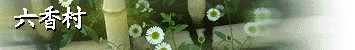 |
| |
摘自京不特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给王一梁的信(里纪是王一梁的笔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亲爱的里纪,你好: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懒惰,我不一定能够完成你对我所要求的工作了,所以我在这里寄上《明镜》中关于德国亚文化的文章。当然这是德语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德语必读文。我现在是处在考试期间,所以我不敢说我能按时完成此文章的翻译工作。我之所以说“因懒惰”,则是因为事实上我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在丹麦的各个地方进行着关于“强调个体人的权利在东方之重要性”的讲演,每当我收到了让我去进行讲演的邀请的时侯,我便马上忘记了“这是在考试阶段”。而这些讲演对于我的思考也是极有好处的,因为每一次讲演都会有许多听众向我提出我所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则促使我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我的思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豁然开朗”,这使我欣欣然。但是,讲演之后我所想到的第一工作是,我应当首先把考试应付过去。英德语的笔试已过,等待我的是英德法的口试,我得去一趟德国。而考试之后,孟浪将来欧洲,我要考虑的是安排我们的见面。然后是搬家的问题。所以,从现在到八月,一系列“计划”已经把我的日子排得极满(八月份的一个讲演也几乎在前天被定了下来)。因此这一段时间我是被这些“日程”囚禁的,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你所要求的工作了。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元素:人权。我从前一直是忽略了这个词的深远意义的,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它是当今世界上所有冲突问题的关键。我过去在提到这个词的时侯从来没有想现在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过它的本原意义。人们常常用那“少数服从多数”来曲解“民主”的意义,然而只要人权在场,“民主”就不可能被曲解成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了。所有这个词不在场的地方,就是暴政、独裁、宗教狂热的暴力、种族歧视、恐怖、消灭个性的绝对秩序和其他不公正。我想,你是明白我的意思的。考虑到你应当收到我的这封信,我在这里就不再多展开这个问题了。尖矛人民在没有觉悟到他们自己人权的同时往往还随着那暴政去剥夺他人的人权,所以如果不启蒙人民在这一点上的意识,任何所谓的革命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只是以新的暴政取代旧的暴政而已。所以个体人的革命应当是唤醒每个人,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所应当拥有的人权,也使他们尊重他人所应当拥有的人权。我们多年来所摸索的,到今天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这也是为什么,到了根本上,暴政所畏惧的不是布莱希特,不是萨特,更不是海涅和歌德,而是卡夫卡和伯尔。
我们依旧没有权利去为人们建立任何“准则”,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作为一个中国独立个体人作家的义务:去告诉人们,“每一个个人是有着那任何他人、集团、国家和制度所无权来剥夺的人权;而多少年来某些人、集团、国家和制度一直在一直在侵犯和剥夺着每一个个人所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我已经太久停止写作了,但是我知道我将开始我的写作,不仅是因为诱惑,而也是因为作为一个人,必须去履行他命中注定的义务。我对老不特说,现在我是快乐的。是的,我是快乐的,因为我重新发现了那在我的命运中等待着我去为之努力的使命。“个人啊,去认识你的权利吧!个人呵,每一个其他个人都有着和你一样的权利,那也是你应当尊重的啊!”于是也让我们把“权利”本身这东西弄得更清晰吧。那么多东西在等待着我去思考和写,那么多东西在等待着我向这个世界表达,我当然是快乐的了。而在这个时侯,哲学成为了帮助我理清思路的一样工具,我读哲学。但是,我应当把垃圾工人或者邮递员等职业作为的日常职业。因为,以我的体力劳动,以我为这个世界作出的具体贡献,我可以来换取报酬,但是我没有以“思考者”的身份向这个世界去索取的权利。这个世界不欠我们什么,独立思考是每一个独立个人的义务,写作或者呐喊则是诗人、哲人和独立作家的命运。如果我们把命运当成了我们的职业,那么我们就是在堕落。如果我因为我的无能而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谋生的职业,我也不能把写作和思考当做职业;在我得到世界所给予我的一切不是由职业的报酬而换得的东西是,我只有感恩。我现在在丹麦的心情和那时在我去云南前得到耗力克的帮助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在嘴上无话可说,但是在心里是无比的感恩;因为谁也没有“欠”我这些,也没有谁“应当”给我这些,但是因为爱(或者博爱)我得到了这些,如果我不感恩,那么我的灵魂就是在犯罪,如果我不感恩,我也就不配称自己为“独立个体人”。事实上,你也是和我一样的,我们心中无边的感恩是我们无法用话语来表达的;因为我知道,即使是在你处在酒精之中,你也没有让自己去为胃写作。我们的感恩之心也使得我们没有辜负这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着爱。宁可不写作,也不去用我们的笔使得我们的灵魂犯罪(最大的犯罪莫过于明知恶而去弘扬恶了,莫过于御用文人的为虎作伥的行径了),所以我们在感恩的同时也有理由为我们自己骄傲了。我们是那么健康!即使实在困境中、在迷惘的时侯,我们也健康。
就象从前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周围遇到人性中的许多弱点,诸如诿过、嫉妒、软弱、自大,等等,那么,亲爱的里纪,让我们时时相互提醒:既要保持我们的宽容又要让我们顺从人和人之间的缘份原理。我们是在以灵魂对世界交往着呵,强者更多地期待自己不具这些弱点,而去原谅、而去宽容处在周围的这些弱点。如果我们总是对环境有期待,那么是环境强过我们了,只有在我不是对环境而只是对自己有期待的时侯,才是我们强过环境的时侯。我还记得你的“我在故亚文化在”的豪气。我是个独处者,所以不很艰难,但是你却不得不和一种环境朝夕相处,所以比我艰巨得多。我们的命运。
我真想你能在欧洲,因为我现在渴望那彻夜长谈式的交流,交流对象没有别人可以取代。
好了,我不多写了。随信也把德语课文寄上。
你的忠实朋友
不特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七日
------------------
------------------
------------------
但是他们终于把王一梁送去了劳改农场。
摘自王一梁母亲二零零零年四月三十日的信:
“现在天气日渐热起来,他所穿的衣被都是冬天的,当时在看守所,我每星期六送去一些食品。原以为去了大丰,就可接见,因此热天的衣服被子都没送去。再说已三个月了,他的日用品牙膏肥皂也该用光了,他身上又无分文。劳教是改造思想……人要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冬天要穿御寒的衣被,夏天要穿凉快的衣物,三个月后正值高温之下,刚去的三天是严寒,不让我们送衣被,现在快夏天了,又不叫我们送东西……总不能坐视到七月底,那怕争取只送东西不见人。请大家想想办法托托人……
看来他的命运是如此安排,我们都没法拯救他。现在只有好好改造,接受教育……现在只好认命,还抱一些幻想能提早释放,前阶段的幻想我彻底消灭了,请那些朋友也就算了,就等待二年……”
------------------
◆加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