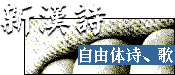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呼兰|康金井|两个奶奶|林家|钻石王老五|传说与故事|打碗花|
呼兰
一盒火柴,就能让我想起呼兰
它的名字带有一股刺鼻的硫磺味
从康金井乘火车去哈尔滨
我多次途经县城,却没有到城里去转悠
因此,它的模样就像受潮的火柴杆
在记忆中擦不出火花。只有一次
在梦里,我冒冒失失地抵达过县城
一个卖冻梨的老汉对我说
"这就是呼兰,不信你冲河水喊两嗓子,
它会冒出蓝烟。"我捧着冻梨直打冷颤
手脚麻木,满嘴哈气往外蹿
小时候,吃冻梨先用凉水拔一下
等梨表脱掉一层透明的玉衣
再下口。呼兰不会长得像冻梨吧
萧红姐姐、萧红阿姨、萧红奶奶
不会像梨皮一样难看。长岛在电话里
跟我说,他去过萧红故居
看了呼兰河,可我却不能跟他谈论
有关呼兰的轶事,我用钢笔把它写进祖籍
一栏。我确实沾了一点萧红的光,因此
有些脸红,本来嘛,我的脸就像黑土地
一样黑里透红,并影响到了我的女儿
两年前,我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当长长的暗夜,威逼一个少年
成熟、迅速衰老的时候,我掏出一根
火柴,划亮整个县城,她的女儿萧红
用一双审视的眼睛望着我。"
除此之外,我还能对呼兰说些什么呢2000.9.10
康金井
八卦街像一只风筝,在1:1200万
比例尺的地图上看不到它的影子
呼兰河更远,因萧红而流经三十年代
对我来说,康金井只是一个站台
南来北往的火车解开过我不同的衣襟
10岁之前,我睡在路基东面,红色
车轮肆无忌惮地碾过我的胸膛
将坦克和大炮运往边界
把红松和水曲柳运往南方七十年代初,一列货车翻下路基
大片的玉米被压倒,那时,我还
没有成熟,好奇心仅限于司机或司炉
怎样跑下车头到玉米地撒尿,然后
像熊瞎子一样掰玉米,到炉火里
烧烤,像我在灶火旁烤熟焦黄的土豆
一样,没有未来和理想,司机只管
开车,轧断玉米和农民的腿,我只管
做梦、尿床、惊醒,就像今天
我从不把居住留地称作故乡2000.9.9
两个奶奶
1."带你长大的奶奶是个萨满。"
三年前,父亲无意中说出这句话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快炸了
那时,破除迷信,二奶堵严了窗门
偷偷在夜里跳大神,有几次
惊醒,我大气不敢出,真的吓坏了
油灯昏暗,只有一丝光
另一个妇女一副虔诚的模样二奶振振有词,我却一个字也听不清
一个字也听不清,否则我不会
遗憾,我失去了一个近在咫尺的传统
其实,我继承它的可能性很小,奶奶是满
我是汉,我们之间除了亲情
总还有禁忌。二爷过世后
二奶就改嫁了,改嫁前她杀了一头猪
骂我和弟弟是白眼狼白眼狼是什么呀,什么呀?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意识模糊,没有
不良反映,现在,我明白了,奶奶
已在外省度过了20年孤独的时光
她死前会念叨我的乳名吗?
"小东、小东、小东……"一个萨满
将咒语放入我幼小的胸膛,呵,胸膛
是您呼吸的坟墓吗?它安静、迷信
伴我走过20年的迷惘,在每个
失去信任的暗夜,我多想拨亮
油灯,看您跳大神之舞2.
走了一个萨满的奶奶
还有一个平原般坦荡的奶奶
童年蒙昧的油灯,还有人为我拨亮
黑土般厚实的火炕上,奶奶盘腿而坐
随手卷一支纸烟或是嗑瓜子
我和弟弟小狗一样围在她身旁当时家里除了课本和马列毛的东西
其他的书全都烧光,可奶奶肚子里的
闲话似松花江水在冰层下流淌
父亲有时会严肃地对奶奶说
"您老给孩子讲这些东西可不好"
可奶奶并不听他的,谁能改变一个
乡下老太太的信仰?多么可笑呵
一个读过很多书,并在书的扉页上写
"学而后知不足"的人,并没有成为我的
启蒙老师,反而是大字不识、裹小脚走路
乡村的奶奶,启开了我混沌的茅塞这些杂芜的闲话,是奶奶道听途说的
偶得,她默记于心,并口授于我
于是,我就有了王小二砍柴的愿望
有了男扮女装跟穆桂英出征的荒唐
以及乡村流浪汉式的幽默和无常
20岁后,我痛哭的方向是北方
我只哭我的奶奶,我恨自己不能到
她的坟头上去烧纸,我嫉妒那些
清明节扫墓的人群,真的,我想带着
我的书,烧给她看,虽然我是个
无神论者,可还是想把
文字的骨肉一笔一画烧给她奶奶给我讲过的故事大多已经忘记
只有这个与死亡有关的梦依然清晰:
那是一个不确定的场所,两个听差
领着奶奶沉入回旋的廊底,奶奶说
好像是马厩旁,她在梦中嗅到了马粪的
草香,一根金色的柱子栓住她乌黑的
辫子(梦中她可能还是个姑娘)
不大一会儿,两个听差的不带一丝尘土
走进红漆的大门,等到他们出来
她才看清是两个长着驴头、马面的人
喊了一声:"抓错了,主人不想见你。"
奶奶在油灯下重复这个梦
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感激,她对我说
一旦听到主人的召唤,她就回去2000.9.11 2:33
林家
林家村以我家族的姓氏命名
父亲说早先还叫过林家窝棚
文革时改名红旗,没竖多久
就倒了,习惯战胜了
见异思迁的热情我看见与我同姓的地主的儿子
天天到各家各户挑大粪
开忆苦思甜大会时,他低着头
立在板凳上一声不吭,没脾气
对人毕恭毕敬,村民说他
心里有一本变天账。但批判
并不激烈,除了说吃就是说穿
有点像巴甫诺夫的条件反射最让人激动的还是游大街
给地主、右派、小偷、破鞋
脖子上挂一块牌子,头上糊一顶
纸帽,煞是好看,年轻人
鸣锣开道,像是过愚人节或
动物狂欢节,除了过年
乡村没啥节日,13岁
我离开林家,再没回去过2000.9.10
钻石王老五
井沿上住着王老五,他最爱
蹲在井台上发愣,披黑棉袄
像一块巨型土坷垃,死活也不肯
开化,他的固执是出了名的
谁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能想什么,想媳妇呗。"
我从没见过他的婆娘
也没见过他下地干活,他侄子是村支书
谁敢惹他呀。反正没人给他焐炕头
他在哪儿都是凉的,比井里的水还凉我在井里拔过黄瓜,又凉又脆口
他想媳妇的滋味也是这样吧
从太阳升起到落下,王老五
像钻石一样一动不动,水井丁冬的
声音在他的心里漾开他侄子为啥不给他找个婆娘
我也不知道,可能没有合适的
也可能他不想要,他一天到晚守着
井台,就是在等水井一样清冽的
女人,带着丁冬的耳环走上来我没有更多证据证明这猜想是对的:
他爱的女人早年投井自杀了?
他年轻时在井台上看中一个打水的女子
那女子却嫁到了外村?他一直在等
一个人在井台上出现?可能地点不对村里总共有四五口井,每口井咸甜不同
丁冬声也不一样。我想跟他说,王五叔
你每天换一口井蹲着,可能会好些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其他几口井
都填住,这样就可以瓮中捉鳖了
传说与故事
1.村里有一位业余猎户姓李
打鸟也打野鸡,还喜欢捕杀
黄鼠狼和狐狸,下猎套
埋铗子,无所不精
有一天,他从外面捉回一只狐狸
村里的大人、小孩
都来看热闹,将他家的窗户
堵了个严严实实
那只狐狸在他家的炕上
不停地转圈,临死前
两眼泪花落满炕席
猎户一边磨刀,一边嘀咕
上好的皮毛,卖个
几十块钱没问题。狐狸哀求的
眼神越来越黯淡,利刃的
寒光剥开它厚厚的毛皮
第二年夏天,猎户的两个儿子
淹死在村东的大水坑里
按老人的说法,一只狐狸
有四条腿,因此,报复的
数字也是相等的2.
我在平原上只见过一次
狐狸,那是我的右眼被玉米茬
刺伤的地方,一只火狐
拖着华彩的长尾向东方逃去
许多人放出院子里的狗
企图追上它,大呼小叫的村民
冲出了家门或爬上了梯子
我只能用一只眼注视火狐卷起
的烟尘,一会儿功夫,几只狗
被火狐施放的烟幕弹薰了回来
家狗那能有狐狸聪明,光是
那条尾巴就能逢凶化吉
奶奶说,狐狸刁走了一个孩子
的右眼(我不相信),三天后
它将还给那个孩子一只
幼狐的眼睛,这可是真的2000、9.25
打碗花
眼睛像沼泽,开着一束花
我曾试探着采撷,又深恐
不能自拔。这是常见的乡
野风景,饮烟袅袅之地
也是我儿时玩耍的水洼
那些溢于水面的劣质油花
泛起泡沫,呛人流出终生
的泪水,姑姑就在这层油
花后面张望,总也数不清
锅台上的星星,儿女们拖
着扫帚星的尾巴长大,她
每天唱:"摘了朵打碗花"大手大脚,本可以闯天下
可是她没走,她说一根肋
骨动,房梁就得塌。每天
给猪一盆食、鸡一把米
锅一瓢水、摘朵打碗花
你也许纳闷,为什么摘的
是打碗花,而不是豌豆花
韭菜花、其他花?17岁那
年,她从地里回来,随手
采了一朵,刚进屋,就看
见耍钱的二爷领个陌生的
小男人回家。从此,姑姑
就分不清落在老槐树上的
是喜鹊还是乌鸦,她每天
都站在纸糊的窗格前唱:
"……摘了一朵打碗花。"2000.12.2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