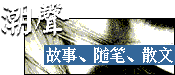坦 白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没有眼睛的母亲对眼睛刻骨的在乎。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与她交流过,但我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永浴黑暗,再受她一样的苦。
之一:我是盲母会说话的竹杖
35年前的阴历九月廿日,我从19岁盲母的身体里出来,张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的存在,让不谙世事的母亲多了一些生着的平静与从容。
四年后二弟出生时闭着眼,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直到今天二弟的眼都没有像母亲期待的那样睁开,他成了母亲永远放心不下的牵挂。
二弟出生后又过了四年,已经八岁的我放学回家,看见炕的中央躺着刚刚出生的三弟。我爬上炕仔细端详了一番这个我们家崭新的成员,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怪怪的味道。三弟的脑门上有一圈明显的阶痕,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所有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于是我放心地吃过午饭继续上学。
后来我抱着三弟在巷子里玩,为母亲收生的邻居老太婆看见了,指着三弟说:“瞧这孩子的眼睛多大!他降生那一瞬,爱爱还问我孩子有没有眼睛。并坚决要求‘如果孩子没有眼睛,就将他投进便盆里’哪!”
爱爱是我母亲的名字。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我的心受到的震撼至今都让我隐隐作痛。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没有眼睛的母亲对眼睛刻骨的在乎。尽管我从来都没有与她交流过,但我知道: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要永浴黑暗,再受她一样的苦。
四弟出生后我已经能干一些家务了。父亲常常是从中学的课堂上把我唤回家,让我给月中的母亲擀面条。那时候白面少,面条要掺杂大半的豆面,擀好也不容易,但我却擀得很好。
我的懦弱的性格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我的童年生活。我记得三年级时一个中年女老师用浓重的方言教我们一首诗:“雪皑皑,野茫茫……”,我的邻居又是同学的王建明就改编成:“瞎爱爱,眼盲盲……”来嘲笑我。
今天想来当年也只有十岁的王建明未必就是要使坏。他们只是用这种方式寻找自己的乐趣。但他们的乐趣建立在了对我的伤害之上,我的脆弱的灵魂一直振颤到今天。
到30岁的时候王建明已经学会了拉拉面,在小城车站的寒风里呼喊里着:“拉面,大碗拉面……”来谋得生活。有几年我经常出入小城,看见王建明的机会也有过几次,偶尔也打个招呼。
我回小城结婚的时候王建明来为客人拉拉面。他看见我们从外地带了摄像的,就悄悄的问我:“拍了电视,在哪个频道播?”
30岁以后我与许多童年时代的小伙伴们相遇了,我或许会有一点点优越感。比如当年副县长的儿子、我们小学年代的班长王新权在今天小城的重要部门任职,一次回乡碰上了他,他就夸我在报纸上的几篇文章写得不错,还会用自行车载我一段路。而在20年前我大概是不会与他怎么来往的。我深深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压力,因为母亲的缺陷,我多了一些谨慎。
假如说我身上会有一丝一毫忍辱负重的品质的话,这不仅是自信的结果,更是自卑的结果。面对王建明们蹦跳着高喊:“瞎爱爱,眼盲盲……”,我从来没有想过反抗。我面对的势力是何其强大,我又没有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那些最最无助的遭受伤害的日子里,我只能默默地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
尽管在许多年里我不愿意与人们谈论有关眼睛的话题,尤其怕听到“瞎眼”这个词,但我一直做着盲母的竹杖却从来没有羞惭过。直到三弟可以拉着母亲的衣角陪她上街了,我才从母亲的身边解放出来。那已经是我十几岁以后的事,上了中学,功课似乎也紧了,陪母亲就逐渐的少了。
可我多年里是母亲会说话的竹杖啊!我终日牵着母亲的手在小城我们必须去的地方出入。比如我们把从灶台上焙干的南瓜籽拿到收购站去找老尹,就会换得几块钱。我拉着母亲去买鞭炮的地方就可买到草纸。为什么母亲有一段时间要用草纸?那时候我似乎知道,也似乎不知道。懵懵懂懂的童年懵懵懂懂地就过去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六一”的衣服》小文章,是讲做母亲竹杖时期的事的:
我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经常有新衣穿。记忆里似乎除了春节,就是只有到了“六一”前夕,盲母才为我们兄弟几个张罗新衣服。
妈妈看不见,我就领着她到百货大楼的布料柜台前,我将我能看到的适合我们兄弟穿的花色讲给妈妈,她或者斟酌一番,或者让我拿主意,先选好了布。然后,再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可以得到帮助的关系户,做成衣服。
记得五、六岁的时候穿带小格的白色夏衫,大家都说选得好。隔年,实在没有更好的可选,我勉强定了一款白底有椭圆小黑点的布料。待做成衣服“六一”穿到学校,许多同学都说不好,他们认为这种图案应该穿在女人身上。不久之后,我果然见到街上有中年妇女在穿同一花色的衣裳,就很泄气。不过小时候难得有新衣服,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再也不穿这件衣服的决定。
我一向是个自卑的孩子,在漫长的童年时代没有上佳的表现,所以直到六年级的时候,才加入少先队。我的新衣裳是一定到“六一”才穿的,可我入队那年,五月三十一日就要举行仪式。那天上学我穿的是一件别人剩下的海蓝色的春装,衣服还有些大,很不合身。到上台宣誓的时候,我们班的班主任曹老师还犯嘀咕:“看你穿的什么衣服!”
那年虽然入队了,但那个“六一”也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拉着母亲去听盲人宣传队的演唱也是我童年时代的重要节目。母亲记性好、喜欢唱,她与宣传队的几乎所有成员及其家属都有来往。家在乡下的宣传队的盲人演唱家们一旦进城,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王生彪的父亲是宣传队的队长。每次开演前,锣鼓声之后,都是王生彪的父亲先讲话:“左权县盲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现在开始。”
那时候没有电视,电影经常要买票。国营单位、国有企业的效益似乎都还不错,于是盲人宣传队就在县城各单位巡回演出常常达半个月。他们下乡之后,我们就没有了节目可看。
王二小是那个年代最受人欢迎的盲人艺术家。他的一只手上长有六个指头,我小时候似乎也拉着他的这特别的手玩过。
王二小40来岁吧?他略略能看见一点路,就成了宣传队的向导,一串盲人走在街上,光头王二小总是最前面的那个。
盲人宣传队里还没有女性,所有节目中女性角色都由王二小担任。他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表演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与喝彩,他是那时小城最出彩的演员。
喜兆是吹唢呐的。30多岁了可能攒了一点钱,有人就撺掇他娶妻,对象是患有精神病的“疯桂珍”。20多岁的“疯桂珍”成天涂个大花脸、扎个朝天小辫在街上被人们逗着。喜兆花钱为她买了好看的衣裳,两人却没法过夫妻生活。因为有好事的人教唆,“疯桂珍”就在街上不停地舞蹈不停地唱:“黑狗跳,黄狗叫,花狗咬掉喜兆鸟。”
这样一种生活境遇里的喜兆吹起唢呐,高亢里就多了一层悲凉。
母亲是不是真正萌动过跟着这帮流浪艺人四处漂泊、寻找她另一个理想意义上的生活呢?我今天当然可以心平气和地问她。但在许多年前,这些盲艺人只要在我家与母亲说起要她一起走的话,我就会大动干戈,毫不顾忌他们甚至母亲的面子。
尽管我从来没有鄙薄过盲艺人,但我不能容忍母亲也去了,与他们一样四乡游走。
我生气了并竭力阻挠的事是不是就一定会对母亲有影响呢?我不知道。母亲在家里摸索着抚养大了她的四个儿子。冬寒棉,春暖衫,针线活,三餐饭,盲母默默经营着这一切。现在想,母亲是不是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记得我小时候,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哼唱着忧伤的歌谣,甚至锅灶前刷碗,她都曲不离口。这些曲子大概都是那帮盲艺人唱的内容吧,还有就是我们地方流传了千百年的开花调……
我一直想,做儿子的我能成器,就是盲母今生最大的快慰与幸福了。尽管母亲没有别人家的荣华富贵,她甚至没有许多人都拥有的光明,但她的儿子应该是令她骄傲的。
1996年年底离开家,到第二年的岁末,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妈,我其实不习惯给您写信,也几乎不直接给您写信,因为,这些字都须麻烦别人读给您听,于是,信好像是写给别人的一样,总不像是我和您直接交流。您写来的信不能由您执笔,那种亲切感好像不存在似的,叫我对它有些排拒。
“我这是第一次给您写信吗?第一次用我惯常用的文字向我的母亲表达一些意见吗?我也真有些委屈,我能用文字写信给许多陌生的人读,惟独使用它向母亲表达一份敬意时却如此困难。许多回梦想着给母亲一双眼,您能用它来看您养育的儿子和儿子所写下的那些别人都夸漂亮的文字。这个梦做得好苦,并永远只能是一场梦。就如同我不能挽救父亲的生命一样,我无法还给我以生命的母亲一双眼。
“文字写到这儿的时候我流了很多泪。我义无返顾地走一程、再走一程,我忍受着心灵的巨大创痛。我一般不和别人谈论家事,我不是不热爱我的家,而是谈论它时心情太沉重。离家而去,我远一程、再远一程,但对母亲的牵挂、对父亲的愧疚,伴我走天涯。……”
在这封亦泪亦愧的信中我婉拒了母亲希望我在北京为四弟找工作的要求。我会是母亲的骄傲吗?
二弟在省城读完盲人学校并学了健康按摩,在一家大型浴池做活。我去看他,他说给我按摩,我谢绝了。我宁肯花钱找别人,我也不会用二弟。不是身体受不了,是心受不起。
后来二弟回到乡下,他把自己融进了那群流浪的盲艺人里,并成立其中最优秀的歌者与乐手。
二弟31岁了,没有成家,他用自己游走四方得来的钱贴补家用。给母亲买米面,给三弟5岁的女儿买童车。我建议他上长春的盲人艺术大学,他不想出来,他要让自己的歌永远回荡在太行山的山山水水间。
50多岁的母亲打算替二弟抱养一个女儿,将来好照顾二弟的生活,但我不同意,我是怕这孩子像我一样,终身在心里隐隐疼痛。
至于二弟,他歌唱着,行走在太行山无穷广袤的大地上,他的健康的生活本身,就理所当然是母亲的快乐与骄傲!
在童年的阳光下,母亲曾经张着她无珠的双目问我太阳的颜色。那时候我还是她不懂事但会说话的竹杖,我说太阳是红色的。什么是红色呢?母亲尽量张大了眼来感受光的力量,她似乎说过有了一些光了,似乎就是红色的……
可是什么是太阳,什么是红色?母亲哪里能够知道呢?但我常常把自己穿得红艳艳的,我就是红色;我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为太阳的“阳”,她就是母亲眼里的“太阳”。还有什么能比亲生骨肉更可感知的呢?我想母亲会懂得红色,会看见太阳的!
之二:我20岁母亲40岁时,父亲已经60岁了
一个小城里的盲姑娘,长到19岁了,她的父母要把她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安顿她的一生,才能使她幸福,使父母放心呢?
外公外婆在极其有限的选择里,选择了后来成为我父亲的那个人——一个目不识丁、脾气暴躁、曾经下过煤窑、将近40岁没有娶到媳妇、在外贸公司刮肠衣的工人。但他不是瞎子。这可能是我的外公外婆最最看重的,也是将他们的女儿送出去的最可说服自己的理由。
我的母亲没有眼睛,在外公外婆漫长的人生里肯定不是最令他们痛苦的事。没有子嗣,对于生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他们来说,是一个怎样巨大的遗憾啊!我的第一个舅父14岁死在外婆怀里,第二个舅父27岁因疾而亡。至于我的母亲没有眼睛,那只会是无数次嚎啕之后的一声叹息。
外公所居住的赵家大院是山城不错的一处院落。他的一墙之隔的本家亲戚曾经富有过,富有的亲戚家的更加阔大的宅院后来收归国有,在那片古老的屋顶下组建了县里的外贸公司。那个40岁没有结婚、从松树坪煤窑进城的乡下人,在这个公司里刮肠衣,他的师傅是两个操轻快语音、衣着洋气、戴眼镜、脸色白净的女人。她们来自那时令小城人非常神往的大都市——天津。这两个女人都给我留下了淡淡的印象。许多年后我经常出差来到天津,这个滨海城市却再也没有了早年那两个女人所携带的洋气味儿。
因为住得近,所以可成婚。然而是谁最早倡议了这门亲事呢?我不知道。但他们成亲之后一年就有了我。
我出生后,母亲的两个姐姐中至少还有一个可能在读书。她们的命运尽管日后还会有磨难,但她们读了书,将来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而母亲,她们的盲妹却早早地做了人妻。而最后,她们姐妹因为祖上的房产成了仇人。唉,这就是生活吗?
在父亲与母亲之间“爱情”究竟有多少?甚至他们有没有“爱情”?我懂事后老觉得这是一个令我困惑和不愿深究的问题。反正是他们让人可怜的婚姻结出了我这样的果实。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个年龄很大又没有文化的工人,一个年轻的唱着忧伤歌谣的盲姑娘,他们组成一个家,仅仅是为了生活,哪里还能消费得起爱情?
但是因为有了我,陆续又有了我的三个弟弟,他们就过起了最普通中国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争吵虽然不断,但暴躁而出言蛮横的父亲却从来没有难为过母亲。争吵往往以父亲妥协母亲获胜而告终。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父亲的工资能拿到58元钱,尽管与我同班同学赵玉山做武装部部长的父亲领100多元工资相比仍有差距,但比更多的纯粹农家,我们家的日子并不难过。
虽然父亲从来不穿新衣服,母亲很多年里也只有到春节才拿出结婚时那件暗红色灯心绒上衣、深蓝色灯心绒裤子穿一天,但我们兄弟却一年一定有两身新衣服穿。到我读中学了,课外读物要花更多的钱,我就提出这笔新衣服的钱给我自己,家里不用再给我做衣服了。父母给了我钱,但到春节,新衣服还会有。这样在我身上,家里的钱就花了两份,我便很觉得不好意思。
我五六岁或者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给我做了一件学生蓝小大氅,这是一件实用性不强,只有正月走亲戚、元宵夜看闹红火才偶尔穿穿,但它很显身份和尊贵,比我们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也未必肯给孩子做,但父亲却给我做了。
那个时候外贸公司是令人羡慕的单位,效益好,福利高,自行车还发过两、三次。零碎的东西就更多。我上六年级的时候父亲发了一块紫色的缎子被面,家里就做了一床全新棉花的被子给我,父亲在家里专门为我支了一张单人床,叮嘱我每天晚上洗了脚再睡觉,而他们却并不经常洗脚。没有高贵过的父亲喜欢将我培养成一个有身份有教养的人。
很小的时候,一次父亲带我出门,不知因为什么他说了脏话,我就正告他:“你要再说野蛮话,我就不跟你一起走。”父亲很以此为荣了一段时间,常常在人前哈哈笑着夸耀我。有次我和他去副食商店打酒,酒漫出了锡壶,他在柜台前就要喝掉一口,我反对他这样做,他也就听从了我。
我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规矩?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潜意识里愿意父亲是个体面的人。不过几十年的生活造就了一个粗野的他,稚嫩的我怎么能改变了定型的他呢?比如他夏天不仅光着膀子,而且光着脚。他的厚实的脚掌踩在小城糙砾的路上,对他来说可能也是快乐的一种。
父母结婚后组织上问父亲给母亲上什么样的户口,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的农村老家。那是距县城有37里路的一个贫穷之所在。但在当年城镇粮食供应也不是那么从容的情况下,父亲更眷恋那片土地。最初我们也的确享受到了农村土地的好处,交农业社很少的钱,就能从农民手里获得很多的粮食。秋天,我们家炕上的南瓜像山一样堆起来,一直吃到第二年的春天。
但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拥有城镇户口的好处愈来愈明显。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我们交钱领粮的时代就一去不返了。升学也向城镇居民倾斜,父母就忙着托人找关系给我们转户口。可这已经不是一件可以由他们操持成功的事了。
父亲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经常回到他的乡下老家。但我和母亲回去的次数就少得多。因为不通客车,一般都要等在阳泉开车的刘奋同回乡,我们才坐在驾驶室回一次。我稍微大一点,有时候驾驶室的人太多,就让母亲抱着弟弟挤进去,我上卡车顶上。一次因为在车顶上着了风,从乡下回来头疼了几天,外婆说是乡下的山夹的。于是我对到乡下感到恐怖。祖母去世了,但我哭闹着不肯坐车,我和母亲就没有回去为她送葬。那是八岁那年的事吧?母亲似乎正给三弟喂奶。
刘奋同因为开车,在我们家吃饭都不喝酒。他说他只喝点啤酒。但我们家没有啤酒,甚至什么是啤酒我都想象不出。直到我到榆次进学才接触小香槟。小时候所谓的酒就是白酒,可以到街上零打,是大人们喝的。可以让我喝的只有黄酒,偶尔外婆有心情的年份才酿。外婆还会淋(读去声,滤的意思)醋,叮叮咚咚的醋从架起的缸底的小孔流出,整个院落都弥漫着香浓的酸味。
刘奋同开的是一辆解放牌卡车,我对毛主席写在车头上的那两个字印象极其深刻。我们回到乡下,围观车的人很多,围观我们一家的人也很多。我对乡下人热衷于围观这样的风俗感到惊讶。那时乡下人见到汽车的机会少吧,就如同生活在县城的我对小轿车怀有好奇一样。我们管小轿车叫蛤蟆车,只有省里来的大领导才坐。我们县的领导只有吉普车。
刘奋同常年不在家,他的还算出落的妻子与乡政府任职的一个刘姓本家有亲密接触。这也是那时候大人们经常说的话题。但是荷香嫂和我母亲说起过我父亲在乡下的一个相好。那是崔家的很和蔼的女人,她给她非常本分老实的丈夫生了四个女儿。我们回乡下也主要吃住在崔家。我的刘氏亲戚也会轮流请我们吃饭,但崔家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父亲费了很多周折把崔家二姑娘弄到他的单位,转了正式工,吃上城镇供应粮,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件关于人生出路的大事。父亲的亲侄女在我们家也住了好久,但就没有这么幸运。她自己后来有了另外的前途,但似乎已经与父亲关系不大了。
崔家二姑娘长得与她的小眼睛的姐妹不同,倒有些像我父亲。父亲是不是心里清楚她究竟是谁的血肉?我不知道。他与崔家女人有过怎样的情感历程呢?在当事人都已作古的今天,这将是个永远的谜。
我20岁时,母亲40岁,可父亲已经60岁了。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到汾河边上去读书。有一天突然想起在我与母亲之间、在母亲与父亲之间都是二十岁的差距。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许多不好言说的故事。父亲在他选择妻子时的思想波澜,母亲在她答应婚事时的斑斑心迹,会不会是一首忧伤而无奈的歌呢?静静地流传在太行山,像风一样平常……
之三:北寺巷春秋
狼秋籽生有一群孩子,狼巧莲也生有一群。她们俩是北寺巷两个苦命的要强女性,但她们却做着相互的仇人。许多年前他们率领着各自的子女在巷子里当街对阵,哇哇哇地对骂着“破鞋”、“骚货”,成为早年北寺巷黯淡日子里的有趣内容。
狼秋籽的丈夫在阳泉煤矿做工人,死于疾病。狼秋籽上阳泉陪侍病中丈夫的那个冬天,她的儿子王建明因为没人缝制棉衣无法御寒,我们班主任老师就给王建明放了一冬天的假。
狼巧莲的丈夫是由单位组织乘卡车去大寨参观被树剐了葬身路上的。她的二儿子刘向云也是我的同学,她经常夸我比她家二小强。她说:“二小要是像你一样听话该多好啊!”
两个要强的寡妇抚养着各自一群子女,应该说日子也并不容易。可她们究竟为什么要相互仇视呢?我今天还说不太清楚。有一次我和刘向云到王建明家里玩,刘向云是有顾虑的。尽管王家也没有另待刘向云,但他在王家院里还是被经过王家门前的他的二姐看到了,我陪他回家时,他受到了家里人的指责与审讯。
她们两家最初住在北寺巷的最北端。狼秋籽住槐树院北院。槐树院南院新从乡下娶回了媳妇,人长得很丑,但肯干活,口碑就极好。巷子里不知是谁给她取了个“人人爱”的绰号,大家觉得有意思,一夜之间就传开了。我经常看到“人人爱”提着一桶泔水埋头喂猪,心里就发笑。
槐树院门前的槐树直径有两米,树干都空心了,有几年春来不发芽,有几年春来槐香满巷。这棵老槐树是小城最古老的生命了吧?千年也该有了。他知道的小城的故事比今天所有小城人加起来还要多,可惜,大阅历无言语,它什么也不说。后来有人在槐树上挂了红布,我经常路过老槐树,而红布不褪色,说明不时有人换块新的给它。
槐树院的对面是烈士陵园,是小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外公说共产党也迷信,要不,为什么要把新中国烈士的尸骨埋在封建社会选定的万寿寺的旧址上?
北寺巷的得名与万寿寺有什么关系吗?我没有考证。解放初它叫仁寿巷,后来叫过一段时间丰收巷。在我生活于此的那些年,它没有换过名字。
北寺巷是小城住家的金街。旧时小城首富温家就在这里有大片房产。外公的赵家也算小康家业。外公和他的弟妹都读过不少的书。读过书的外公的弟妹解放后到外地做了官,外公为了照顾这个家而留了下来,但阅读是农民身份的外公终身保留的一个习惯。
外婆家的院落在北寺巷的中段,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如果太行山是我生命的母体的话,这个小院就是我生命的胞衣。它的一切痛痒都触及我的心灵最深处,并波及每一根神经末梢。
我小时候,外婆家的小院排北寺巷15号。那时巷子里各家的院子都很大,但都已经是杂姓杂居。旧时代大户人家的居住格局虽然还能看见,比如几进院落、东西对称的厢房,但因为已经为不同的人家所拥有,旧时代的气息便荡然无存。那时候各院落都有后花园式的闲地,种树种花种菜供孩子们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后来向小城迁移的人口越来越多,宅基地有了严格限制并可以买卖以后,北寺巷除了老槐树,几乎都成了屋顶。外公家的院落没有变,但排序从15号改为27号、38号、42号,仅仅也就几年的时间。小城老巷拥挤得不仅没有了空地,简直就快没有空气了。
我小时候北寺巷北段是一个生产队,四队。刘虎旦是队长,王海珠是副队长。副队长负责收取各家的电费。因为几家合用一个电表,所以按着电灯瓦数计算均摊。为了防止有人作弊讨便宜,王海珠将他的辖区内每一盏灯都在灯泡与灯口结合部贴了封条。我们家的灯上就长时间贴着王海珠的名字。他可能患有哮喘,收电费的王海珠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戴着口罩。
王海珠同院的北屋,住着贫农王秉义。王秉义漂亮的妻子曾是小城第一大士绅温子模的妻子。温被129师镇压后,她下嫁穷人。但我依稀记得人们管她叫“地主婆”。
这个院外面的一个小院,住着兔娘和木匠启旺。兔娘是大队书记刘小兔的娘,但她改嫁后母子不来往。启旺住了监狱,兔娘再改嫁,启旺获释后,兔娘又回到他的身边。
但到了晚年,他们先是分灶、分床,后来在三间屋子的中间垒了一堵墙。他们分灶分床的时期我去过他们家,他们都和我说话,但他们俩不说话。兔娘有一块颜色极艳的毯子,有一张精致的带抽屉的炕桌。
兔娘是外婆的好朋友吧,她经常甚至几乎天天在外婆家聊天。有一次外婆养的一只小鸡奄奄一息了,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兔娘来了,她断定是冻坏的。于是将小鸡放在底火旁边,过了不久,这只鸡果真活了过来。
兔娘是个主意坚定、果断利索、瘦小精干的老人。她极有爱心,晚年她是靠替别人看孩子为生的。因为她敬业,找她的人自然很多。她还是养猫的专家,她养的猫干净漂亮,还是捕捉耗子的能手。
但兔娘要强,她得理不饶人。巷子里一个绰号叫“轰炸机”的中年女子劝她说:“大娘,人都这么一把年纪了,和启旺叔合起来过吧。”
兔娘回敬:“小贱货,你看他好,你和他合起来。你他妈那一把茶壶不开你提那一把!臭水喷到老娘的头上来了。”
“轰炸机”也不是善茬,但面对兔娘,她只能自认倒霉,灰灰地走开。
兔娘病重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去看了看她。墙已经垒起来,屋里非常逼窄,她孤独地犬卧在炕上,更显瘦小。她的身边有她的艳艳的毯子、精制的炕桌,还有她的强悍时强悍、温驯时温驯的猫。
每天都要来外婆家一两趟说无数话的兔娘再也不会出现了。我一时还适应不了没有兔娘的童年。很小的我去独自面对病倒的她,真是对旧日子的一种依恋,对生命即将消失而感到的一种惋惜与疼痛。
外婆家的东厢房有一盘古老的石磨,母亲说她小时候经常用驴拉磨,但在我记忆里它没怎么使用就拆掉了。石磨是在电磨进入小城后逐渐消逝的,外公就在生产大队的电磨房工作,成天价浑身上下落满了面粉的细小颗粒。
我经常到电磨房找外公,外公站在电磨机后边高高的台子上,将面池里主家送上的一铲斗一铲斗还要再磨一遍的粗渣,重新倒入电磨机。我觉得外公的工作很有乐趣。
大队订阅的所有报纸都放在磨房。我去找外公其实是为了看报纸。最新的报纸我不能都拿走,因为大队干部偶尔也要翻看一下,但过期的报纸就无所谓,我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文艺副刊或重要的时政文章剪掉或者带走。有一年大队还订了《人民文学》,至今有几本还在我的旧书箱里。
电磨房夜里也需要人,外公吃完晚饭就到那里睡去。有一段时间我和外公一起去。
外公有一台比《现代汉语词典》还要单薄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小时候听《星星火炬》,后来听《阅读与欣赏》、《小说连播》、《中学英语辅导讲座》。住在磨房的深夜,从大队会议室的电视里看完《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还可以收听美国的华语广播和台湾的对大陆广播。
外婆家的石碾比石磨拆得还早。碾磙和大碾盘都曾是我生活了多年的那个小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一起组装着干活的情景却不曾为我所经历。
我小时候推碾要到槐树院或者刘淑馨家或者杨家。看谁家的碾闲着,去问主家取到碾杆,大人用腹部顶住碾杆,一手推一手还要在碾台上不停地扫。像五六岁或七八岁的我,两只手把住碾杆,绕圈走就是。
印象中刘淑馨的年龄很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但他强健的妻子突然死了,死在有可能早死的刘淑馨的前头。大人们很觉得不可思议。
刘淑馨家养着很多蚕。有一天我忽然对养蚕发生了兴趣,就缠着外婆要。外婆说我带你去刘淑馨家要几条吧。
那是一个中午,刘家的门敞开着,除了炕沿上年迈的刘淑馨在打盹,没有别人。敏捷的外婆在养蚕的大竹盘里抓了一把,拉起我就往回走。
外婆没有想作贼,其实我们是可以要到的,但刘家没有可以答应我们的人,我们就只好走了一个捷径。现在想起来,当时外婆也觉得好笑。
杨家院里住着杨增寿一家、杨凤鸣一家、哑巴和他爹,后院是杨琐庆和他爹。在两院之间有一棵桑树,我不仅去采桑叶,还和几个小伙伴爬上矮墙去偷吃桑葚。绿里泛红的桑葚味道好极了,可惜离开那棵桑树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
杨增寿的子女个个是文艺天才。他的两个儿子先后都到晋中平原上重要的晋剧团担任演奏员,凭的是自己的实力。据我外公说,大队的人真赖,杨家长子被外地剧团选中后,干部们硬拦着不放人走。不得已,杨家长子就把户口从城里先办到乡下,再从乡下离开了太行。
杨家的女儿叫杨美花、杨美月,那是名副其实,她们如花似月,成为北寺巷的骄傲。杨美花人漂亮,嗓门也又高又亮。她曾夸我是个好孩子。但她却迟迟没有结婚,快三十岁了,嫁了人,但那男子已经有一个九岁的男孩。艳丽的杨美花做了这九岁孩子的继母,我就看到这孩子出入北寺巷,眼里有怯怯的光。
哑巴和杨家住一个院,房子似乎比杨家的还要好,但家里黑得像煤窑似的。他爹爱从别人家煤堆上拿几块塞进棉衣里回自己家烧。我们小伙伴就追着他爹乱叫:“偷煤炭老汉张喜汉!”
杨增寿活了比较大的岁数,他的妻子是一个端庄慈善的女人,经常到子女们家去住,杨增寿一个人就到我们家院窜门,和租我们西厢房的俊新姥姥聊天。
杨增寿说:“我这寿数还能增加,可见我家先人给我起名时的英明!”
他究竟活了多大,我不知道。记得有一阵他们院临街的墙上写着一人高的红艳艳的标语:“大干快上!”
这个标语褪色后,整个社会对标语的热情已经逐渐淡去。此后小巷似乎没有什么引人的颜色。
外公不太喜欢杨增寿,也许因为他不太喜欢张扬的性格吧。外公的好朋友是刘致和。但刘致和也是北寺巷唯一的“右派”。
刘致和不会说流行在北寺巷人口头的话,他操别一种语言。他的外地妻子是一个优秀的裁缝师,过一段时间回小城陪刘致和住一阵,还会带上他们的外甥。他们的外甥和我同龄,我们就一起玩耍。
刘致和什么时候离开小城?在外地干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因何罪又迁回小城?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但那时候大队喇叭里经常通知社员们晚饭后开会,内容是批斗右派分子刘致和。
我年龄小,这样的政治活动是不参加的,但外公似乎也不去。不过第二天我们到学校还是可以听说,昨天夜里刘致和被张明伟作民兵的哥哥打了。
经常挨批遭打的刘致和在北寺巷里非常规矩。他的补着大块补丁的劳动呢外衣经常洗得白白净净。
刘致和是北寺巷人,可他祖上的房产哪里去了?他作了“右派”回到北寺巷,就住在驴圈里。但他把驴圈收拾得非常干净,用雪白的纸裱糊了整个的蜗居,映照出太行山在70年代初的酸涩。
刘致和是个书法家,外婆家房子多,每年腊月都要请刘致和来写大半天的对联。整个小院就成了红色的海洋。
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刘致和离开了北寺巷,后来听说他弄平反。他给外公来信,称“丙辰兄”,外公让我回信,我就以外公的口气写“致和弟”。但外公说也要写兄。我不明白,外公就解释说,尽管我比人家大几岁,但这样的朋友写信,还是都要称兄的。
刘致和后来怎么样了呢?他在北寺巷受的所有委屈能因为平反了勾销吗?
尽管许多年里我看着一个“右派”在我眼前无奈地走过,但我那时太小,还不可能与他用相同的话语交流。今天我醒悟到自己错过了一个在北寺巷认识历史的好机会,但1965年才出生的我,怎么可以不错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