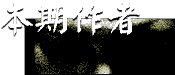花样贺卡还有年华 及其它
一、花样贺卡还有年华
沙子乐队首发式之前,摩登天空寄来一张邀请卡,外表看起来像一张明信片(实际上它也就是一张明信片)。图案很现代,一排五彩斑斓的避孕套,我小时侯对明信片印象很深,新华小学的门口两毛钱一张,不过那时的图案是翁美龄万梓良他们,偶尔还有变形金刚的。黑龙江的冬天特冷,中午不想回家,就骗了爸妈的钱,以吃饭为名,买贺卡送着玩。有一次老师翻书包,没收了一大堆。直到高中毕业,一哥们儿再给我的留言上还提及此事,这厮字里行间,饱含激情,令我感慨不已。后来他考上清华,我沦落补习班,从此不相往来。
我读高中时的贺卡,已愈加精美了。已经有了可以对折的那种,有藏着音乐的,有带着香味的,五花八门价格不菲。每年冬天都会有报纸杂志对送贺卡之事大放厥词,说话的大都是些不堪重负的家长,理由也是五花八门,就差国家颁布专项法律明令禁止了。可是我每年收到的卡也是堆积如山,我一般不回。只堆在箱子里。每搬一次家,就把它们全部在院子里烧掉,那么多的明星和卡通人物就在我家的院子里面舞蹈,舞完了就不见了。
舍不得烧的是女孩儿的手艺,她们亲手做的自然珍贵,不过我也从来不回,我这个人笨手笨脚,做不了细活。用钱买吧又怕玷污了纯洁的阶级情感。她们得不到回报送到失去耐心就不送了。
我不是没钱买卡,而且每年老爸都会带回一大叠邮政发的有奖明信片。他说让我送同学,我妈说不如留着等中奖吧,我懒得跟他们争论索性不闻不问,可能直到现在那一堆一堆贺卡还在我的那个抽屉里锁着,也不知道中奖了没。我确乎已经很久没回家了,大约他们没搬家吧。
我们这代人,叫跨世纪的一代,经历了观念情感伦理等等乱七八糟一切变化最突飞猛进的时间段。人们辛辛苦苦的进化了几千年,无非是解放了女性发明了大炮知道了把东西煮熟了吃,真正质的飞跃都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完成的,现在克隆人也有了艾滋病也有了,信息传递和传染一样方便。很少有人用纸写东西,我好像昨天还陪着那姑娘跑遍康复路去找当年的南韩贺卡,后来就收到那个姑娘的电子贺卡,再后来她也不见了,消失在网络那些林林总总的数码之中,我失恋了。
比我老的那个老崔在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声音至今在耳边,可传出那把声音的旧单放机,今天到了什么地方?
我现在收到电子贺卡一般也是不回,上次被老家一哥们儿实在逼得没办法,就在网易随便挑了一个给他发过去了,还顺便捎带上两句祝福的话,前前后后不到三分钟。网费大约是三毛六分钱,他挺高兴,说你真够意思。可我反而觉得空空荡荡的,象是没吃饭。是啊,我小时候那些没吃的午餐,现在,都到了什么地方?
二、我们都被科幻电影给骗了
科幻电影近几年贼火,特别是在好莱坞电影市场上,从《未来水世界》到《魅影危机》再到《恐龙》,一部一部赚光了影迷的银子,还影响了一代人。这群少不更事的小影迷们,从小就立下志向,要杀光妖兽和外星人,保卫世界和平,阻止世界末日。我们当年看孙悟空时,似乎也有这种想法。
国外的科幻片多得数不清,大牌明星们纷纷披挂上阵大演成人童话,看的人眼睛直冒蓝光。而说穿了其竞争无非只有两种,一种是拚场面,一种是比恶心。
外片胜在大成本制作,这一点毋庸置疑。说穿了人家就是拿钱堆出来的,用高投入换高票房,媚雅的小青年就是喜欢这一点。而这一点中国人是做不出来的,据我所知,中国的科幻电影很多年前倒是有一部,叫什么《大气层消失》,片子拍得简陋粗糙非常难看,那还骗了不少孩子呐!更不用说老外用先进技术包装的离奇故事与恐怖预言了。日本的科幻片一向也以拍得滥著称,大河原孝夫的《酷斯拉》倒是争回了不少面子,可惜一露面就玩的是西方的那一套,单是看宣传就让我想起《侏罗纪公园》,科幻电影究竟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幻想?
比恶心是西方恐怖片的绝活,他们管那种恶心的恐怖片叫科幻片。香港鬼片里莫名其妙的绿色粘稠液体,到了美国就成了生化武器,那些灵异事物,在西方就成了三度半空间的G8物质。还有那些奇形怪状的小虫子,怎么恶心怎么来,最好是看得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们也似乎倾向于这种精神受虐,整天惴惴不安的生存,甚至担心接吻时情人那嘴里会钻出一条粘乎乎的虫子来,真是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其实科幻电影光怪陆离的充其量也只是外壳而已,它的故事构架大都是最单调传统的那一种“大团圆结局”。这些和中国传统武侠片相似,不管背景有多大,武器有多先进,动作多夸张。最后清一色都是正义战胜邪恶,英雄抱得美人归。阿诺史瓦辛格的新片《第六日》,借用了克隆人的概念,在这个节骨眼上推出,倒也讨巧。可它的情节和香港恐怖片《怪谈协会》中的一个故事极相似。甚至诡异刺激的程度还不如港片。像《未来水世界》那种假设,杜琪锋很久以前拍《现代豪侠传》时就用过了。不过香港人管那不叫“科幻电影”,叫“新武侠”。
科幻片的分类也是模棱两可,大凡涉及未来的,有一种以上不知名生物的,甚至稍有不符合常理的地方的,都可以被称作科幻电影。有一网站居然把《发条橙子》列为科幻电影,真是比电影本身还夸张。你丫怎么不说占基利的《格林奇》是科幻电影啊?好多人就是被科幻的名字镇住了,以为科学的有多牛逼,有多高层次。我就觉得那些片子没什么可看的,有什么呀。
打着科学的旗号幻想,怎么不着边际都看似很有道理。科幻电影,说起来倒挺吓人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
三、人民到底需不需要非主流
本世纪最后一个圣诞夜,在北展剧场看朱哲琴唱歌,唱着唱着突然窜出一男一女两个老外,站在台上面面相觑做出种种怪异的声音象在表演外国口技,搞得观众朋友极为不满,于是台上台下怪声此起彼伏,热闹得更像一个圣诞夜了。朋友说,这是我见过最怪的一次演唱会。我说,其实这挺牛逼的。
我都不知道我说的话是真是假,是什么意思。
最近,总是看到那个名字,连缀在一部很热卖的影片背后。率领着两个香港明星的名字,成为第三个明星,这样的“王家卫”更像一个名字了。
从前的王家卫,是代表香港非主流文化的,有人把他看作是这块文化沙漠里的一块惟一的肥沃土壤。可是在传统的概念里,艺术始终应该属于一小部分人的。他一旦介入各种时尚媒体,在大众中蔓延开来。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我不明白一个拍艺术片的导演为什么会带着主演四处招摇,这样的场景让人很容易的想起冯导带着他的葛优吴倩连在全国上下“没完没了”的往事,很容易想起痞子蔡带着他的垃圾文字和全国读者第N+1次的亲密接触。如果艺术家真的不能免俗,那我们对他们的深切敬仰岂不是痴心错付落花流水伤心太平洋?
前几天还有一朋友跟我说现在的非主流反而成了主流,而主流的反倒成了非主流。这话我说得我云里雾里不知道他的意识里到底什么是主流什么是非主流。事情就是这样,看来他很不高兴,所有的音乐台都在放那些听不懂的朋克,所有的大学生都迷恋NIRVARA、GUN N’ROSE,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能令他们很快的高级起来。大陆乐坛也是,出了个乐队就想搞得另类,写一首歌就想写的先锋,然而先锋毕竟不是逼出来的,另类也不是摆出来的,先锋就是先锋。当另类成为时尚,爱就成了往事。
世纪之夜在臧天朔的朋友酒吧看了一场演出,看了许多北京的地下乐队喧闹的现场。个人觉得不错的只有一个叫“木推瓜”的乐队,那首《哆嗦哆》给我印象很深,可这样的歌大众能不能接受,大众到底能不能接受用那样的声音改编那首家喻户晓的《娃哈哈》?会不会当乐评人争先恐后的说他们好的时候,人民群众才恍然大悟地说原来不错?这是什么审美原则?
在张广天把“格瓦拉”塑造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宝贝形象之后,孟京晖又带着他的臭虫们在儿童剧院排队恭候大众对先锋戏剧的检阅,先锋戏剧的演出终于成为了一桩公众事件,艺术工作者们得偿所愿了,商业操作者们利益均沾了,人们群众从此高尚了,而艺术呢?大众说,我们热爱艺术,我们需要;我们爱摇滚乐,我们需要;我们爱先锋戏剧,我们需要。我们需要自己变得优雅而崇高。
我们真的需要吗?我是指我们中的大多数。当《格瓦拉》们站在剧场门口以穷人的名义出售各种纪念品各种商业符号时,我们知道英雄其实也是需要收保护费的,自由是需要钱的。当我看到格瓦拉的主题歌,想到了《我的祖国》和《血染的风采》,我知道艺术被利用了,被利用的是名字是外壳,而这些,似乎人们需要。似乎只有这些符号这些形式才是人们需要的东西。
什么是需要?人们到底需不需要吃饭睡觉?这是肯定的。人们到底需不需要谈恋爱?答案也毋庸置疑。似乎连朱文的“人们到底需不需要桑拿”,也可以问得理直气壮。可是作为非主流的艺术,人们到底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很“大话西游”吧,可能把它作为一个问题就是荒谬的。
在需要面前,我们变得无力而脆弱。艺术究竟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还是说得更严重点为人民币服务,在商品社会里我们说不清楚。我们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四处都是无形的力量,无形的力量控制着我们,还要说我们把它控制了。也许是真的吧,那我们为什么还感到不舒服?
朱哲琴的演唱会散场时,朱说这是我们搞的一个试验,希望这种艺术形式能被大众所认同。散场的喧哗中我没听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也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