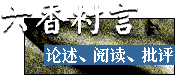文学麦当劳里的匿名写作者
--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批判之一
◆从杏花村到麦当劳
今天的写作者犹如建筑工人(但不是建筑家,更不是建筑大师),在文学期刊上建筑起一座又一座的酒吧、咖啡屋或舞厅。或许,我们应该为此鼓掌。酒吧、咖啡屋或舞厅,在大众和一部分评论家的眼中早就变成了都市化的标志和符号。他们为都市文学在当代文坛的缺席而担忧和焦虑过,因为他们深信都市化与现代化是同构的。而纸上的酒吧、咖啡屋或舞厅恰恰满足了他们的期待。柔软或闪耀的灯光、透明玻璃杯里的液体和水草般扭动的身体,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和符号。所以,当年轻的写作者们跳上文学的舞台提出什么“用身体或皮肤写作”时,台下涌起了如葵花般盛开的掌声。我们有些陶醉了。
不妨先让我们重温一下那农业时代日常生活的诗意:“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杜牧《清明》)在这里,写作者同时是一个饮酒者。但“酒”和“家”两个词语的自由结合,使喝酒的地方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场所。酒家的位置“杏花村”,暗示那是一块弥漫着古典情怀的土地。飘落着三两花瓣的古典情怀,往往是中国的落魄文人消解文化暴力的有效方式。在这种氛围中,“酒”不仅仅在胃中燃烧,它更能使饮酒者获得暂时性的内心的解放。写作者的心态是自由而非功利的,他们可以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路上行人”乃至世间的万物进行对话。当然,这种“酒的诗学”在精神内核上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批判精神。但它同时也避免了写作者因为对批判精神的表达焦虑以及过于严肃而产生的结结巴巴口吃现象。杏花村里的“酒”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空间,它无须保证或监督写作者一定要表达什么。它是要解除而不是重新设定关于写作者的禁令。“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唐·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酒”成为写作者书写内心、回归家园的通行证。数千年来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是一手提着酒壶一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再让我们看一看一百多年前经典的巴黎小酒馆:
(无产阶级密谋家)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可疑的人……他们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流浪汉之流的人。……
(他们)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查工人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放荡者。在秘密会议上像斯巴达人一样严肃的阴沉的密谋家,突然温和起来,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大名鼎鼎的老主顾。这种酒馆欢乐由于密谋家经常遇到危险而更变本加厉。
这种小酒馆不是建筑在纸上的,它们散布于随处可见并且可以触摸的街角或地下室。19世纪欧洲语境里的小酒馆是与革命相关的,它能使人“从沉醉中获取革命的能量”。但这种革命不仅仅指发生在街垒的政治暴力,它还象征着资本主义时代写作者内心的冲突。本雅明通过波德莱尔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馆发现了“文人”的影子。“文人”同密谋家一样,总是出没于小酒馆和小酒馆之间。小酒馆的顾客是不断流动的,“文人”会与他们纵情谈论“美酒和女人”(对于酒和性,我们不要习惯性地赋予它们否定意义),“文人”会做出各种无法事先预言的事情。“文人”藉此获得了流浪汉般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但它又是“摆脱作为一件商品,一个符号的存在所需付出的代价”。小酒馆的“酒”,使写作者拥有了与自己与尘世进行搏斗的勇气。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们的内心特别需要那种“探险性的,流浪汉般的”内在节奏。他们这种具有革命气质的书写,会有效地颠覆资本主义时代的复制行为和工具理性对内心的奴役。
仍旧回到今天的写作者为我们准备的酒吧里,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1987年,海子曾使用“病中的酒”来书写关于荷尔德林的寓言。随着那个激情时代的远去,中庸保守现世的哲学开始弥漫于当代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酒吧的作品以集团的方式走上文学期刊以及大众媒体的桌面。当然,这与大大小小的酒吧在街头的涌现有关。但街头的酒吧与文学的酒吧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当代中国文学里的酒吧,实际上是年轻的写作者在幻想中的“酒的麦当劳”。酒吧里的“酒”因为是烈性饮料而未能通过时代的审查,被悄悄置换为麦当劳里的软饮料。这种软饮料仍然被称作“酒”,但它与内心的解放和革命无关,它只是集中体现了麦当劳中的交换原则。在当代写作者的笔下,酒吧的秩序就是异性相互勾引、商业合同谈判以及无聊文人的意淫和口淫规则。这种酒吧实际上受麦当劳秩序的支配。麦当劳是以饲养的方式解决人的欲望问题,它的流水操作程序把人的需求置换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利益关系。麦当劳式的“酒”使他们的纵欲、斤斤计较和募仿诗意的撒娇行为,通过看似公平的交换拥有了合法性。在酒吧里流淌的欲望,并没有一些评论家所说的“解放肉体和精神的意义”。它只不过是个体之间的利益交换。今天的杏花村,也与农业时代的古典情怀无关。它早已被注册为商标,遵循着商业社会里麦当劳的游戏规则。
◆文学的麦当劳化
不仅仅是文学酒吧的“酒”被麦当劳化,时下的文学期刊、文学活动、文学机构或从业人员都不能幸免。“酒”的失败,暗示着内心的解放和革命将更加困难。在90年代,中国文学逐渐丧失了“酒”的精神、“酒”的逻辑、“酒”的真理。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正在全面麦当劳化,我们的文学正在迈进那巨大的金色拱门。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所揭示的,麦当劳在中国甚至成为“某些学者读书写字的好地方”。麦当劳作为美国文化(西方文化)和快餐文化的符号,在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麦当劳对世界的成功入侵,是因为“它为消费者、工人以及经理人员提供了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而文学麦当劳里的阅读者、写作者和文学编辑,也无非就是文学的“消费者、工人以及经理人员”。他们都成为机械复制时代中的一个环节,他们的行为不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他们根据别人的定货清单来阅读、写作和编辑。曾有年轻的写作者,在书的封面赫然印上“某某制造”的字样。“制造”一词,无意中泄露了“文学的麦当劳化”这一众人皆知的秘密。再进一步,我们就会发现麦当劳模式对当代文学造成的内伤。
效率。随着海子的自杀(1989)、汪曾祺的病逝(1997),农业时代的抒情成为了绝唱。当代的中国诗人在90年代纷纷从麦地里走出,告别了梦想的天鹅、果园和星空。本来,写作者失去头上虚幻的光环后,可以平心静气地在日常生活的最深处居住并且沉思。但麦当劳时代的效率原则,仅仅提供从饥饿到温饱的最快途径。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下,文本的阅读不再是一个审美过程,它成为阅读者的资本符号。于是,大家神色匆匆地翻阅着普鲁斯特、乔伊斯或博尔赫斯,然后又神色匆匆地聚到一起唾液四溅地谈论。《人论》(卡西尔)、《性格组合论》(刘再复)在80年代的热销,让人感受到启蒙时代的激情。而《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以及博尔赫斯的作品在90年代成为热点,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复兴。它不过是一个由众多的赶时髦者共同参与的幽默故事,那些厚厚的书籍很快在他们的书架上落满灰尘。文学名著的缩写本、改写本以及连环画卖得比原著还要好。哲学通俗读物《苏菲的世界》、《纸牌的秘密》,大有取代黑格尔、梯利和罗素之势。麦当劳里的写作者被拔苗助长,他们缺乏深厚的精神资源,普遍呈现出营养不良的面色。
可计算性。在麦当劳里,量成为质的对等物。当写作行为转换成制造行为,我们对写作者能力的检测也开始以尺子和秤为标准。“可计算性”的原则,同时也是一个“简约”的原则。它把需要耐心的文学审美过程,简约成对厚度、重量和长度的简单测量。加入不同级别的协会,需要有若干数量的作品发表。专业作家像工匠一样,每年有着自己的写作任务。而写作者也缺乏耐心将作品打磨好,因为用秤来称一块精致的玉不会比一堆垃圾更重。有些写作者放弃了“为人生而写作”、“为艺术而写作”,他们是“为浴室而写作”、“为卫生间而写作”。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发现的“拾垃圾者”形象,开始出现在90年代中国的语境里。在经济学中,如果“劣币”(不正当收入)驱除“良币”(正当收入),就会使市场增加不稳定因素。同样,文学麦当劳里的可计算性,不仅没有为文学确立秩序,还暗暗纵容了投机倒把的写作者。
可预测性。麦当劳里的食品在不同时间和地点都是一样的,它提供一个封闭的可预测性的模式。而文学的魅力,在于它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断提供新的元素。二者的秩序是不相容的。90年代的文学写作和研究,却以被异化的代价打上了机械复制的烙印。只要我们熟悉了写作者和研究者的密笈,就会发现他们不断重复的套路。当代文学的困境不在于对经典作品的反复摹仿,而在于写作者的自我抄袭和互相抄袭。打开一本本文学期刊,我们很难辨认出谁是新鲜的歌者。在时下有关“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大量评论中,很少有具体的作家论,所涉及的作品也是非常有限的几篇。这既说明了写作者们作为个体的单薄,也说明评论家的“人云亦云”。机械复制使他们的写作和研究不再是脑力劳动,而仅仅是誊写或输入文字的体力活。同时,文学的可预测性还可以提供一种安全感,他们不愿意冒着风险提出新的观点。
控制。流水操作程序(非人性的技术)控制着迈进麦当劳的每一个人。在这里,不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而是程序和技术奴役所有的人。在文学麦当劳里,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规则控制着写作者、媒介、出版部门、研究机构和协会的命运。写作者要获得内心的自由,首先要抵御外在非人性的技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而在一个麦当劳程序日益占垄断地位的语境下,反抗有时意味着被遗忘。因为文学麦当劳对写作者来说,是“适者生存”而不是“优胜劣汰”。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不得不考虑经济上的效益。它们大都有一个庞大的理事(董事)会,理事(董事)会成员多是公司老板、政府官员。90年代后期文学期刊的停刊、断奶(政府停止资助)和分流,暗示着文学独立生存空间仍在逐渐地逼仄。与此相对的是,梁凤仪的小说直接挺进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些视潮流而动的文学投机商成为文化英雄。
◆匿名的写作者
1992年初,北京开设了一家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麦当劳快餐店。在开业当天,就接待了约40,000名顾客,创下了麦当劳单日营业额的新记录。在文学麦当劳里,也同样坐满了各有打算的写作者们。他们以各种姿态出现:有的面色匆匆,有的一声不吭,有的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大量的写作者不断地进进出出,位子刚刚空出来就会有人填补进去。只是谁也记不得他们的面庞,文学麦当劳也不会因为他们而改变些什么。每天发生的大量事件,迅速被随之而来的另一些事件湮没。在这里,写作者留下的名字及时地得到覆盖,以致于无法辨认。失去“酒”的写作者,再也没有仅凭潦潦草草的几十字便在文学史上站住脚的豪气。
在90年代,伴随文学麦当劳化进程曾产生文化命名的狂热。在文学讨论中有二十几种“新XX”,如“新状态”、“新体验”、“新历史”等等;在文化讨论中有十几种“后XX”,如“后现代”“后殖民”之类。(不可否认,其中有一些深入而必要的思考。)“新”“后”的标新立异,犹如商业广告的策略。这种词语的繁殖受麦当劳效率原则的支配,它构筑了一个个虚幻的表象。它们在词语的走廊里展现的只是仅供参考的预测效果图,而非实际的场景。“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提出,集中反映了命名的策略性。它先圈出一大块土地为己所有,然后慢慢从中挑拣自己所需要的进行包装。这样,写作者被控制并具有了可预测性。命名犹如花里胡哨的标签,诱惑着人们的购买欲望。但是,过于肤浅和繁杂的命名恰恰导致了写作者的匿名。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那些渴望和寻求命名的写作者。命名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是写作者为掩饰自己的单薄而打开的保护伞。写作者通过命名获得“群”的认同,从而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从中获得利益。但这种命名始终无法凸现作为个体的写作者,他们在“群”的命名中丧失了自己。他们的理论演讲往往胜于诗性吟唱,他们不断地制造着各种新鲜的名词,他们与大众媒体互相称兄道弟。他们的写作与内心无关,那些“新XX”“后XX”在他们眼中如同上市股票。写作者一旦扮演了公共人的角色,他的作品就有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正如今天,有几个人能说出“新XX”、“后XX”的旗号下到底有那些写作者和作品?人工命名的行为,使写作者反而失去自己本来的姓名,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匿名状态。他们在文学的树木、石头和建筑上刻下歪歪斜斜的“XX到此一游”,以为这样就可以不朽。这无疑是文学麦当劳时代上演的一出喜剧:写作者们在脸上涂满千篇一律的油彩以凸现自己,最终他们真实的面庞也被遮盖和遗忘。
还有一些对命名不感兴趣的写作者。他们的写作是出于内心的需要,他们不愿意接受定货清单,他们会仅仅因为兴趣用几个下午的时光琢磨一句话。自然,他们也是匿名的,他们还会被文学麦当劳里的聪明人视为小丑。这些写作者被到处驱逐,他们只能蹲在墙角继续书写他们的诗句。但或许正是在墙角、“散发出霉味的/楼梯口和窄小的房间”,他们捡到了“劣质咖啡和纸烟,或一小杯/淡红色的甜酒”。于是,他们得以重新品味“酒”的诗学。事实证明,这些匿名的写作者最终将得到追认。我们在这里会想起王小波,他狂欢节似的叙事文体勾勒出自己“小丑和傻瓜”的形象。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王小波,极力逃避着文学麦当劳对自己的奴役。他不惜为此放弃在名牌高校执教的教席,作一名自由职业者。他“处于生活和艺术的交界线上(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中间领域”:他“不是一般的怪人或傻子(在日常意义上)”,但他“也不是喜剧演员”。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声音,会在寂寞中获得永恒。还有诗人胡宽,他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作品,但留下了近两百万字的手稿。他在酒糟公墓、垃圾和洞穴中,发现并书写着具有茂盛的生命力的土拨鼠。他的诗歌如同疯人絮语,有一种疯癫的颤抖的节奏。文学麦当劳里的体面人,自然会无视并嘲笑他的存在。在他们眼中,这些例外的陌生的元素是自己中产阶级生活的潜在敌人。所以,这一类写作者大部分不为我们所知。他们选择了在沉默中生活,在沉默中思考,在沉默中写作。但他们的匿名状态却是暂时的,他们终将在黑夜中传出自己内心的声音。
或许,文学乃至社会的麦当劳化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进程。但真正优秀的写作者,往往是隐姓埋名的。他们会躲在某个角落,去重新获取“酒”的精神、“酒”的逻辑、“酒”的真理。那些渴望命名的聒噪者,最终在自己的喧哗中丧失自己的声音。甘于匿名的写作者,默默地为我们提供了《诗经》、《古诗十九首》以及伟大的史诗。仍然是他们也只有他们,会在不经意间隔着岁月的长河向你递去一枝沾满尘土的金玫瑰。
(2000年4月)■〔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