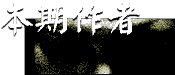时间的形式
……那缓慢而甜蜜地销蚀着身体的时间。
--米兰·昆德拉
“矮胖的工厂守门人微笑在火焰的阴影里……他对时间有着超常的嗅觉和敏感。”在《火焰地》中,我曾这样涉及过守门人与时间的某种关系。覆绿蜀山的脚下,有着熊熊焰窑的陶瓷工厂的矮胖守门人--人们叫他矮坤大。脑中有关他的记忆,背景总是炽白近乎透明的故乡夏日。肥肥鼓起并在肉缝间夹着汗珠的圆肚皮(穿宽大的须用带子在腰间系住的蓝布老头短裤,汗黄的短袖衬衫从来敞开在肥肚的两侧),佛一样和蔼的笑(带那么一点点乡村世事过来人式的聪黠)。超长的两轮木头板车,有的卸空,有的装满刚从窑内烧出来的金光闪闪的陶器,从厂门口进进出出。下午,只要平顶简陋的传达室东墙下一出现“阴头”(房子投下的阴影),守门老头就会迫不及待地拄着拐杖,去附近人家葡萄架下的井内提来一桶井水,浇在东墙下粗糙的水泥场上。“滋-滋-滋-滋--”烈日灼烤下焦渴已久的地面拼命汲吮着冰凉的井水。这时候,老头便把他的那张老藤椅搬到外面,舒坦地坐在里面,双手扶着圆滑的木拐杖,露出肚皮,和蔼微笑着看每一辆进出工厂的木头板车,和每一个走过的大人小孩打招呼。“矮公公(孩子们这样喊他),现在几点了?”--守门者人生中的一个典型镜头随之出现:假装捋起粗肥手腕上的衣袖(实际是裸露的手腕,并能在手腕的肉上看到脉搏的跳动),端详一下“手表”(子虚乌有的手表),然后认真而又肯定地判断:“4点零9分。”--故意不说整数,以显示其准确和自信的程度。我,或者邻家的某个孩子,听完后会立即拔脚朝家中跑去,看一下放在堂屋长台上的闹钟,再飞快地跑回来:“准佬!矮公公!”他便开心地大笑。他嗜好所有的人对他进行“时间”考验,他终归是骄傲自得的胜利者。他,跳动着的、弥勒佛一般微笑的肉身钟表。而童年日常生活中父亲的一件事(起床),则准确显示着一天中的一个特定时间。瘦小却筋骨硬朗的父亲那时是宜兴合新陶瓷厂窑上的驳运工。那是重活,即把烧好的缸瓮壶盆罐等等陶器从窑旁货场用木扁担、大竹筐挑上河边的大驳船,摇船往丁蜀镇上的“陶批站”(陶瓷批发站),再从船上把所有的陶器挑上岸。日复一日,几无间隔。大概跟陶器出窑的时间有关吧,干这个工种的工人都得起早。处于工厂边缘的矮小局促的“披屋”内,闹钟铃响,父亲起来,我们三个孩子也总会从甜热的梦中醒来片刻。穿衣,简单漱洗,吃东西(无馅的米粉团子、汤山芋、泡饭或少油的麦面薄饼),竖在门后的木扁担与门框的轻微撞击,熄灯,关门。干活去的父亲的脚步声远了,不用看钟,我们都清楚:每天的这个时候,是凌晨3点半。熹微而清贫的黎明,要等我们再一次熟睡之后,才会来临。和父亲类似,一个返乡者的身影,也准确显示着一个特定时间,不过不是一天,而是一年中的一个特定时间。返乡者的两个儿子冒文明和冒小年,是和我一起在窑场上捉迷藏、在“胡花狼”(苜蓿)地里翻跟斗练鲤鱼打挺的疯野玩伴。他们家在油菜花田边高高暗暗的阁楼上,平时,由返乡者的妻子,那个在紫砂厂做茶壶的女工一人在家照顾并严厉管束着他们(吃过晚饭到阁楼下叫兄弟俩出来玩,总不敢喊名字,而是学着电影里特务的联络暗号--鸽子叫--进行联系)。我对他们很羡慕(两兄弟自己也很骄傲),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地质队员,长期漂泊在外(好像是在湖北吧),为公家寻找各种各样的稀有金属矿床。他们老是在盼着自己的父亲能够早点回家,我也在盼--倒不是为了他们父亲所带回来的吃食或好东西中也许会让我沾上一点光,而是因为,这个返乡者的出现,会让我在心中生出一种暗暗的激动和幸福:噢,年又要来了--有鱼肉吃有鞭炮放有压岁钱拿的年,顶多再过一个星期,终于又要等来了。冒家兄弟的父亲--背微驼、说普通话、满身白肉(在工厂雾汽腾腾的浴室内我曾见过)的一年一度的老家返乡者,在我的眼里,成为了“年”这个时间的使者和化身。
除了表现为事件形式的时间之外,记忆中的时间之于我,还常常呈现为声音形式。古老的铁质小轮船(漆成绿色),突突突地擦着蜀山脚下又长又窄的木头南街,在清波微漾的蠡河上朝北驶去。这是每天从丁山开往无锡的固定班船。轮船很小,吃水却很深。客舱是一个打通的空间,随便放置着几条长长的木凳供人歇坐。上城的乘客三教九流,斑驳纷杂,有投亲访友的,有买结婚嫁妆的,有求医问药的,有讨债的,有到梅园开源寺烧香的,有往崇安寺热闹场所白相的,有赌博赢钱后返家的,嘈杂方言在劣质香烟的烟雾中如煮如沸。竹篮、麻袋、鼓鼓囊囊的布包与扑叫的鸡鸭、沾泥的百合以及新鲜红白的猪后腿交相辉映。碧绿的河水,几乎就齐着舷窗在你脸旁荡漾。小轮船驶近蠡河上的蜀山码头时,便“呜-呜-呜--”地拉响它的汽笛。听到船声和笛声,在河边劳作的人们就会丢下手中的活计,相互说道:“时间真快啊,又到10点半了。走,下午再做吧,该回家烧饭吃了。”换糖佬的镗锣声不同于船声和笛声,那种在家门外响起的缓慢、铜质的声音,提醒的是懒洋洋空荡荡星期天下午2点左右的时光。换糖佬是一个长高、沉默、有着满嘴花白胡子的老者。他孤身住在南街街尾某一间幽暗的木头房子里。我曾到过他家的内部(急着做弹弓便找到他家上门买2分钱3根的水牛筋),白天的屋内也很黑,模糊中的简单灶台和竹制家具散发一股湿和霉的陈年气味。进深很长的屋的后部,一块方方的窗户很亮,从窗中,可以看到一丛自蜀山上悬挂下来的如线藤蔓,鲜绿刺眼。换糖佬平时把摊子摆在东坡小学门口。黄旧的木挑子内,有切成小块、沾着白粉的面糖,有金黄透明的圆形棒棒糖,有用两根小竹棒可以将软糖绕来绕去的绕绕糖;除糖之外,还有水牛筋、炮子、铅笔刀和花花绿绿中空细瘦的彩色塑料牛筋(上课或在教室午睡时,可以将其一头放入课桌内的水瓶中,一头含入嘴里偷着吸水)。星期天学校没人了,换糖佬就挑着他的家什,不紧不慢地敲着那面铜镗锣,按着某条习惯了的路线走街穿村兜售他的生意。镗锣声在我家门前响起时,一般都在午后2点左右,正是午觉应该醒来的辰光。听到由远而近熟悉的声响,有时我便会马上钻到烧饭的锅台旁,从某个布满灰尘和蛛丝的灶上壁洞中,费力找出一只空瘪牙膏壳或一只干黄的鸡肫皮,跑到老头那儿去换回几根水牛筋或一小块面糖。然后,再算计着花1个小时做完家庭作业,这样,在父母干活回来之前(约下午5点),还可以出去玩上一圈。换糖佬的镗锣声在我听来表示的是星期天下午的时间,那时候,在清晨催促、提醒我抓紧吃早饭上学的,是家里挂在墙上的那只农村有线小广播发出的声音(又一例生动的声音形式的钟表)。那时清早的广播里有一个“每周一歌”节目,这个不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的“每周一歌”唱完后,是6点30分。唱歌时,应该也是我每天吃早饭的时候,不然,上学就要匆忙了。依然清楚地记得在冬天的寒冷清晨,一边吃着热腾腾的白粥加咸菜,一边听于淑珍(?)唱《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情景。“每周一歌”的旋律,变成了我可以欣赏和聆听的时间。
“从他(她)的脸上,我已经看到了他(她)老年的样子。”走在路上,碰到某些偶然相遇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她经常对我这样说着。她实际是在想象中看见了时间,看见了无限时间直线中具体的一段时间。而我,则在个人生活中心情复杂地亲眼目睹过这种时间(具有一段长度的)的留痕--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亲历,同时于浑然不觉的时候,也在被他人目睹着时间在自己身上的刻痕(所谓“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L是老家理发店的……女性。那时候,刚来跟她父亲学理发时,是夏天,穿着有蓝色花朵的连衣裙,在理发店内的两面镜子里,像极了一枝亭亭、圆润,散发着细细光辉的微笑青葱。……理发店的生意因此好了许多。时间像河水一样无声流淌。在外地偶尔匆匆回到老家看望父母,一般也不会去理发。几年过去。一次回乡,在黄昏马路两侧临时的嘈杂菜市上,我碰见了她。牵着蹒跚的她的孩子,失去光泽的头发马虎地束着,身上的白理发工作服沾满碎发和日常积下的污痕,脸上,也显出了原来似乎没有的几粒雀斑(请原谅我的观察)。她仍然微笑,但……已没有了“亭亭”、“圆润”和“细细光辉”。她给蹒跚的女儿买馒头吃。我们打招呼……她们在身后菜市的人群中走远……那一刻,我是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了时间,我看见了属于时间的某种邪恶。是的,在某一点上貌似温柔的时间,实际却深深潜存着--一种狰狞。证明很容易,只要随意截取一段时间的距离,看这段距离在具体的人或物身上留下的印痕,你就会震惊地发现:时间,原来是如此残酷(“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终于明白,我的前辈所害怕的,正是残酷,源于时间的这种残酷)。
作为“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时间确实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具有无数的“变脸”和外衣。前述种种,只是时间就我而言的形式(我个人感受到而他人不一定能感受到的,表示时间的事件、声音或其它),私人形式。时间的公众征候(形式)更是比比皆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和死亡的环境:鸡鸣-黎明;草木萌发-春季;闪电-夏季;落叶-秋季;飘雪-冬季;井水的温度-温热即冬天,冰澈即夏天;圆月-月中;弦月-月初或月末;繁星-夜晚;河流的枯水期-秋冬;河流的丰水期-春夏;太阳近乎直射-正午……时间斑斓的流逝与变化,使地球上每个人的生命都具备了星夜般的神秘和魅力(农业时代的神秘和魅力,当然有的人或许一生也不会去释放这种东西)。而当今世界,内心饥饿且混杂疯狂的汹涌人类的伟大努力,似乎就是模糊并去肢解证明我们活着的时间。空调混淆了冷暖,磅礴的航空器取消了时间,封闭得越来越严实的居室隔绝了风霜雪雨,还有冬天的西瓜、夏天的萝卜(无季节蔬果),还有铺天盖地的化妆品,数不胜数的“去皱纹”、“丰乳”、“再次青春”的美容手术(努力抹去某段时间的长度在身上特别是脸部的留痕)……由此,当代的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特征逐渐凸现,这就是:时间的丧失。
(1999.4)■〔寄自江苏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