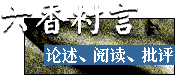我把博尔赫斯的《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看作文学翻译的寓言,大概是基于这样的尴尬:尽管我一向有着对“外国文学”的阅读热情,其实却不具备接触它们的起码条件。我不通外语,无能越出汉语的长城。如此,我能够认知的“外国文学”,不过是翻译文学的描述;就像在那篇有名的小说里,被不遗余力地缔造发明的四十卷《特隆第一百科全书》,才是幻想世界的现实--那被虚构的某颗命名为特隆的星球、星球上的全部所有和一切细节。
当然,我知道(那毕竟是常识),“外国文学”--存在于诸多对我来说不可索解的语言里的文学现实,绝非特隆式的乌有。然而,又何妨将它们假设为乌有?权当它们是文学之特隆!实际上,它们进不了我阅读的视野。考虑到语言划定了界限,我可以说,“外国文学”并不存在。存在于我所熟习的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之中的,那由翻译家们加以描述的所谓“外国文学”世界,其实是另一种文学现实,一个翻译文学的世界。如果你认为那些翻译家们、特别是翻译家们组成的协会和研究所,跟特隆故事里那个“秘密慈善团体”有几分相像,那么为什么,你不能暂且把他们所描述的“外国文学”当成虚构呢?
我认为,博尔赫斯(或某个译述者--有必要故意混为一谈吗?)为那篇小说续写的后记,令特隆故事更有意义。--它谈到幻想世界如何进入了真实世界。耐人寻味的,也许不是刻有特隆字母、像睡着的小鸟般轻柔颤动的神秘罗盘的偶然被发现,或成人才勉强拿得动它、小孩却根本没力气拣起的一个指头大小的锥体带来的可厌和可怕,而是特隆对既存语言的渗透方式。既存语言像池中的蓄水,它能够稀释那滴唤作特隆的蓝墨水,却也一定被滴入其中的蓝墨水特隆多少改变了它的颜色。正是这种改变,让人联想到翻译对译者使用的语言和那种语言之文学所做的事情。你听说过,钦定本《圣经》是翻译改造语言的多么好的例证;你也听说过,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和庞德的“中国诗”,如何表明了文学翻译不仅是以不同于原作的素材和法则进行临摹,而且是用新的素材和法则去再发挥、去再创建原作的努力(有如贝聿铭,在卢孚宫前安放的是一座玻璃金字塔);但它们都不如在现代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翻译实践,更足以显示其发明新语言、设计新文学的作用和意义。那蓝墨水特隆在汉语的池中造成的景观,细想起来几乎让人不敢相信:它不仅改变了池中之水,更似乎改变了整个蓄水池,--它使得之后汇入流出其中的水,看上去总也带一点蔚蓝。--现代中国的诗歌样式、散文样式、小说样式和戏剧样式,特别是被称作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样式,它们哪一样不是由翻译造就的蓝墨水特隆幻化开来的?它们形成的语言现实里,如此现实地吸收了翻译描述的特隆。并且,那种蔚蓝,没有让人将对它的烦恼持续太久。
甚至,因为翻译“外国文学”而遭改变的现代汉语文学,已让人浑然不觉、不记其有异。尽管仍会有滑稽的提醒:会有人痛心疾首起来,批评小说家蹈袭了翻译小说的样式,批评诗人们动用了翻译语言之蔚蓝。--只不过,这刚好又可以是反方向的例子,证明从惊人到迷人的现代汉语文学景观的来历,被忘怀得多彻底,--责怪者没想到,他用以痛心疾首的文章样式,也正蹈袭自以往(不管是否翻译的)文章样式,其痛心疾首的语言,也是被染色的。那悖谬的固执引人注目:认为文学翻译玷污了现代汉语及其写作的“原创纯洁性”,进而懊悔,“外国文学”已经由翻译,属于了现代汉语文学之过去,--像那个小说的叙述者(而我读到的是那个译述者)谈及的:
在记忆里,一种虚构的过去已经取代了另一种过去的地位。关于这种过去,我们什么也不能明确地知道--就连它是虚假的也不知道。
那么,这样的忧虑仿佛有见地吗?--再不警惕那仍在进入现代汉语文学的、被我假设为翻译虚构之特隆的“外国文学”,也许,于不知不觉中,现代汉语文学的现实会反成为乌有。从那篇小说里,你也能读到差不多的忧虑:由于现实世界朝特隆“这个有秩序的星球的细微而广阔的证据屈服”,由于“与特隆的接触,以及特隆的风习,已经使这个世界解体”,由于“一个孤独者们(我忍不住想在括弧里提示你:为什么不把他们想象为翻译家?)的分散的朝代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作为一种估计,“从此以后一百年,就会有人发现一百卷的特隆第二百科全书的。”,--它的后果则不堪设想--
到那时候,英文,法文,以及纯粹的西班牙文都要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世界就是特隆。
小说却紧接着说:“但我并不在乎,”小说给出了一个十足博尔赫斯式的结尾(译述者已将它操练得那么纯熟),“我照样在阿德罗格城旅馆的宁静日子里继续修改勃朗的《尸灰瓮》的克维多文体译文的未定稿(我根本不想拿去付印)。”
竟然在最后涉及了我的兴趣所在。很可能,正是那貌似闲笔的结尾,提醒我将这则特隆故事,跟我感受中的文学翻译取得联系。而这种联系,我相信,为我打开了被我的阅读一带而过的幻想的秘密。我再次去注意我并不曾忽略的一句话--“特隆是一个迷宫,然而是一个由人所规划的迷宫,一个命定要由人予以解开的迷宫。”--意识到我还是忽略了它,没觉察它里面扭转故事进展方向的那股力量:它使得整个故事的讲述口吻多了点戏谑,令特隆故事忧虑的远景,听上去不过是这故事包含的真正虚妄……
在“拉莫斯·梅希亚城的高纳街上一座别墅的走廊尽头”,在“阿德罗格城的一家旅馆里”,都高悬着“令人不安”的镜子。特隆故事正是从这两处镜子的“幻影深处”向你展开的。实际上,特隆故事就是一个镜中故事;特隆世界,也无非一个镜中世界。镜子的虚构能力,它设置迷宫的规则,在于它对摄取之现实的变向和变形,被幻想出来的特隆,则体现和服从了镜子的这种能力和规则。并且,镜像必须取决于镜子。镜子作为一种现实,是不能被摄入镜像的现实。镜子的被摄入,需要另一面相对的镜子。尽管特隆被假定为一个平行于真实世界的幻想世界,映出特隆世界的镜子,却是那属于真实世界的、将它捏造和虚构的语言。无论臆写了《特隆第一百科全书》的语言,企图令特隆世界进入真实世界的语言,或有可能面世的特隆第二百科全书的语言,都是同样的语言,人的语言,照耀人之世界的魔镜。特隆的幻象,其迷宫性质,正是由语言魔镜所赋予。特隆不构成另一种语言,它并非相对于人之语言的另一面镜子,能够令真实世界成为其镜中的一个幻像。不过,--我将要羼入已经用过的另一个比喻,--特隆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悬空着映入语言蓄水池、成为其镜像的那滴蓝墨水,它并且滴破、化入了蓄水池之镜。故事的奇想是:特隆由镜像融合进镜子。
然而,这种融合进镜子的镜像,并不真的会像某种忧虑,渐变成与自身相对和相反的另一面镜子。蓝墨水特隆滴入后复归平静或再不得平静的语言蓄水池,是同一面镜子,仍然体现着语言魔镜一贯的胜利。正如“蓝墨”水是一种蓝墨“水”,特隆对既存语言的渗透,其方式也无法是非语言的;即使被发明出来的可能的特隆语,也必定是一种人的语言。融合进镜子的镜像不过是特殊的镜像,由语言幻想的特隆世界,根本只属于语言世界,哪怕它充斥、占领了人的全部语言世界,它依旧只属于语言世界。--语言世界不会反过来属于特隆、消失于特隆,就像你没见过,打碎的镜子里还会有完好无损的镜像。
来自特隆故事的消息,被我接收的,现在看来,不是幻想世界进入真实世界的消息,而是语言世界接纳幻想世界的消息。在读到“现实几乎立即在不止一点上向后退让,而且事实是,它渴望着退让”的时候,我会把“现实”理解为“既存语言”。由于幻想世界无非是语言的发明创造,那么,那消息报导的,并不是一种语言自身更新语言世界的方式吗?当特隆故事被看作了寓言,那些被假设为虚构了“外国文学”之特隆的翻译文学,除了是汉语的镜中之像,还能是什么呢?翻译文学的幻想法则和描述方式,除了是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的,还能是怎样的呢?现代汉语通过文学翻译,跟通过其写作,要做的无非是同一件事情,--去建设现代汉语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实际上,对现代汉语而言(就像对别的语言而言),文学翻译也是写作,只不过这种写作对现代汉语的特隆意味,使它总是被当成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一种现实之未来,而当这种现实之未来融入了现代汉语文学的现在,它又立即被当成了影响现代现语文学现在的过去。翻译文学常常仿佛并不是现代汉语文学的现在,--它常常被以为是跟现代汉语文学相对的另一面镜子。然而,它并不是。它的想象力,翻译文学而不是“外国文学”的想象力,只有在翻译者所用的语言中才可能实现,它应该被视为现在进行时的现代汉语写作。我的阅读感受,倾向于认为我所假设的并非假设,或那假设首先并不是假设。因为,我知道(这也毕竟只能算常识):我所面对的翻译文学,首先是属于汉语文学的;一种伟大的汉译作品,首先证明了汉语的伟大;一滴汉译的蓝墨水特隆对汉语的池中蓄水的改变,首先是由于汉语改变自身的意愿、其改变的可能性和值得被改变;伴随着现代中国的翻译实践,被认为跟文学翻译脱不了干系的,新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样式的形成,尤其是现代汉语的发明和渐趋成熟,首先是汉语及其文学自身的急需和自我创造。在我看来,对翻译文学的接纳,是汉语文学的自我接纳。汉语几乎是梦见了被称作“外国文学”的特隆世界,并且用翻译的方式将它们接纳。被翻译描述的“外国文学”并不构成汉语文学的所谓“借鉴”,它奇异地融合进汉语之镜,有如蓝墨水溶化于水中,--它甚至不能被说成是池中蓄水的一部分,它几乎无处不在现代汉语的文学之中了。
对特隆故事的谬谈、将它跟文学翻译的个人化牵扯,我不想再去多作发挥了。要经由特隆故事说出我眼中的翻译文学(它并非有些人误认为的“外国文学”)的想法,很可能,早早就埋藏在我初读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的经验之中了。那是在十七年前,我对那个小32开平装本封面上特异的蔚蓝印象深刻,--它填充在H形图案的上半部分。有一回,闲聊过对这种蔚蓝的喜悦之后,我听到一个比方,说那H形图案正欲发展成蔚蓝的U形,就像现代汉语文学,会完全失守于文学翻译带来的影响。这比方添加了闲聊的乐趣和严肃性,让我在又提及H形图案里的那种蔚蓝时总要记起它。不过,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同意“失守”那么个被动的词儿了。--我也不同意,由于文学翻译表面上对现代汉语写作的巨大影响,而把它形容为写作的众多父亲里一个易于被确认的父亲。实际上,文学翻译也是写作,是现代汉语的写作成果,假如它竟然像一个父亲,它的父亲形象,也一定是写作这儿子生养出来的。在文学里,儿子的能耐造就父亲,博尔赫斯则引述艾略特:“作家的劳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概念,也必将改变未来。”考虑到我前面说过的,翻译常常被当成现代汉语写作的未来和过去,这一引述就相当贴切了。而当文学翻译是现代汉语写作的现在进行时,它就是写作的主动选择。现代汉语的文学写作“获取”它的翻译文学,--“失守”的说法,过于不确切。
我相信,每一次真正的文学翻译,都能从写作中找到理由,文学翻译的标准,也就是写作的标准。正是出于写作的理由,正是以写作的标准为标准,现代汉语文学经由翻译拓展自己疆域的能力才值得惊叹。一个事实是,从文学翻译得来的阅读体会和想象,必定跟“外国文学”原作读者的体会和想象强烈地不同。汉语,现代汉语,它的声音和气质如此紧密独特地跟我们的民族感情和感受产生关联,现代汉语的翻译文学作品,只能强烈地不同于也许对应于它们的“外国文学”原作,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学作品。老口号叫嚷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用我们的民族语言虚构描述的文学之世界图景,也正是我们的经验、记忆、传统,以及新写作的背景和出发之地。
(2000.4)■〔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