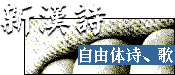很久没有人给我写信。
我在等着一封信。
“我有着骆驼一样的耐力。”
在一幢20层楼的顶层,
在一个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梦中。
一封信已草草写就。
一封信被轻轻地放在眉棱上方。
我权且这样认为,
我权且这样说,并且说:
“在‘自由’和‘规则’的背面,
太阳照常升起。”
你是另外一个人,
你是一个只在春天的早晨才及物的人。
就像一个动词,
它的属性需要不停地变化,
但只限在春天。
我想,在这首诗里
描述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方便得多。
一本英汉对照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
一本早已打开的英文词典和我的诗。
(在这首诗里出现“我的诗”
是件不光彩的事。的确!)
我一边读,一边喝茶,一边伸手推开窗户。
出现在面前的是
挤在一起的高楼和楼下的人群。
它们都是物。
如果它们在这个下午能喝上你沏的茶,
它们会说:“3月28日,摄氏25度,太好了!”
仅仅因为你的茶,它们
出现在一本小人书里,
它们将喜欢上冷霜的恐怖故事。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身边,
就像你在一首诗里推开我虚掩的门,
就像我午睡的时候,隔壁的人在高谈阔论。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我们的生活也不见得就枯燥无味。
■
他,在乌鸦的叫声中降临人世。
乌鸦:他感应事物的,一张牌,
从不在赌场使用,也很少谈论。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他很少有什么态度,
且远远地避开。(其实,
他很聪明,并非无能,
如稍事用心将游刃有余。
“聪明才智浪费在这里实在可惜,
虽然,我浪费了很多。浪费吗?
也许,我错了?”他这样说的时候
总是心不在焉。)他像独行侠
生活在他居住的城市(内心上的)。
他很少和地方上的“大人物”打交道,
像人大会议从不参加(参加过一次),
虽然他十九次当选为人大代表,
从县到省到中央,犹如芝麻开花。
“谁和我去散步?”这是他
每天晚饭后都要问的一句话。
一家人没一个搭腔,即便
他那臃肿不堪的老婆。“婚前,她
几乎是县里最漂亮的美人(美人也要分出个
三六九等),生完孩子就变了个样。”
身为丈夫的他可不这样认为。
他喜欢肥胖的女人,他的审美
停留在唐代,杨贵妃仰慕的女英雄。
“我受不了江南水乡潮湿的空气”,
这仅仅是他离开家乡的一个借口。
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为此
饱经妇女们的冷嘲热讽,他毫不在意。
他,我的好友(并非生拉硬扯,
虽然我们的友谊诞生于一场械斗)。
他的烟瘾特别大,经常被老婆叱责。
“恶习难改”,他总以这句话
掩饰无处躲藏的尴尬。
“好一张脸孔!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在他六岁生日那天,一位算命瞎子
闯进他的家门。“为了图个吉利,
母亲就让他摸着我的脸,算着我的命;
那瞎子算走了我的生日礼物:一个鸡蛋。”
失去礼物的他整天都哭丧着脸,
心里却在琢磨“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小小年纪就懂得制造平衡。”
漫长的童年,八年抗战般难熬。
八年一过,日月如梭。如洗的日子
令他憎恶算命的瞎子:“兀立的一句,
既没有时间,更没有地点……”
他,热爱家庭生活的男人,
喜欢做家务:洗衣做饭什么都来,
乐得他老婆屁颠屁颠的。
也招徕不少讥讽,一样不在意。
一个过惯家庭生活的男人,离开
老婆的日子比漫长的童年还要难熬。
他四处收集各式各样的征婚启示,
一有闲暇就坐下来阅读:“又一个
肤白貌美,还可大她十几许……
十八岁开始征婚,十九岁干什么?
皮肤细腻的五十七岁,谁能耐得住寂寞?”
他一边取笑,一边感慨。
他总能让生活多一点乐趣。当然,
他也有苦眉愁脸、怒发冲冠时。
这种场面难得一见,他宁愿
让怒火在内心燃烧,烧得他满脸通红。
每当这时,他就独自一人步行到城外。
为何抛妻别子,来到异乡他只字不提。
闯荡天下他不热衷,游山玩水没有兴趣,
狎妓冶游更不是他的脾性,谁知道呢?
虽然,他有的是钱。啊,腰缠万贯。
“钱!是个好东西。真他妈的好!”
对钱他还是有态度的:“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他的豁达缘于他的遭遇。
他的遭遇适合在小说中出现,就像他的爱好。
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县城图书馆里的
每一本书他都读过,连女儿的
生理卫生课本也要读上一遍。
“生理卫生,重要得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读书,他隐秘的私人生活。
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从不写书。
著书立说,是别人的事。他
连一封信都懒得写。(他的懒是出了名的,
用我家乡话说:“懒得屁眼掏蛆”。)
出来快三年了,一个字都没给家里写。
“读那么多书都不知干什么去了!”
家里人对他这种行为怨气冲天。
是啊,家里毕竟出了个读书人。
“这哪像个读书人。屁!丢人现眼!”
他父亲愤怒的唾沫星溅了我一脸。
“什么是读书人?”我疑惑了很多天,
最终也没搞清。他,一笑了之。
不能再这样写,再写就把他写成个怪人。
赞美他几句?他一度是
地方名流(人大代表,生活的一个侧面)。
“名流是用钱堆出来的!”这是他的名言。
他早已厌倦做一名小镇名流。
其实,他也算不上什么名流,
他极少参加名流们的聚会,
名流们具备的派头一样也没有,
还时不时地攻击名流们的作派。
天长日久,被驱逐出“名流圈”。
消息传来,他大摆宴席庆祝了三天。
说句心里话,他懊恼不已。
他从舒适的家庭生活走了出来。
类似于他十七岁的那次奇遇:
“……那个人快饿死了,那个人
就是我师傅,也是给我算命的瞎子。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瞎子,
只是混口饭吃。他是个高明的医生,
却永不行医。他把医术传给了我。
他一生贫困潦倒,渴慕着荣华。”
他今天富裕的生活全凭那瞎子的医术。
他二十岁行医,八年后名满“天下”。
救死扶伤,他不可动摇的医德。
哦!赞美是邪恶的隐喻。
装怪!是我们的一大美德,
具有深厚的美学基础。“再说,
怪有什么不好!” “我
父亲有个怪僻,总爱在阴雨天
谈论他早年的风流韵事,母亲
乐呵呵地听着,不时还提个醒……
我父母晚年生活不可缺少的乐趣。”
他毫不避讳地谈论他的双亲,
他爱他们,他的爱充满了温情。
■
1
我住在小镇的边缘,运河的北侧。
对这座苏北小县城没什么好感。
狭小,自然就拥挤;狭小又使人好斗。
1980年的这座苏北小城破败不堪,
没有所谓的改革初期的活跃。
这里的人斤斤计较,恨不得将满地的石头
一个不留地捡回家。噢,满地的石头,
哪一块能接近我?我心不在焉地
在运河堤上游来荡去。河面上
船来船往,小城似乎繁荣得不行。
2
现在,1997年8月27日
晚上11点54分。光阴似箭,
一点也不过分。浓稠的光的密度稀疏了。
白发苍苍的父亲又在调换哪个频道?
高血压冠心病的父亲,十五岁
就远离家乡,扛枪打仗。
非凡的经历如今在折磨着他:
葬身火海的母亲和妹妹,
长达一百五十华里的奔袭,
从苏北平原到江西丘陵的
携家带口的讨饭生活,出其不意的
某位领导的莫须有的暗示。
当然,这里不能排除他的继父,
“我一辈子都不准备原谅,
他的死罪有应得。”古稀之年,
父亲在轻松地对待死亡。
“不就是死吗?”听上去毫不在意,
其实是在赌气。母亲为此恼火得很,
生命来之不易啊!我的外祖父,
民国中期的地主,千顷良田转眼即逝,
到母亲出嫁时已没什么可以陪送。
3
偌大的空间消失了,
这是我回家的错觉。时代的
步伐在家乡越迈越快,东西大街似乎要
宽过长安街,姑娘漂亮不过小媳妇……
这些都是时代的特征?“是吧,也许是吧。”
我在心里暗自嘀咕。
富裕的生活改善了人们的心境。“出门遇见泗阳人!”
来自周边地区的诅咒越升越高,
我不明就里,他人心里雪亮。
4
按长幼秩序,下面我该写长兄长嫂。
很久没给他们写信,并捎去问候,
哪怕是假心假意。此时
该加进一个人物:姐姐。
为了弟妹们不受阻碍地读书,
很小就开始做工,江南的农活异常繁重,
为多挣一个工分兄妹俩
起早贪黑,顾不上吃饭。
写到这里不禁鼻子一酸,眼泪落下。
如今,姐夫离去,丧偶的
姐姐带着女儿维持着生计。
生活不免让人痛心,热情就这样在递减。
孩子们的生活还是
快乐的,无忧无虑的。
5
关于泗阳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在那里虽然有很好的朋友,但永远只是
一个中转,哪儿又不是呢?
逃荒的父母把我生养在赣北农村。
我总爱说:“我喜欢那里。”
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可说的地址。
不可说的是我在梦中经常回到那里,
而小伙伴们一个也记不起来。
记忆在领略什么是残酷,我在领略什么?
生活不断地排出污水、施放噪音、
制造假象、树立英雄。噢,
没有隐私的社会,小道消息
传递得比互联网还快,堆积如山的政治笑话,
打发光阴的不可缺少的素材。
家乡,家人:两个微不足道的名词。
(1997.3.28-8.28)■〔寄自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