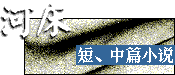熙熙攘攘的都市,梦影幢幢的都市,
鬼魂在光天化日之下拉行人的衣袖!
--波德莱尔
我在小时候碰到过许多离奇古怪的事,对于我那稚气洋溢的心灵,这些事自然是不可理解的,且其中的大多数后来也都忘了。少数留有印象的,长大后则都变得可以理解了。惟独有一件事是个例外,随着年岁的增长,它越发变得不可理解了。在夜深人静之际,有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事来,并细细地琢磨事情的全过程。我发现它不仅显得离奇古怪,且给人以倒吸一口凉气的恐惧感。我还发现,对付它的最好办法不是去深究它,去设法理解它,而是尽快把它忘了,忘得越干净越彻底越好。
那时我还在念小学,从小学二年级起,每年暑假,我都要到一位姑妈家过上半个来月。姑妈家虽然是在大城市里,但照我看来,她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的意思是,家里的摆设丝毫也不比我家好到哪儿去。但有一台熊猫牌录音机却是我们家没有的,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它的型号,叫L04。对于普通的城市家庭,这东西可算是稀罕之物,是姑妈省吃俭用了半年,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老实说,这台在当时颇为先进的收录两用机对于我,比姑妈家的饭菜甚至比姑妈本人都更具吸引力,像现在的小孩子喜欢郭富城张惠妹一样,那时的我喜欢蒋大为苏小明。
姑妈没有孩子,看样子再也不会有了。她曾有过一个孩子,名字还是我爷爷给取的呢。我曾在许多场合下听爷爷讲过瑜儿的死。有一年夏天,瑜儿来我们家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在临走的前一天,脚底板戳了一根生锈的钉子。上火车时,瑜儿还是好好的,只是行动有些不便,火车过了徐州,就不对劲了。他感到头晕,还感到冷。为了对付头晕,爷爷就往他的太阳穴抹万金油;为了对付寒冷,除了把自己的中山装给他披上外,又往别的旅客要了六神丸和阿斯匹林--那时即便是治感冒,药物也是很贫乏的。但瑜儿还是死了,就在火车减速进站时死了。爷爷每次讲述这事,就无限后悔,他怎么没想到给瑜儿打一针“破抗”呢。但那时的“破抗”是珍稀药物,需要开后门,且那时的人也没什么卫生常识。爷爷摸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叹息道,这孩子多乖啊,他总共只喊过两回冷,第二回喊冷时,脸和嘴全都紫了。他还说,他再也不给孩子取名字了。
瑜儿的死是我每年夏天都要在姑妈家呆上一段时间的直接原因,似乎这样就能减轻全家人尤其是我爷爷的愧疚感。后来我才知道,我格外讨姑妈喜欢,多少还因为我长得跟瑜儿很像。我肯定是见过那位比我长六岁的表兄的,但他离开我家时我才刚满五个月,因此毫无印象。出于避讳,小时候也从没有人向我指出这一点。至于我,当然是非常乐于去姑妈家的,我在那里享受上宾的待遇,要火车有火车,要遥控汽车有遥控汽车(以我的年龄,已有些不宜玩这种幼稚园里的玩具了),至于逛公园看电影下馆子等,也多少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了。我在自己睡的那张单人床下还发现了一抽屉落满灰尘的像章,各种形状、各种姿势的都有,最大的简直比中号盘子还要大。姑妈说,这些都是文革中闲得无聊的姑父收集的,他放弃了集邮爱好,改为收集像章。大城市毕竟是不一样的,它至少能使姑父收集到那么大的像章。小时候我也曾见过不少像章,但最大的(说来可笑)只有小碗大。不过我所说的那件离奇古怪的事不是指这个,它发生在我准备上五年级并开始迷恋熊猫L04的那个暑假里。
记得那天吃过晚饭后,姑父有什么事出去了,我躲到小房间里,守着那台铅灰色的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磁带是姑父从黑市买来的),在把带子从A面翻到B面时,忽然从楼下传来一阵鼓乐声,还夹杂着尖锐的小号声。我以为这是另一台录音机发出的,但很快便发现这是实况,是地道的实况演奏。我把脑袋由窗口探出,发现声音时高时低,乐队并不在楼下,而是隔着一栋楼,在后面那栋楼之后。假如我把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继续听下去,就不会遇上这档子事了,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却有些失魂落魄,好奇心飞到了窗户外面。
我来到大房间里,电视机的反光一亮一暗地映出一个人影子,姑妈正在看电视。她似乎被深深地吸引住了,竟没有立即觉察到有人进来了。在姑妈家,我从未受到任何的冷落,连一秒钟的怠慢都不会有。也许电视里的内容实在太精彩了,我顺着姑妈的视线望去,遗憾的是,小小的黑白屏幕上的镜头却是市领导参观某啤酒厂的流水线,属于最枯燥的地方新闻。天已经有些黑了,姑妈没有开灯,却把搁在高低柜上的电视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至少比往常大。我站在她身旁稍后处,头一回发现姑妈的背驼得利害,在昏暗中显得又瘦又小,几乎缩成一团。我觉得姑妈好像有什么心事。
姑妈转过头来,朝我笑了,见我的嘴唇动了两下,便起身去小关音量。我又听到了窗外的鼓乐声,于是我说:
“姑妈,我想到外面玩一会儿。”
“想去看热闹?”姑妈猜中了我的心思。
“嗯。”
“后面的楼里,有个老太太死了。”姑妈直了直腰身说:“老太太活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是喜丧。”
原来姑妈什么都知道。既然外面这么热闹,为什么不带我去看呢?姑妈可是什么好玩的地方都带我去的。何况又是喜丧!我还从没有见过喜丧呢。这时传来了一阵急切的锵锵声,我看见姑妈哆嗦了一下,又缩成一团,仿佛那不是一阵急切的锣声,而是一阵凛冽的寒风。但我一心只想着自己的事。
“我看一会儿就回来。”
“这么晚了,就别去了。你姑父又不在家。”姑妈有些吃力地说。
“姑妈,我都这么大了,不会跑丢的。姑妈,我去一下就回来。”我撒起娇来。
姑妈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终于放行了。我一溜烟地下了楼,耳边的声音却变得很弱,直到我绕到后楼的侧面,才遽然大起来。在楼间的空地上果然搭着一座敞口的棚子,昏黄的灯光照见一堆乱糟糟的人影,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
我走近围观的人群,正赶上乐队暂停演奏。我从人缝中一眼瞥见了死者的遗像,它被供奉在桌子的一端,旁边站着两个纸人,真人般大小,模样就像古代的丫鬟,棚子的后壁上则挂着许多花圈,最大的那个花圈正好在遗像之后。姑妈说得对,那的确是个老太太。桌上点着三支蜡烛,摇曳的烛火使老太太的脸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黄。从那凹陷的面颊和突出的颧骨看,老太太嘴里的牙齿想必不剩几个了,她还有兴趣尝一口供桌上摆着的水果、点心和凉菜吗?
在我看来,围观者都抱着平和的或漠然的态度,他们中的多数是妇女。奇怪的是,竟有许多女人吸烟,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尤其吸得利害。天已经全黑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拿着手电,在人丛中乱走。他忽然将手电光对着一个女人,原来他在跟女人怀里抱着的一个更小的男孩开玩笑。孩子的母亲连声说别闹,他才嘿嘿地放下手电。
我挤到入口处四下张望。棚子差不多有三层楼高呢,架子是用铁管子搭成的,上面覆着绿色的帆布。供桌的左侧是乐队,此刻正坐在条凳上休息;右侧则有好几张桌子拼在一起,许多人在喝酒,搛菜,小声地说话,其中有四五个还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显然是前来吊丧的亲友。那一侧还有两个临时砌成的灶台,烈火熊熊,搁在上面的水壶卜卜作响。不一会儿,水壶被一个系围裙的女人提走了,往上窜起的火焰使棚壁增辉,使一本正经的脸庞泛起红光。
有一样纸糊的东西唤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它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开始我没有注意到它。这是一辆由怪兽牵引的纸车。一个双手握着铁管子的小女孩见我好奇地盯着那头虎黄色的怪兽看,便好心地告诉我那是纸马。那是纸马吗?它的后半身虽然像马,且背上搭着饰有碎花的马鞍,但在竖起的耳朵旁,却多长了两只弯弯的牛角,且它的脖子又粗又长,与马的身体不成比例,所以它还是一头怪兽。在怪兽身旁站着一个脸蛋红润的牧童,头戴浅黄色的斗笠,身穿紫色长袍,脖子上系一朵大红花。姑妈说得对,的确是喜丧,否则怎么会让那孩子打扮得像新郎官似的呢?而那辆纸车,使我想起了正月十五的兔子灯。与又小又丑的兔子灯相比,它是多么漂亮精致、绚丽多彩啊!纸车的帘是粉红色的,顶是雀绿色的,围子是紫黑色的,轱辘是橘黄色的,在元宵节的那晚能拉上这样一辆车,再在车里点上一根粗蜡烛,那该多美啊!
我那幼稚的美梦很快就被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打断了,乐队又开始演奏了,有七八个人在拼命地击鼓敲钹。我觉得这声音很过瘾,但当我看见那个跟我说话的女孩捂住双耳时,便也学她的样子捂了一会儿耳朵。一个挤在前面的老头退场了,他用一只手虚罩着耳朵,像是在表明:我很想看下去,可是我的耳朵受不了啦!他们敲累了,便被安排去喝酒(原本是亲友坐的地方已经空出了),换了一帮吹号吹喇叭的人。有两只喇叭很奇特,是由许多长短不一的金属管子排列成的。后来我才知道那玩意儿叫排箫。有一个吹小号的,时而把号从嘴巴里移开,微仰着头,眼睛半睁半闭地喃喃自语一番,仿佛在祈求上苍给他力量,以便吹得更响。还有一个穿白背心的男人,嘴里想必塞了什么,从他那鼓涨的腮帮子里发出尖锐的响声。那汉子使劲晃荡着上身,脑袋一会儿抬起,一会儿低下。他抬头时,头顶的灯光垂照在胸口上。那胸口红通通的,油晃晃的,显然冒汗了。
他们吹了很久才停下,我以为该结束了,而我也该回去了,姑妈也许已经等急了,不想他们只擦了擦汗,便又开始了。这回吹的是主题联奏,其中竟有我熟悉的曲子,什么蒋大为、苏小明、李谷一等人的流行歌曲,统统都串上了。调子虽然不很准,我觉得还是比听录音机强。毕竟这是实况演奏呀。我越是想回去,节目却越是精彩了,有个女人换了身红缎子衣服,和穿白背心的汉子唱起谢莉斯、王洁实的二重唱及《夫妻双双把家还》。女的甜甜地唱一句“你耕田来我织布”,男的便粗犷地跟一句“你挑水来我浇园”。还有人扮成小丑演起闹剧来。周围的人开始发出阵阵的喝彩声。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热闹的送葬呢。我算是大开眼界了,要不是出了那事,我肯定会把我所见到的这一切讲给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小伙伴们听。他们也跟我一样抱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人死了应该哭得天昏地暗才对。
那些去喝酒的人又过来了,还披上了绣金线的红袈裟,简直跟电视上唐僧穿的一模一样,只是帽子差点劲,是一种小黑呢帽。他们像方才那样把鼓和钹敲得震天响,然后鱼贯地走出棚子,咚咚锵锵地进了一座黑漆漆的门洞。以我幼稚的知识水平,此刻也能猜出他们这是上哪儿去。他们显然是上死人的家里去,至于去干什么,我也知道了,因为人群中有个声音在说,这是要把死人的魂带出来。那件令我羡慕不已的纸活(这个专有名词是我后来知道的)这时已摆到了外面的水泥路上,在怪兽粗大的脖子下,还多了一只红色的塑料水桶。它也会口渴也要喝水吗?一个小男孩拎着一对纸箱走到怪兽前,纸箱也是红色的。
披袈裟的人咚咚锵锵地出了门洞,又回到棚子里。两个中年妇女在往一只搪瓷脸盆里投纸钱,盆里积了很多灰,想必纸钱已烧了很久。老太太在接受了这一大笔钱后,似乎显年轻了,尽管摇曳的烛火依然使她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但眼睛里始终流露着满意的神情。她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她在人世间潇洒地走了一回,挣足了寿数,临行前又办了隆重的仪式,给了足够的生活费。
乐队再次走出棚子,站到水泥路上。转眼间,就有许多人在路上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在最前面的自然是拎红纸箱的小男孩,但那个拿手电的小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也站到了前面,且提起了水桶。在到处都是路灯的城市里,难道还要打手电吗?怪兽拉着纸车晃动起来了,整个队伍也缓缓地跟着移动。我发现这时的鼓乐声才是最大的,响得连“震耳欲聋”都不足以形容了。
我站在路旁,看着面前这支熙熙攘攘、半明半暗的队伍。那几个前来吊丧的老人就站在纸车后面,棚子里的灯光朦胧地洒在花白的头发上,使他们除了德高望重外,又平添了一层神圣庄严的色彩。在人影幢幢的暗处有一个小光点,当光点移到棚子的敞口前,我发现原来是一只插在木鱼上的小灯泡。那木鱼竟有小脸盆大,挂在一个壮汉的胸前。壮汉用小木锤不停地击打木鱼,嘴巴还不停地动着,在念什么咒语。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去一个遥远的地方,而我也该回去了。我在外面呆的时间太长了!一想到姑妈在昏暗中缩成一团的形象,我就感到内疚和不安。姑妈今天本来就不开心,难道要让她再为我烦恼吗?
手电光的光圈在一堵红砖墙上移动着,放大着。两个小男孩尽管走得很慢,却开始拐弯了。我既担心又害怕,既紧张又兴奋,当手电光划向雾蒙蒙的夜空时,竟鬼使神差地挪动脚步,跟了过去。我将被这支神秘的队伍引向何方?最终将出现一幕什么样的景象?
人群走得很慢,有时竟完全停下了,使人觉得随时都有倒回去的可能,但队伍还是出了住宅区,上了一条较宽敞的柏油马路。迎面驶来一辆汽车,强烈的灯光剪出许多镀着金边的黑影,它似乎被眼前的这幕奇怪的景象吓着了,胆怯地鸣了一声短笛,掉头就往回跑。
人们乱糟糟地散开了,像出了什么事。原来他们站成了一个圆圈,被围在中央的正是怪兽、纸车一类的纸活。这是干什么?我正纳闷着,突然间升腾起一片大火来,纸活被点着了!我迅速挤到前面,死者的家属正跪在柏油路面上哭泣,哭声是如此嘹亮,尽管这时的鼓乐声超过以往任何时刻,我也能清晰地分辨出来。不管怎么说,到最后还是要哭的,我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纸车的轮子着火了,怪兽趴到了地上,只剩下脖子以上的部分,两个丫鬟也倒下了,大火正在吞噬除塑料水桶外的一切“陪葬物”,无数的灰烬随着熊熊的烈焰高高飘起,仿佛要托举什么。它们也的确托举了什么,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被托起的是一个人!我揉了揉眼睛,在火焰和灰烬之上的还是一个人,且就是那个老太太,跟遗像相仿的是,她也只有上半身。老太太的脸红扑扑的,也不知是涂了胭脂还是被火光映照的。她肯定是来表示感谢的,然而我却发现在跪着的亲属中,有人明显地感到不安了。那是个谢顶的男人,约摸四五十岁,极像是老人的小儿子,他要比两位满脸皱纹的女人显得年轻,那两位女人很可能是他的姐姐。跪在地上的人并不多,想必只有直系亲属才有资格。谢顶的男人尽管没有停止哭泣,但他的双手在发抖,眼珠子在滴溜溜地乱转,似乎既感到恐慌,又在琢磨对策。他抹了一把眼泪说:
“妈,我们送您老人家来了。您的儿女,您的三个儿女都来了。”
略一停顿,谢顶的男人又指着跪在对面的两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说:
“还有您的孙儿,外孙和外孙女。妈,您都看见了吗?”
孩子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指着他们。他们沉浸于悲痛中,对眼下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他们虽然不像大人那样呼天抢地,但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哭泣都发自内心深处。
“我都看见了。真难为你们了。”从火焰之上传来一个声音,声音不大,还有些嘶哑疲惫,但听上去,那的确是一位老太太的声音。
“妈,您在那边还缺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缺,只是不大明白--”老太太欲言又止。
儿子的脸腾地红了,他慌忙叩一个头,痛苦地说:
“妈,恕儿女不孝,不能把您的事办得隆重些。”
“不是不隆重,是太隆重了。”
老太太话中有话。谢顶的男人慌忙又叩一个头,很怕老太太会说出什么来。
“妈,我知道它们太寒碜,不中您的意。我真想给您送一辆四轮马车,由两匹大个儿的‘菊花青’驾辕,前面有一匹顶马,后面有一匹跟马;还有,那鼓乐和供饭也过于简单了,可咱家的条件……再说,在提倡移风易俗的今天,根本就不让搞这种活动了,我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让居委会睁一眼,闭一眼。”
“那为什么还要搞呢?”
“妈,不管怎么说,这是晚辈们的一点孝心啊。”
“你们的孝心我领了。”
“您这样说,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做娘的不是跟你们过不去。我且问一句:你们有钱糊这些纸车纸马,请一帮人吹吹打打,为什么不给我治病呢?”
我看见儿子的脖子也红了,腮帮上有一两棱肉在抽搐。
“妈,您得的是……不治之症。”
“是啊,我得的是肠癌,治不好。可是假如把那一小段肠子切除了,我至少还可以多活三五年。”
“妈,您别说了。”
“我已经八十多了,耳也背了,眼也花了,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何必花这冤枉钱呢。”
“妈!”
老太太似乎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架势,她要说,要滔滔不绝地说,要把自己的苦难与不幸原原本本地说出来:
“可是八个月啊,我在床上整整受了……”
儿子用可怜的哀求声打断了她:
“妈,求您别说了,求您别说了。”
他腾地一下站起来,不知从哪里掏出几张十元的钞票(那时票额最大的就是十元),举过头顶:
“妈,这点钱您先收下吧。不够的话,我以后再给您送。”
他想用钱堵老太太的嘴。这不奇怪,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但他显然是乱了方寸,也许更是慌不择路:连我这样的孩子都知道,给死人只能送另一种钱。我斗胆抬起头来,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老太太,那张方才还是红扑扑的脸此时已成了蜡黄色。我觉得她肯定会拒绝的,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眉梢和眼角竟然牵出几道犹豫的皱纹来。这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我看见老太太眨了两下眼睛,眼窝里满是泪水。不用说,这泪水显然是来自往昔苦难的回响。她应该调整一下情绪,把八个月来的不幸遭遇统统说出来。她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似乎的确在调整情绪,然而没过多久,我发现她的眼珠却偷偷地转了回来,转向那几张钞票,仿佛它们正是她急需的。她并没有伸手接钱,那几张票子却不翼而飞了,与此同时,老太太本人也消失了。
大火转眼间就失去了迅猛的势头,纷纷扬扬的灰烬在空中稍作迟疑,也开始往下坠落了,地面上只剩下纸车的竹架、牧童的斗笠及丫鬟的绣花鞋还在燃烧。谢顶的男人早已跪下了,加入到哭泣者的行列中。从他那抢天呼地的动作看,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也根本没有站起来过。我四处张望,想知道周围人的反应。他们也跟我一样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吗?但他们的表情一律是漠然的,无动于衷的,仿佛的确什么也没有发生。随着火光的减弱,那些无动于衷的脸庞渐渐地模糊成了黑乎乎的一片。我感到很害怕。
我顺着人流往回走,一路上还在想:他们也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吗?我既胆战心惊,又充满着好奇。我真想拽住某个人问个明白,随便哪个人,只要是比我懂事的大人,然而我却没有这个胆量。我竖起耳朵,注意听别人的谈话。他们肯定会谈论它的,就像从电影院里出来的人会谈论刚看过的电影一样。奇怪的是,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不但不谈论这件事,也不谈论别的事,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往回走,仿佛他们不是一群真实的人,而是一群在布幕上移动的皮影。我格外想念起姑妈来。要是姑妈就在身旁,那该多好!不少人又回到了棚子周围,而我再也不敢去那儿了。我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敲响了姑妈家的门。门开了,有人背光地挡在门口,既不是姑妈,也不是姑父,而是一个陌生人。当我看出陌生人是个老太太时,我吓得魂飞魄散,几乎要一屁股坐下去。所幸的是此老太太不是彼老太太,她还告诉我,姑妈就住在前面那栋楼里。
后来我才明白,那天姑妈没陪我去,是因为那场面使她想起了瑜儿的死。但我让她等得太久了,她一点也没有少受罪。进门后,我看到姑妈的眼睛红了,当时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姑父没回来,其实他早回来了,正在外面满世界找我。
像所有的人一样,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会渐渐理解许多以前并不理解的事。当我追忆起这件事的全过程时,对于某些细节,我可以获得了深入的理解,譬如对于那头怪兽及搁在脖子下面的水桶,我就获得了深入的理解:它之所以前半身像牛后半身像马,是丧家为了省钱而把两项功能合起来的缘故。马是驾车用的,牛则是喝脏水用的。按当地的传说,女人一生用水较多,假如阎王爷万一要罚她喝脏水,那条牛就派上用场了。一想起那又粗又长、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脖子,我仿佛能听到从其中发出的咕咚咕咚声!我不但理解了那头怪兽,也理解了包括大脖子在内的每一只器官的功能。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是理解了某些部分,便越是觉得不可思议,且恐惧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顺便说一句,我绝不是怕这种“有钱买棺材,没钱医病”的事将来也会落到我头上。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是不会理解老太太眼含泪水时的复杂心情的,他大概也不会理解何以一点小利就能堵住一张“有话要说”的嘴,使其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忍让与妥协,但一个历尽沧桑的成年人却能够理解甚至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一切。许多年后,饱尝生活艰辛与世态炎凉的我在被抹平了棱角的同时,的确也轻而易举地理解了这一切,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不理解,更强烈的恐惧感。假如我所看到的是飞碟或外星人,我可以以目击者的身份在报纸电视上侃侃而谈--它能给我带来一时的荣誉,满足我的虚荣心。可惜这样的好事从来就没有落到我头上,尽管那种来无踪去无影的方式与飞碟或外星人的行为十分相似。我不但不能在新闻媒体上侃侃而谈,甚至也不能让亲朋好友(包括最亲近我最理解我的人)为我分忧解愁。喜欢开玩笑的会说这是表兄的魂附着到我身上的结果,因为我们长得很像嘛;认真一点的会说这是幻觉,因恐惧而生的幻觉;有恶意的则会说我的脑子有问题了。这尤其令我苦恼。于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如前所述的一条:尽快忘掉它,忘得越干净越彻底越好。我知道这是难以做到的,正如把水手扔到大海里并叫他忘掉游泳是难以做到的一样。
但我还是要努力忘掉它。
■〔寄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