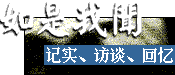对世界文化的眷念
--毛焰访谈
〈毛焰简介:湖南湘潭人,1968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吴晨骏(以下简称吴):先谈谈你本人的创作,你除了画人物之外,还画不画风景、静物?
毛焰(以下简称毛):这一阶段没有画过。很多人从一种表面的层面上,比如从画种啦、题材啦等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一个画家来说,各种选材的方式之间不存在区别。我画的人物与传统意义上的人物、肖像或人像有截然的不同,完全不是一码事。在我的脑子里面,从来就没有想过我是在画某一种东西,比如说我是在画肖像、人像。我只画我关注的东西,而不是说我必须要画某种东西。有一种画家很多,他们必须什么都要画一画,这样的想法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
吴: 在画人物时,你是否选择对象,比如选择画什么样的人物?
毛: 肯定是有选择,但是我的选择也不那么明确。有时这一选择很确定,有时也很随意,没有经过太多的设想。
吴: 你的画上散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光斑,但我同时也感到画面具有立体的效果,你是如何把这两方面处理在同一张画中的?
毛: 大概是靠我自己的一种情绪、一种灵感性的东西,把这两者联结起来,而不是靠一种技法。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技法、语言那个层面上去,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我的认识或我的情绪。我现在不大可能考虑要用什么技法来把某种东西结合在画中。我的那些人物形像塑造出来便有非同一般的、或者至少有一种特殊的效果,这效果当然也包括技法、语言、结构等等。
吴: 你画人物的衣服偏向于选择什么颜色?
毛: 原来偏向于棕褐色的衣服,近期我的作品几乎都只注意脸部的发挥。相对于头部、耳朵、面孔来讲,衣服的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脸部给人的感觉近乎一种呈现,一种实实在在的、一目了然的呈现。我也不是说脸部能带来更多的东西,但它最起码是一种呈现,与我们通常所见的一切不一样的呈现。
吴: 你至今画了多少张油画?
毛: 没有统计过,不算多。画的时间很长,至少也有十五年了,现在回想当初刚开始时对油画的认识,跟我现在相比,那是有天壤之别的,恍若隔世。
吴: 除了艺术的情感因素之外,你的绘画语言与绘画的理念、观念有关吗?哪一方面的观念对你影响比较大一些?
毛: 有关系。但是现在“观念”这个词用得太多了,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扯上“观念”。实际上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观念对艺术家来说是具体的,是艺术家对艺术的基本认识和他对自我的一种判断。观念也许是他的愿望,也许是他的情结或者他的立场,所以艺术作品里面必须要有很明确的观念因素。但是我个人的作品与纯观念性的作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有比较纯粹的观念艺术,方式上相对比较新颖比较前卫。现在我们经常讲的观念艺术,很大程度上与潮流有关系,与时尚有关系,与当代有关系,与波普文化有关系,相对于这个来讲,我的艺术更多地是建立在对古典艺术的理解上,我作品中带有一定灵敏度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我对某些古典艺术里面某种我热爱的东西的一种不自觉的流露,或者一种怀念。所以我作品更多的是与过去有关,而不是现在、今天。
吴: 刚才谈到的那种观念艺术,我感觉其艺术技巧是为其观念服务的,相对于观念,其技巧在绘画上的作用就显得很淡。对观念艺术,你是如何看待的?
毛: 我对此是有自己的认识。观念艺术中很多东西也是我很喜欢的,但是可能因为我很喜欢,反而让我没兴趣。比如像那种装置性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你喜欢就可以了。它的话说得很清楚,它想要的东西也很清楚,它的价值也很清楚,它观念的指向也很清楚,这种东西也只能就是到“喜欢”这个地步而已,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跟我现在画的东西、作品,跟我的追求没有关系。实际上一个艺术家个人化的创作,不可避免所要面临的是他所能要的一切东西,眼前的、记忆中的、想象中的,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每个人对时间的把握也是有限的,艺术家最终的东西说来说去都很简单,就是一种对时间的体验。有的人生活在今天,有的人生活在明天,甚至有的人生活在过去,他们的处境、背景,他们的兴趣和能力都完全不同。从这方面来讲,艺术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有人会说只有艺术才是有意义的,这样说也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一个艺术家面临的东西太多了。
吴: 你怎么看待在油画这个领域中批评家的作用?
毛: 现在不存在油画这个方面的批评家,因为现在的批评家似乎什么都干。我感觉批评家是在干一些事情,但我不太明白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对这些一点没兴趣,他们在发出声音,在说话,而他们在说什么或者说得好不好,我没有太多的感觉。那肯定是因为他们说得不那么精彩,不那么有特点,不那么动听,没什么诱惑力。他们老在说,老在说可能比说得好不好更重要。
吴: 我感到批评家似乎承担了经纪人的某些作用,是这样吗?
毛: 有这样的批评家,他们可能也是客观上的艺术代理人。
吴: 在艺术界,纯粹的经纪人有吗?
毛: 当然也有。我也认识一些。但是大多数是以商业为目的的,那些真正有审美趣味的、有眼光的人极少。中国未来的批评家,包括艺术家、经纪人,他要体现一种综合素质,比方说我们可以提到栗宪庭,他不仅仅是批评家,不仅仅是策划人,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所具有的综合的能力。
吴: 你是怎么看待更年轻的画家和他们在艺术方面的成绩?
毛: 这样的画家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数量的,做得比较好的画家还是很多,包括我对我自己的认识--现在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棒,相当成熟,相当好了,相当有价值或意义了,问题就是他十年以后怎么样,或者他是不是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能够很清楚地认识自己的那种优势或者劣势,这很重要。然后他还有能力去拥有一种自律心理,他有能力去发挥自己,因为确实有一些画家在某一个阶段特别棒,但很快地他就变了,这很奇怪,或者有一个很明显的滑坡,那就很难讲清楚他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当然最终他肯定是与环境有关系,受潮流的影响,受现在这种文化的气氛影响,所以最终真正能够做得最好的只是少数。南京这样的人也很多,这还是艺术家的素质问题。
吴: 在绘画艺术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几位画家?
毛: 在古典艺术中,法国的德拉克洛瓦、德国的丢勒、西班牙的戈雅。这三人是我最喜欢的,他们三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他们都是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的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吴: 目前中国的油画状况是否很正常?
毛: 肯定是正常的。即使它再糟糕,它也是正常的。我现在对纯粹的油画界怎么样,根本就不关心。谈到油画界,可能更多地要谈到学院派或者什么很无聊的话题,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
吴: 在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你觉得油画的价值与市场最终呈现出来的价值是否很一致?
毛: 画卖得好的、卖得价格高的、机会多的人,当然会认为这是一致的。卖得不好的、机会少的,当然会认为这不一致了。谈到钱的问题,我喜欢杜尚的一句话,他说在钱的方面主要是看你能花多少钱,而不是看你能挣多少钱。你能花多少钱这很重要。严格来讲,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在社会中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也就是其价值也好、价格也好,是极其微小的。从社会的角度讲它就是商品,产品,其价值或价格,是不可能让艺术家过上真正豪华的生活。一个画家可能很潇洒、很洒脱、很挥霍、很奢侈,但是他绝对不是因为他富有了才挥霍,挥霍仅仅是他的一种需要。当然艺术家也不能太贫穷,贫穷会使画家变得疯狂、狭隘。
吴: 你是否了解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大体情况?
毛: 卖得好的都是老的或差的,像陈逸飞这样的。一个差东西永远卖得很好,一个老的东西,像古董一样的东西,永远有市场。相对来说,年轻艺术家能获得的支持和经济上的认可,就微乎其微了。
吴: 你经常去国外办画展,能否请你谈谈国外美术界的状况,以及国外的艺术品市场主要靠什么来左右?
毛: 那肯定与那个国家的整个文化需求和文化制度是相关的。实际上在国外,艺术品的商业化色彩远远高于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范畴。它其实非常商业,即使大师的东西也是商品。在美国、欧洲,那种商业色彩、商业运作的高度发达远远强于我们这里。但是由于它良好和非常健全的商业机制的运转,反而能够把那种文化的东西带动起来,移植到社会体制之中、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比如画廊、文化中心、博物馆、还有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和展览活动,甚至非常普遍的中产阶级的家庭,都有非常强的收藏能力,所有文化的东西都是商品。在国外,你甚至可以在大公司的大楼的大堂里看到大师的原作。也就是因为商业,反而让美国社会的文化色彩非常强烈。而某种好的艺术品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几乎是被当成垃圾,而在美国、欧洲,优秀的艺术品代表着精英文化,它们肯定会被留在很好的位置上,决不会被放在垃圾堆的一旁。
吴: 中国的文学界与国外的文学界交流时总是处在一种卑下的位置上,那么在美术界,这种情况是怎样的呢?
毛: 这肯定是差不多的。现在我们的文化对整个世界、对人类的文化的发展是不是有真正的推动,我们先不谈这个。只是说,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环境下所能产生的东西,它的作用与它的能量一定是极其有限度的。那么这个能量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是否具有文化影响力,我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就像我们在自己家里无法开一个 PARTY ,就得到人家家里去开 PARTY ,到一个更大的更豪华的人家去开 PARTY ,在那个地方 PARTY 才开得有点意思,才好玩。毫无疑问,中国的当代艺术可能跟文学的某些方面一样,至少目前它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当然偶尔它也介入西文文化,有一个展示的机会,但这也是很有限的。
吴: 中国的艺术家在面对世界时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毛: 可能我们现在实际上的心理,恰恰与应该具有的心理相反,恰恰是很不融洽,是对立面的关系。因为按照我们传统文化,中国人是具有超脱的、淡泊的心态,他的要求也是很有限的。现在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我们文化所处的边缘的状态,其实也恰恰是因为我们这些人的那种普遍的心态而导致的,这种心态导致了我们在某些方面处于卑劣的地位。中国人现在整个的框架是非常不牢固的,它是一个没有文化建树的东西,再加上中国人的传统的很超脱的、很通灵的东西已经在当代的中国文化当中体现的层面越来越小,体现的力量越来越微弱,那导致了中国人心态的普遍的微弱感。这是很可怕的。表面上来说,中国艺术的机会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一些极其小的机会也会让中国的艺术为之兴奋一阵子,极小的机会也像一个强心针,也像一个兴奋剂。实际上对西方文化中心的认同,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介入的渴望,其实这种心态已经病入膏肓了。其实所有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但是这恰恰不是我们刚才说的应该具有的心态,大家都很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被选择、被挑剔、被强奸、被利用、被猎奇的位置上面。
吴: 在国外从事艺术的华人与国内的艺术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毛: 我记得我去年在美国办画展,是几位大陆去的艺术家和几位在美国生活的华裔艺术家的联展。当时有记者与我谈到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问题,也谈到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国外生活的很多华人艺术家和我们生活在国内的艺术家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在作品中体现出的调调完全不同。我就说过其实他们与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也有他们非常明显的一致性的东西。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的那个环境下,应该说他们进入到西方语境当中的愿望更强烈,但又由于他们的那种心态,导致他们的作品我认为是极不成功的,当然有个别的非常棒。文化的问题,还不简单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它不断地告诉你要以你特定的东西介入它的那个文化体系里去,这在国内的艺术家看来好像很荒唐。说起来,我们这么多年来积累起来的经验、审美和所有的认识,都要介入到另外一种体系中,还希望能够立足,这就好像杂种一样的东西,是终就会搞出很多文化杂种出来,很奇怪的杂种,你没见过的杂种。当然渐渐地大家彼此也在接受,这可能也是未来文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彼此都在相互接受。其实他们起的作用也相当大,不管怎么讲,他们在国外以他们的身份、以他们的能量,在各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我看来我是无法想象,无法设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吴: 你本人目前参加了哪些比较重要的画展?
毛: 对我个人来讲,我参加的展览对我都挺重要的,至于其他人我不清楚,我的确参加了很多展览,而且还会参加很多展览,但是重不重要我就不知道了。
吴: 国外的艺术节与国内的艺术节有什么区别?
毛: 如果你是指西方的大型的展览,艺术双年展之类,那么区别就大了。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国际艺术节,每个城市都在搞,办得就像赶庙会似的,都是在翻跟斗、舞狮子、说相声、歌舞,纯粹学术的艺术性的展览几乎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一出闹哄哄的肥皂剧。因为中国的国情确定了这种艺术节是建立在中国的波普思想上面,中国的波普思想就是平民文化,让平民的身心感到愉快。而国外的如威尼斯双年展所体现出的精英文化,那肯定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种所谓精英文化的国际节。
吴: 你目前的艺术所到达的程度,以及在艺术之河中所处的位置,你有没有明确的认识?
毛: 如果这是建立在我个人的画史上,我对自己的艺术当然是有认识的。但是如果放在我个人的画史之外,出了家门,在大街上面,我就不知道了。尤其是放到历史的长河中,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吴: 你对与你不同风格的作品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毛: 这个方面经常是矛盾的。有时候我特别容易接受很多东西,这与我的爱好有关系。我的爱好和兴趣比较广,而且我从小从事绘画导致我对绘画有一种迷恋,从这一点来讲,我对很多不同风格、不同意识的呈现都有某种兴趣。但从相反的方面来讲,越是这样我就越对这一点有些疑惑,到现在为止我骨子里面真正迷恋的东西,我发现越来越少。我越来越不可能获得一种满足,这导致我对绘画的理解越来越简单纯粹,导致我的迷恋越来越没有根据,这是矛盾的一种东西。最后这变成很不规律的心理反应,一下子清楚一下子又不清楚,一下子喜欢一下子又觉得很讨厌。
吴: 你喜欢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毛: 每个人其实都有演戏的愿望,我也不例外。我在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我喜欢丰富多变的生活。
(根据1999年8月31日下午3点30分至6点30分的采访录音整理)■〔寄自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