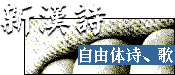老吴看着老张头的孙子,小强,走过来,
在水泥桌前停下,欲言又止,伸手
把老张头的老将轻轻拿起,反扣回中宫,
老吴便晓得,等了大半晌的这盘棋
已无对手,十几年来这风雨不改的棋盘上的老交情,
也到此为止,已不可多得。
老吴一边听着小强低声诉说他爷爷昨晚的事儿,
一边看着地上一些早落的树叶,被秋风倏倏刮走。
刚才,当小强把手伸向棋盘,老吴心里还想,
这小子,该不是也想学他爷爷,要跟我大杀两盘?
但他衣袖上的一小绺黑纱,让老吴看到晴朗日子里
突然出现的黑洞,被卷进去的人,再不会浮现。
小强到来之前,老吴的心情像天气一样晴朗。
他想,有什么事情能比在秋清气爽的公园里
稳稳坐下来,静静等待一位老朋友慢慢露脸
来得更惬意,更自在,更圆满?
他还想,要是碰上刮风下雨什么的,
他们会转移到湖对面的亭子里去楚汉大战,逐鹿中原,
今天天气这么好,老张头肯定是
让家里什么杂事儿给绊住了一会儿,
呆一两支烟的工夫就会出现。
老吴于是点上一支烟,眯起眼,对着棋盘
盘算起老张头惯常的中宫炮开局,以及自己
上马,拱卒,出车等一步步应对的手段。
小强走了之后,留下老吴一个人独自面对
水泥桌上这盘棋。老吴替反扣着老将的老张头
来了个中宫炮开局,跟自己厮杀了几个回合。
然后,老吴停下来,轻轻点上一支烟。
透过阵阵烟雾,老吴继续审视这盘棋,
这盘人人面前都摆着却永远下不嬴的棋。
在老吴周围,秋天的太阳明亮、温暖,
把满地的落叶照得明晃晃地发嫩。
这些光,有的也照到老吴的心里,
照见老吴日后得另想法子来打发的空白时间。
老吴轻轻吸着手上这支烟。
老吴眼看着自己手上这支烟也要燃到尽头。
(1999年9月4-13日)■
二 流 诗 人
其实,二流诗人是一些不错的诗人。问题是,他们不大承认自己。
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我们的问题。
是的,二流诗人是一个不能确认自己的群体。
一部分二流诗人自命为一流,
而大部分始终以为自己不过是三流。
前者才华横溢;
后者,也才华横溢,但少了一点点心理优势。
二流诗人喜欢用一些大诗人的名字做题目来写诗,
喜欢用他们的词语,或者诗句,作为副题,或者题记。
这样一来,二流诗人和一流诗人就显得有点关系,
有点亲密,但显然也有点距离。
二流诗人基本上说不出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在“怎么说”的技法上大作文章,浑水摸鱼。
但问题是没有鱼!
所以,二流诗人应该被贬到鱼塘里去养鱼。
到时候,养鱼人家自然会大声告诉他们:
我们都在岸上好好活着,你们又何必老泡在水里?
二流诗人努力学习。他们学习外国诗人,
主要进口他们的形式,例如头韵和十四行诗。
所以,朋友来访时,二流诗人会拿起
一个精美的空酒瓶子斟酒给客人吃。
当人家问,酒呢?
他说,难道我的酒瓶子还不够精美吗?
所以,二流诗人也应该发配到酒厂去研究一下酿酒问题。
二流诗人的想像丰富。但不奇特。
二流诗人的比喻众多。但不新颖。
二流诗人经常写诗,但多数并不必要。
二流诗人写诗,一般有拉长来写的意思。
当然,二流诗人也偶有短作。
但短作也依然太长。因为本来可以写得更短。
也有人写得很短,比秦朝的古文还短,还艰难。
其实,短,是要平易近人和更加简单。
二流诗人让自己的声音在事物的表面爬来爬去。
他们无法进入事物的内部,
更加无法抵达诗歌内部的忧伤。
二流诗人基本上停留在自恋、恋物和恋人这些热情上面
反复打滚。你看,他们把恋歌唱得多么动情,
但既不动人,也不动听。
二流诗人的思想飞扬,情绪激昂。
他们经常在自己的梦幻中看见事物的本质。
其实,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平静下来,
打开心灵的门窗,让心灵的火球闪光。
也有人这样做了,但发现自己的心灵不够明亮,
就四出寻找标价更高的电灯泡。
二流诗人把诗写出较大的情绪和声响。
他们的诗足以媲美流行歌曲,但始终缺少一点旋律。
二流诗人惯于站在听众面前张著嘴巴高声朗诵,
但却不知道该怎样轻轻走进人们的心中轻轻歌唱。
二流诗人的语言大多比较漂亮。
他们下过苦工夫钻研语言,主要是钻研口语。
口语好玩一点。
玩书面语的人,被他们认为是三流的行当。
二流诗人信奉“诗到语言为止”。
当时,这确实是一条不错的宗旨。
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诗到语言而不止”的工作,
到底还要留待给谁?
二流诗人在自己的想像中积极锻炼身体。
他们主要锻炼腿部以下的筋肌。
他们准备随时一脚就跳到一流诗人上面去,
好像一条跃过龙门的鲤鱼。
然而,跳过龙门的鱼,其实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二流诗人
应该适当放弃一些多余的动作和心思,
就像放弃一些多余的情感和修辞。
我们二流诗人应该坚定不移,继续用
心血和时间,喂养信念和一些简单事物的真谛:
通过持久恒常的写作和一点点皈依,
我们的臂膀,即便长不出丰满的羽毛,
我们留下的诗行,这些青青的藤蔓,
也会缓缓向人们的心间伸延,然后纠缠。
(1999年8、12月)■
今天,我的皮鞋闪着光
这场关于竞争研究经费的研讨会,实在闷。如果不是皮鞋闪着光,
这些讲者的经验,简直一无所长。
昨天晚上,十一周年结婚纪念日,
看完电影回来,她又给她的新鞋上油,
把我的旧鞋也拿来刷了刷亮。
当时,我好像端着啤酒,在看网球,
她坐在电视机旁边的地板上,
低着头,专心致志,给她的鞋子上口红,化妆。
看电影之前,我们走在大街上,
她抬起脚问了我两次她的新鞋怎么样。
去年,她多次坚持我在学生面前要穿西装。
今天,在这灯光昏暗的课堂,我看见我的皮鞋在闪光。
我觉得,她的新鞋不错,她的人也很好。
当我这么想,她在我的鞋面上,又微微发亮。
(1999年9月15日)■
旅游船上,挪威
验票之后,游客们纷纷上船。他们纷纷上到船顶。
他们搬开叠放的胶椅子,找个有利位置坐下。
听说,待一会儿,船的两边
会有一边,能够看见海狮和他们可爱的孩子。
当时的情形有一点乱。
不过,我们都是外国人,也就是
有教养的人,礼貌和距离基本保持一致。
起码,没有人拿椅子碰掉任何人的鼻子。
当然,几把椅子在一些人的头顶上搬来递去,势在难免。
当时的形势,确实有一点点乱。
人们找到船顶两边的有利位置陆续坐好之后,
局面慢慢得到控制。
找不到上好位置的人,退而求其次,
坐在船头和船尾,也相安无事。
船下一泓清冽绿水,
船边两面青山陡立,悬崖峭壁千尺,
山顶绕几朵白云,山头堆几摊积雪,
风景多么优美!
山腰上还挂着一些大大小小的瀑布,
大的飞流直下,一泻千里,
小的牵丝挂线,滴滴淅淅。
它们的差异,好比人的内心、外貌和脾气。
游客们坐好之后,船长开船。
船顶上,人们的头发首先被风吹起。
接着,他们的面颊和脖子也遭到了风寒的侵袭。
于是,有人系紧外衣的扣子。
有人从包里掏出大衣,披在胸前挡风,
反起衣领盖住嘴巴、鼻孔和脖子--那可是寒风们爱钻的空隙。
有人披上头巾,但一面头巾被大风戏弄成几面乱飘飘的三角旗。
后来,有一顶帽子吹落到甲板上,翻了两翻,然后翻落到水里。
人们首先听到那位丢了帽子的东方女士的一声惊喊,
然后看见她水里的帽子。
惊喊的时候,她的嘴巴是圆形的,象一个小写的o字。
惊喊之后,她一手掩着失态的嘴,一手掩着丢了帽子的头,
还有一只手则连忙按下被阵风卷起的裙子。
她惶惑地瞧着七八米外的水面,望洋兴叹了一秒,也许半秒,
然后大梦初醒扑向栏杆,摊开所有的手指--
这时候,谁都看得出,她是多么希望她的双手能够伸得再长一点!
不过,除了她身边的几个伙伴,
她对栏杆的普遍拍打,似乎并没有引起游客们太多的同情。
四周俏丽的风景,也没有得到他们太多的欣赏。
他们在风中的坚持,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时间越长,这样的坚持就越显得困难。
于是,渐渐有人往下层的船舱里转移。
然后,更多的人往船舱里转移。
首先是年老体弱的人,然后是带小孩的人,
然后是不太留恋风景的人,然后是耐不住风寒的人。
船顶的人渐去渐少,样子显得孤立、有点无以为继。
当然,也有人在风中继续坚持。
他们象山头溶剩的白雪,那么珍贵、不可多得,
但了了无几。
但也足以代表我们人类的某些品德。
下到船舱之后,人们发现
船舱里的风景和船顶上的一样好。
起码,相差无几。
虽然照相,相对来说,的确有一点儿问题。
但船舱里空气,比较友好。
何况,还有香喷喷的咖啡和暖气
在一丝一丝升起。
后来,人们还发现,
当他们从船顶纷纷走回到船舱里,
外面的太阳也一样照到下面的船舱里。
噢,外面的太阳也一样照到下面的船舱里!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多优美的哲理,
谁也不用再丢帽子。
这时,一位香港来的中国诗人,
已经坐在船舱里面记下了一首旅游诗的稿子,
用他古怪的东方文字。
(99年6月11日)■〔寄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