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 方·
回答几个问题
〔编者注:今年一月间,沈方先生通过网 络接受了本刊的采访。提问者为祥子〕问: 首先谢谢你把诗 稿投给《橄榄树》。《橄榄树》一直得到 许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从你在《橄榄树 》发表的一些诗聊起如何?
答: 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运动,可 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产生了不少杰 出的诗人,从 北 岛、多多到 韩 东、于坚、西川等人都写出了著名的 诗歌。至于诗歌运动的意义,目前还众说 纷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八十 年代,诗人们比较全面地进行了探索。因 此,才有了九十年代更接近于诗歌本身的 汉语诗歌的写作。
我也是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我是一 个笨拙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起点不高的人 。我既回避“旗号”、“主义,又远离高 深的诗歌理论。参加过诗歌小组之类,始 终是“哈雷慧星”式的漫游者。我早期的 诗歌(正确地说是一些幼稚的习作),至 今看来令人惭愧。这是“悔其少作”的通 病。当然这也是一种积累。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一些客观原 因,我似乎离开了诗歌。但是,诗歌是这 样一种东西,一旦传染就无法根除。如同 一个人的脸,终其一生不能改变。而现实 不可能是完美的,就象罗伯特·勃莱在听 众不欢迎他的朗诵时,情急之中喊叫的: “你们一走出去,现实就不会是你们所想 象的那样!”。于是我又开始写诗,而且 出于简单的想法,我写得比较平静。
诗歌成了我抵挡现实、保存自我的巢 穴。也可以说,我是在模仿叶芝建筑一座 塔楼,让精神有一个生存的居所。既放弃 了登高呼号,又消除了试图“藏之名山” 的奢望。所谓“时代号角”也好,边缘性 的“个人写作”也好。我以为我是有距离 的。我倾向于认为,诗歌是对生存状态的 的关怀。这些年来,我写下的诗歌,大多 是自言自语式和虚拟交谈式的。而且,我 不大投稿,偶尔试试也往往令人失望。不 客气地说,我的诗歌无非是孤独状态下的 自我慰藉。我以为,我应该坦率。我发表 在《橄榄树》上的诗,基本是这样。
另外我也应该承认,以《橄榄树》为 代表的网络杂志,现在成了我的兴奋点。 在耗费时日的漫游中,就象发现了岛屿, 我找到了新的交流。投稿需要勇气,而发 送一个电子邮件有一种神秘的快乐。相对 来说,比较亲切。
问: 什么是边缘性的 “个人写作”?能具体谈谈这种写作态度 和你的创作的距离吗?
答: 这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可以 说是一个方向,也可以说是一种态度。在 一个商业社会,归根到底,人是经济的动 物。文学艺术,更具体地说诗歌,不可能 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始终处在社会的边 缘。“时代号角”式的救国救民的政治性 写作,在现实面前无疑是苍白软弱的。
处在边缘的文学艺术,在强调精英品 格和独特审美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另一 个方面。“个人写作”是一种倾向,诗歌 在其中很容易成为个人角度的智力游戏和 学院式的高超技巧。当然,一个写作的诗 人,在他全部的写作中,很难避免滑入这 种倾向。抽掉了情感的诗歌,或者说在消 解了日常生活的诗情之后,剩下的就是文 字了。感动消失了,有的是理解、分析。 出于对诗人们的尊重,我不想指出具体的 诗人。比如下面这首诗:“土拨鼠在挖土 /有人问/土里有什么/土拨鼠说:土里 有土”,连分析都很难展开,“此中有深 意”?有没有,只能猜测了。也许可以说 这是最简单的诗,就是说“土里有土”, 而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这个观点可能有失偏颇,在诗歌史上 ,不排除有些诗人构筑的诗歌世界,主要 是哲学的、理性的。但是,这些诗人是区 别于“个人写作”的。我认为“个人写作 ”是危险的。如果进一步说,完全个人性 的感情私语,也不会有普遍意义。我说的 距离是,我愿意接受世俗化的倾向,主张 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日常诗情。不过,我有 时侯不免会怀疑自己,这样把握是出于藏 拙的目的?我想和祥子先生探讨一下这个 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诗情”与通常 意义上的诗意,是有区别的,其重心是在 “情”上。完全脱离现实是不可能的,诗 人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矛盾体。这不 仅是一个审美的倾向问题,而且也是一个 有关诗歌本身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摇滚歌词这一类现代民谣,确实是一个重 要的现代诗歌文本。
问: 让我还是保持一 个采访者的角色比较好,否则这篇东西就 太大了。:)我只是想很快地表明两个个 人的观点:(一)文学阅读必然是一种猜 测的过程。是文本和个别读者的经验相交 流的结果。一句话脱离了日常的使用环境 ,它的含义就不可能确定。(二)而这可 变的含义,和这句话的形式有关,和读者 的期待,经验/知识有关,却和作者的创 作态度、意旨没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有 意研究作者的本意。作者本意和作品的含 义不是同一概念。
新作者在自信确定之前总是怕被划入 一个群体,因此在言语中常常强调写作中 个人的成份。但每一位作者都受益(或受 害)于其他人的写作,尤其是同时代的人 。写作总是对已有文本的一种反应/反驳 。我想,作者的创作心态之所以成为这么 大的话题可能更多地和写作者的社会地位 在最近几十年的激变有关。
让我们回到你在《橄榄树》上发表的 诗这个更有意义的话题上来吧。你在《橄 榄树》九八年年终的长诗增刊上发表的 《天堂的舞蹈》有许多你过去在《橄 榄树》上发的短诗的句子,和我们现在发 的你的一组诗在音韵和情感色彩上都有明 显的不同。你是否也有自觉?能不能说说 这些诗的创作过程?
答: 祥子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一个写 作者,不可能离开阅读,他也就无法逃避 其他人写作的影响。甚至在有的时侯,还 很难排除模仿的痕迹。我要再说的是,保 持写作个性,不等于边缘性的“个人写作 ”,重要的是要寻找共性,或者也可说是 感情的共鸣。文学与猜谜式的文字,有根 本的区别。在智性的乐趣之外,还应该有 点别的东西。
还是来回答祥子先生的问题吧。要解 释清楚自己的诗是困难的,而且在事实上 是不可能的。更会有这样的情况,写作前 或者写作起始的意图,往往与最终的结果 相悖。可以说会产生一种反叛。好在问题 不是这样提出。先说说我的写诗习惯,通 常的情况下,我写在一个笔记本上。我至 今无法在电脑上直接写作诗歌。写诗的时 侯,多数是零星的业余时间。也有可能是 在上班用的工作笔记后面,一页一页往前 写。因此,我的诗大部份是短诗。
我几乎不写长诗,《天堂的舞蹈》是 个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例外。那是在19 96年下半年,我连续在一个笔记本上写 了《天堂的舞蹈》的雏形,是一些没有题 目,只有数字编号的篇章。整个篇幅比现 在的状态要长得多。而且那时也没有《天 堂的舞蹈》这个题目。
现在来看,这属于一个人被抛入商业 时代后的迷惘。后来就放在那里没有去动 ,一直到1997年底、1998年初这 段时期,才突然想到了题目,好象是找到 了一条线,删去大约三分之一,整理成现 在这个样子。
在这期间,我从中提出某些章节,写 成几首独立的短诗。这些短诗脱离了原来 的氛围,变成了另外一种存在。这是有些 句子相同相近的原因,这也可说是写作变 化的乐趣。至于现在这组诗,写作时间要 晚一些,我也感到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我 自觉,这组诗比《天堂的舞蹈》要清醒一 些。这既可说是,从一个时期进入了另一 个时期,也可说我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人 。当然,不变是相对的,甚至可能会有自 相矛盾。
问: 我很喜欢现在的 这批(包括登在 去 年十二月期的那首)的节奏。很干净 ,显得对要说的东西和叙说方式很有信心 。不过就是这样有内容指向、语言也直指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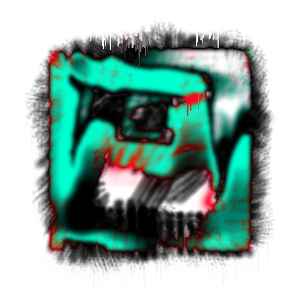 心
有打击力量的诗,目前的读者也不是很多
。我们估计了一下在《橄榄树》的读者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是读诗的,我想这在目前
较大型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中也许已是算比
例较大的。因之而生的问题之一,从写作
的角度去看,就是尚在写诗的人较少有机
会受到其他作者新创作的刺激。你能在这
一年把过去的诗进行整理,并能写出一些
不同的诗,是偶然而然还是有些其他外在
的契机?
心
有打击力量的诗,目前的读者也不是很多
。我们估计了一下在《橄榄树》的读者中
大约有三分之一是读诗的,我想这在目前
较大型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中也许已是算比
例较大的。因之而生的问题之一,从写作
的角度去看,就是尚在写诗的人较少有机
会受到其他作者新创作的刺激。你能在这
一年把过去的诗进行整理,并能写出一些
不同的诗,是偶然而然还是有些其他外在
的契机?答: 先来说一点题外的话。最近获悉, 安徽的《诗歌报月刊》面临停刊。去年1 1月,在江苏张家港参加诗会的76位诗 人联名致信安徽省有关部门,希望能让《 诗歌报》生存下去,但看来还是前途渺茫 。年末年初,国内纯文学刊物的生存,成 了一个热门话题。文学期刊的停刊、消失 似乎成了一个趋势。上海《文学报》一篇 文章提到,旅居德国的作家龙应台说,“ 目前内地文学期刊的‘没落’也许是一个 新阶段的启始。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 该会有各种风貌的文学刊物,雅的俗的, 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有 “雅俗共赏”的刊物。”
现在这个时期,可以视为文学的整合 期,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在某种程度 上,是写作者或者说国内的文坛造成了现 在这个局面。一般来说,诗歌的读者就是 一个诗作者,或者是一个潜在的诗作者。 纯粹意义上的读者向来不多,一首诗倘若 能抓住这一类读者,必定是杰出的诗。当 然汪国真的那些诗另当别论,但这个现象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仅仅看作是媚俗恐过 于简单。现在的情况是,旧的诗歌被读者 唾弃了,而新的诗歌却放弃了读者。遗憾 的是,我们有好多诗,不仅失去了纯粹意 义上的读者,同时也把作为诗作者的读者 弄得疲惫不堪。
如果来点“实话实说”,坦率地说, 我也不太读现在刊物上的诗。不是我不愿 意读,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不读“过世不到 二十年的作家的书”那种高度。我还是很 愿意借鉴同时代诗人的。使我经常放弃这 种努力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好多诗实在不 知所云,或者是读了以后让人无动于衷; 二是刊物上的诗太多,好诗和庸诗、烂诗 混在一起,鱼目混珠,实在没有闲功夫去 寻找好诗。过去有一句话:“写出一首好 诗是名诗人,写出十首好诗是大诗人”。 写一首好诗果然不容易,但要读到一首好 诗也并非是易事。我以为对诗歌的甄别和 评论日益成为重要的事情。同样遗憾的是 ,有不少评论总是热衷于炒作和推出自己 的理论体系,起不到对读者的导向作用。
在这种状态下,写诗的人要“挺住” ,只有依靠他自己的“内力”。不过说是 “内力”还过于机械,还属于技术层面。 只有把诗当作了生活方式的人,才有可能 “挺住”,并写出好诗来。诗歌首先是一 种生存形式,是一种脱离了现实、超越了 现实的生活。试图从一种理念出发,在现 实中寻找诗歌,必然是笨拙的,同时也是 伪善的。那样的诗,不过是偶然的机遇, 是零碎的片断而已。诗歌存在于诗歌世界 之中。庞德说过,大诗人的诗不可能每一 首都是好诗。庞德的话可以这样理解,一 个诗人生话在他的诗歌世界里,诗歌从那 里象植物一样生长出来,但是不可能每一 种植物都开出花朵。
当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诗,或者是 说是一些诗句的时侯,我不可避免也无可 奈何地把它们当作是个人的日记和交谈的 记录。在一般的情况下,写过之后要过了 一段时间,我才有可能重新翻动笔记本, 往往在这时侯就会有新的发现。这时侯也 就是诗歌最终成形的时刻,在此同时,新 的感觉、新的写作冲动也就产生了。需要 说明的是,在语言方面比较倾向于明白、 重量和力度,追求那种脱口而出的感觉。 当然,对于读者来说,这种想法可能依然 是一厢情愿的徒劳。白居易的《卖炭翁》 不可能是写给那位生活中的卖炭翁看的。 石壕村的老汉,也不会读杜甫的《石壕吏 》。白居易和杜甫同样,无非是写出了他 们内心的良知。彻底地说,太多的想法对 写作者是多余的。
问: 在我问最後一个 问题之前,让我先谢谢你这么认真耐心地 解释你的看法。这中间我的机子还爆了一 次,要你重寄答案。但再好性子的人也是 有限的。希望我们能在《橄榄树》上不断 地读到你的新的文字。
我个人对“挺住”的信心一向不足。 我总觉得“幸福感”、“享受”、“娱乐 ”等等更可靠一些。吴晨骏在这期的 【编者短语】中在谈到为什么大家坚 持做《橄榄树》这件没“好处”的事时提 到“理想主义”。我们有许多编制者的确 是这样的一些今天极难得的有理想的优秀 人物,我能和他们一起同事是一个福气。 但就我自己来说,一些做得比较长的事多 是些谋生必需或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是否 觉得在今天的环境压迫下,特别是生活的 压力,写作本身的乐趣已不足以支持作者 写下去了?如果是,你觉得像《橄榄树》 这样的民间刊物又能做一些什么支持作者 的事?
答: 现在很少有机会,能在我附近找一 个朋友比较纯粹地谈论诗歌。这样一次网 络访谈,其实是愉快的事情,同时也是我 有兴趣做的事情。
诗歌毕竟是形而上学,不可能有什么 实用性。尤其不可能带来金钱。在这个问 题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所谓“英雄 所见略同”吧。要“挺住”不能依靠刻意 的企图,还得出于一种本能才行。理想主 义的努力非常值得尊敬,而单纯的理想主 义恐怕靠不住,理想往往容易破灭。一个 人终其一生,鲜有实现理想,几乎没有。 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会以悲剧来收 场。世上的喜剧,要么是闹剧,要么是笑 中有泪。也许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客观上,写作者确实需要一个环境。 没有生存空间和必要的激励,写作者无法 存在。这个环境也必然有好或坏、充分或 不够之区别。我想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吴 晨骏他们在南京发起的作家问卷以及由此 引起的讨论,我以为在客观上起到了开拓 写作空间的作用。有人斥之为狷狂,这恰 恰说明了这些人的虚弱。国内的文坛,实 在是需要一些有力的刺激。
作为诗人这一个体,既不能脱离环境 ,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环境。对文学史我缺 乏研究,但是常识告诉我,曾经出现了大 作家和经典著作的历史时期,也不是文学 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唐诗所处的历史环境 ,诗在那时侯首先是做官的“敲门砖”。 “写作本身的乐趣”对写作者来说,比环 境更重要。写作的乐趣对有的人起作用, 对有的人就不一定起作用。具体地说,写 作者必须始终处于“有感而发”的状态, 才有可能一直写下去。
至于文学刊物,我首先要强调,从文 学角度看不应该有民间或官方之分。客观 现实是,许多官方刊物,尽管还有经济支 持,也无法避免式微趋势。刊物的存在和 作用,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也许读者比 作者更重要。作者还可以不考虑读者,刊 物如果不考虑那就只能是笑话了。刊物一 方面是作者的聚集中心,另一方面对作者 必然会产生影响。《橄榄树》这样的刊物 ,是一个新的文学载体,更有发展空间。 《橄榄树》能聚集一批作者,同时又拥有 一批读者。这就是对作者的支持。再说具 体,我就是外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