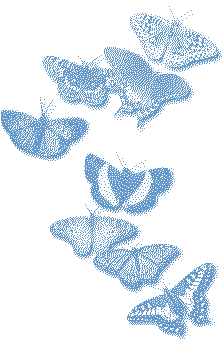
·阿 钟·
梦海幽光录
60我在一个拱楼下,这座拱楼象征着一 种界线,这个界线的另一边,是一个繁华 的世界。
我父亲出现,他对我的出行充满了希 望,并为此感到欣慰。他为我送行,眼睛 里满含着醇厚的情感,他那发自内心的期 待让我感觉出沉重的份量。
父亲走了……
一个野孩子,身上藏了许多贵重的东 西,还有许多现金。他是我晚辈中的一个 孩子,也许就是我的外甥,我说:
“你怎么可以乱拿家里的东西。”
我捉住他的手,把他衣服里的东西拿 出来,虽然他顺从了我,但一边又把我放 到架子上的东西重又揣回怀里。我非常气 怒,大声呵斥他……也许拱楼的另一边才 具有适合我那一套生存语汇的气氛……
一条我从小长大的街道上,是一个石 头筑成的建筑群,其中有两间屋,我和弟 弟各住一间…… 我在睡觉,起床刷牙… …我没有开门的钥匙……我在安排一次家 庭酒会,有一位女伴,但我没有进门的钥 匙……我在一个钥匙铺,与摊主进行有关 钥匙型号问题的讨论……
我要回家,路过一家印刷厂,这是我 上学时的必经之路。地上泥泞不堪,我走 得太艰难了,但我还是被地上的垃圾拌倒 了,我终于从地上爬起来,但还有一截艰 难的路没有走完!我继续往前走,但路被 堵住了。因为有人在地上挖了一个很大的 坑,坑洞上铺着木板,周围都用木桩圈围 了起来。正在做着这件事的是我的同学富 ,我曾在他的衬衫上发现过血迹。他看见 我,赶紧叫他边上的人为我腾出座,但我 没坐,站着和他说话。
他说,这个地洞在夏天可以使他的家 凉快一些。他每年都要在这个时候把洞口 上的一层浮土挖掉,下面的一层木板是可 以活动的。
绵绵细雨把每个人都淋得水淋淋的, 他说,这两天学校里出了一件事,许多人 都被管制起来了,好像是因为赌博。邓开 远也来看过了,但又回去了。她说:“怎 么会有这种风气呢?”但她回去不久也被 抓起来了。
据说,邓开远是邓小平的女儿。
61
外面下着雨。
一位远道而来的女人来敲我家的门。
我从楼上下来。
我家里还住着一位我曾邂逅一面的男 子,我们共同接待了她。
她是一位遥远王国的国王,她说明此 次的来意是为了物色一位她未来的总理。 我想,这倒不错,我倒可以去应选。但我 没有说出我的想法,结果她看中了这位男 子。
很快,这位男子离开了他的国王,回 到了我的家里。
他说:
“什么王国,那只是一个很穷的县, 她在那儿当县长。不过,这个县有自治权 ,有独立的外交权。我在那里只是帮她做 一些鱼的买卖,我是一个搬运工。”
我明白了,在她的王国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国王,一个是总理。而总理的工 作只是一个杂务工所干的事。
62
我弟弟去外地了。
几天后他从湖南的一个山区里寄回来 一包东西。
我在搁楼上睡觉,似乎听到家里在议 论这件事。母亲说:
“这上面写着是还给阿霞的。”
我明白她是指一张类似于支票的东西 ,弟弟往家里寄钱,是通过某个组织转这 笔钱的。其中所需的手续就是必须写明汇 这笔钱的原委,否则收款人就有可能收不 到。
妹妹说:
“这是给哥哥的一首歌。”
表弟说:
“这都是举办演唱会的材料吧。”
我明白这是弟弟为了给家里举办一次 家庭联欢会提供的一些歌唱或朗诵材料。
我被他们的议论所吸引,赶紧下楼来 ,翻阅这些放在桌上和已挂上墙头的资料 。有一首歌词,是给我的。措词华丽,浮 软,我想,或许他认为我是诗人,所以给 我这份东西。
在这堆材料中还有一份硬纸制成的材 料上写道:
“这里的九百五十元,交给我们家庭 的主管人阿霞。”
另外他还这样写道:
“一个老头把我带进这座深山的一个 寺庙里。走进庙里,我突然发现一杆长枪 对准我的胸膛,我迅速往地下一蹲,捡起 一把菜刀。这时,那个老头马上走过来, 向他们说明了我的来历,他们才退到后面 去了。我发现在这个庙里埋伏了许多人, 他们是一些准备战斗的起义者。老头将我 要带回家的这笔钱交给一位书记员,办了 手续,我在上面画了押。然后我便迅速离 开了这个庙,穿过一条小径,在黄宗英的 接应下,踏上一条小船,离开了这个绿水 青山的地方。”
……
63
一个老头有一批木料,交我保管,我 一个闪失,被人骗走了。
他们先去找那个骗子,这个骗子,我 们相互都认识。但这个交涉没有成功,所 以老头还是来问我要东西,我负担不起, 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我在一条阴暗的小弄里,然后来到马 路上,一辆车驶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乡 巴佬,后面跟着我的朋友亮,醉醺醺的。
我们便一起走进一所房子,门里是一 个旋转的楼梯,我往上攀爬,但楼梯变得 越来越窄。
我猛然发现,从另一条对称的楼梯上 去,可以更容易些。因为那条楼梯不但较 为宽阔,而且是垂直的,不象这条楼梯有 这么多的弯道。
于是我从已经爬完三分之二的这条旋 转楼梯上下来,再从另一条楼梯上去。在 楼梯的入口,亮拦住了我的去路,我便和 他议论起来。
我们的议论沉重而阴暗。我觉得一切 都是那么的滞涩,黑色为主基调的气氛使 我感到异常的不安……
64
我的朋友刚来访。
我们谈论起昨天发生的事情,这件事 好像与大街有关。也许发生过一次暴动?
他约我明天上午在横浜桥的茶室聚谈 。
第二天我去了。茶室里非常拥挤,不 知怎么的我到了一个车站上……
我在一个车站等车,我靠在墙边坐了 下来,于是便和边上的人聊了起来。我对 他大谈五代十国,谈到唐后主的时候,车 来了,他只好上车。但他上车之前好象犹 豫了一下。只见他在车上很焦燥不安的样 子,他对不得不和我分手觉得遗憾。只见 他迅速从衣襟上解下一块牌子,匆匆在上 面写了几个字,扔了下来。
车开走了。一个人从地上捡起牌子, 走到我身边,把牌子递给我。只见上面写 着他的姓名和地址,还有另外一些复杂的 文字。这时我才似乎有点明白了他的身份 ,他是一个具有众多人数的帮会组织头目 。那人示意我也给他留一个地址……
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我回到家,妈妈正在门口洗东西,她 问我:
“饿了吧,去拿一点吃的吧,你弟弟 那儿有很多。”
我走进家门,只见家里一点空余的空 间都没有,一张床占据了家里所有的地方 ,我父亲巨大的身躯则占据了整个床铺, 而我弟弟却躲在一个角落里玩耍……
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厅堂,厅堂的边 上有一张床,一个套着假辫子的前清人物 正在床上,他好像怀着巨大的恐惧等待命 运的判决。我明白,象这种人的结局很可 能就是在一顿棍棒之下被活活打死。果然 ,一个清朝校扑走了过来,举起粗壮的棍 子朝他头上打了下来。但他并没有被打死 ……他戴上假发,再压上一只瓜皮帽,整 整衣服,走了出去。
我明白,革命发生了。我终于明白, 我的朋友刚来谈的正是与此有关的事情。 革命,对,在街上爆发了革命。
一个人走过来,象一个老朋友似地和 我打招呼,于是我也就把他当成了老朋友 ,和他一起走了出去。
我们一路走着一路谈着,谈着谈着, 我和他,我们一起在前面的虚影中消失… …
65
我的朋友亮从外面来,从远离城市的 地方来,从山区来。他带给我两幅照片, 是两幅妆扮毛泽东的照片。一幅扮青年毛 泽东,一幅扮中老年毛泽东,两幅照片看 上去都很英武、漂亮。
我坐在门外路边的一张桌子上看照片 ,这地方有点象农村的一个小市镇。一个 年轻漂亮的陌生女人走来,挨着我坐下, 和我一起看照片。她和我挨得很紧,力很 大,结果我坐不住,从座椅上滑了出去, 我们一起摔了个底朝天,长椅子也滚在一 旁。听着旁边许多人的哄笑声,我没有觉 得很难堪。我们还是坐在一起看照片。然 而这个女人实在太重,我压不住我坐的这 一头,结果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我们又 摔了个底朝天,这弄得我很吃力。
我去接电话,这是一个柔声细语的女 人的声音。不知道我们谈了一些什么,这 个女人的声调是既严厉又动人,我对能和 她说话是既自豪又恼怒。我没有满足她的 要求,虽然我很想满足她的要求,最终我 还是坚持我的主张。这个女人在一阵疯狂 的暴怒下挂断了电话。我一下子好像失去 了什么似的,就象一个贫血症患者,一种 软弱无力的感觉向我袭来……
66
表弟在给日本的一个亲戚打电话。听 筒里传来一个声音问:
“喂,你是谁?哦,是你吗?”
表弟说:
“是我,小哥哥拾到25万日币。”
小哥哥指我的弟弟。
但对方的声音很严肃……
一张地图……
筑来,他说要到泥不湿去。我说,泥 不湿在哪?他说在新疆。于是我们看地图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泥不湿。他说,人家 问我们要债,所以我要去一次。
正说着,讨债的来了。没说完几句话 ,他们便打了起来。
我也加入到这一场混战之中,结果我 的拐杖被弄得不成样子,缩成短短的一截 。我要他们帮我去买一根,但天色已晚, 他们说买不到了,我真是沮丧极了。我在 妹妹的搀扶下,向家走去。路上,我仍在 希望有一家商店还开着,以解除我眼前的 尴尬。
我在一个昏暗的房子里,乱七八糟的 陈设。
我妹妹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油印的, 另一本装印很精美。这两本书是专门评论 我的诗歌的。我发现其中的评论恰当而中 肯。我以前怎么会没有发现这两本书呢? 据说那本印刷精良的书的作者曾来找过我 数次,都没碰上。他很崇拜我,读过我大 量的诗。他原是街道宣传部副部长,但他 宁肯写作,工作却不用心。不知谁说,那 还不如辞职好。
67
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举起听筒, 一个非常轻微的女音。
我问:
“你是谁?”
回答:
“我是金小苹。”
我想起有这么一个人来。
她说:
“我想到你这儿来,你有空吗?”
模糊中梦断。
……我到乡下去,和陈一起去。陈是 一位朋友的弟弟,我做经理的时候,到我 店里来帮我。
我们走出镇江车站……
一个屠夫,浑身一丝不挂,突然在我 们的身边出现。旁边就是一座大山,屠夫 斜靠在山坡上,他的身躯占据了整个山坡 ,粗糙油腻的皮肤辉映着阳光。皮肤粘附 着一些细碎的肉末,掌心的油脂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一会,他转身面向着我们,并 和陈交谈起来。
突然,他现身为一个女人,身穿老式 的蓝卡其外套,说话中露出上海口音。
我问:
“你是上海人吧?”
“是,我是插队来到这里的。”
她变得对我友好起来,我也产生了一 种遇到同乡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女人很面 熟,但我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她。
68
我去领工资,小舅彬和我弟弟陪我一 起去。
有一片广大的田野,浩瀚无边,有一 座很高很陡的桥,只有越过这座桥,才能 到达我的目的地。但这座桥实在是太陡了 ,在往上攀爬的时候,我几乎付出了我全 部的勇气和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