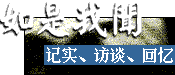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赵毅衡·
一度好斜阳
--追思吴方其实我无法谬托吴方的知己,想为吴 方写篇悼文,却总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 吴方的及身著作,我虽然读得不少,萍踪 异乡,手头只有寥寥几篇复印件,无法给 他的理论或文学成就作个总结。犹豫再三 ,想想不写也罢:吴方生前从未托我写什 么,至今也没有哪位编辑向我征稿。忽忽 然已经过去一年半,写悼文的理由越发不 存在:“时间早过了”。
每年都听到国内一二位学界或文坛大 人物去世的消息,而且不久后就会有单位 出面编纪念集之举,也常有被征稿的荣幸 。坐下想想,却只是在某某年月听过一次 课,或在某某会上听过一次演讲,我只是 芸芸听众中的一个,沾到一点智慧的恩泽 。就靠这些,也有资格列于凭吊者之中?
毛主席去世的大悲时刻,我正在一个 煤矿接受改造。某副书记的夫人,为她的 丈夫应当站在第几位,到党委狠吵了一场 。那天全矿工人连家属小孩共同努力,就 是没能哭出一个气氛。肃听天安门城楼上 的排列顺序时,我竟然为治丧委员大人们 的安危犯愁起来。恭送伟人,本很容易出 乱子的。
吴方绝对算不上任何等级的人物,也 无人会编记念集,也不存在治丧排第几位 的问题。我给吴方写这么一篇太晚的文字 ,怕也不会有人责我僭越吧。
听到吴方的死讯,正是一九九五年夏 天离京前一夜,记得是八月十六日。一个 朋友借送我和虹影的由头,找了一些同行 喝酒。文人聚会,气氛少不了欢快热烈, 说话少不了放言高论。忽然从机场来了二 位不速之客,严歌苓和她的丈夫
Larry Walker。Larry 曾在沈阳任美国领事多年,北方话说得油 极了,声调准到能装傻,把妻子的名字叫 出几种意思绝倒的声调变体,满堂为这个 洋鬼子喝彩哄笑。
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下午吴方悬梁 自尽。
我正在没命地大笑,突然刹车,一下 子呛住了,惊得双眼发直。
“唉,安乐死的机会也不给一个!” 旁边一位听见了,插上一句嘴,摇头叹息 。显然他们早知道了这个消息。
我想追问一点情况,每个人给我介绍 了几句,就被别人抢去了话头:作协党组 正在提拔“跨世纪人才”,有的新领导几 乎比在座人儿子的年龄还小,那个消息当 然更吸引注意。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客 是好客,天下多的是有趣谈资。天下每秒 种都有人死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死去 ,谁也不能保证,死后人们会为他悲哀多 长时间。葬礼还没有开始,夜还没有星移 斗转。吴方把绳圈套到脖子上的时候,如 果想到朋友,恐怕是希望我们为他终于得 到解脱击缶而歌吧。
我呛得气顺不过来,只好走到阳台上 去。
一九九五年夏,我虽然是有思想准备 而回。但整个中国忽然变成了一个特大市 场,无时无地不在喧闹嚣腾尘土飞扬,依 然给我猛烈的“文化震撼”。友人这个楼 不高,看不远,但是朝哪个方向看都是熙 熙攘攘有买有卖,赚钱的自由使举城若狂 。而在这烈火油烹的“美好日子”中,若 有些知识分子自愿杞人忧天,苦恼于责任 感,当然只是应了堂吉诃德的雅谑。不过 我那时突然落入的凄凉心境,与此无关, 只是为古老而浅薄的人世无常感慨。
我第一次听人郑重其事地说起吴方, 却是一位知识界的重要人物说话。文化部 文艺所办的《文艺研究》杂志,吴方在一 九八八年底成为第四个副主编,到一九八 九年秋天的大换班时,竟然还在。“这就 是希望所在!”那位朋友以他特有的热情 说道,“这就是证据:石缝里会长出树来 ”。
翻一下那几年的《文艺研究》,觉得 吴方的留任,恐怕不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特 别提拔吴方,也说不上是某个方面借此发 出什么信号。这个表情沉重严峻的“大刊 ”,八十年代的最后两年的确编得很不一 样,文章短小而精彩:李锐论现代派,汪 政晓华论间距,陈晓明论拆除深度,蒋原 伦提倡批评的攻击性。这些是不是吴方的 “新政”,我说不清,八十年代末,一些 最僵硬的人物都“咸与维新”,自称“容 忍”,不一定吴方才能组这些稿子。到八 九年第五期起,此刊就全套“主旋律”, 吴方的留任也一样不起作用。
但是那朋友眼睛中的希望之光,也使 我朦朦胧胧产生了希望。我就把一篇论文 《中国小说中的回旋分层》给了吴方。那 个气候中,讨论形式问题也是犯忌。虽然 吴方来信表示欣赏,刊出却是一年之后的 事。九一年第四期该刊的正副主编名字全 部消失,明摆着在清理了。下一期就不再 有吴方名字。吴方后来说我的那篇是他做 这个捞什子副主编签发的最后一篇文字。 一九九二年,他在杂志已经呆不下去,辞 了职,去文研所作清静的研究人员。又过 了一年,他离开文化部,到语言学院任教 。
我没有问他什么原因。如果吴方的留 任是个小小的错位,他的去职恐怕不是。 他并不是个激进的前锋,他只是一个诚实 的知识分子,但是中国常有诚实的知识分 子不能做副主编的时候。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回北京做一年的研 究,一时找不到地方,在东郊机场路的社 科院研究生院招待所住了三个星期。北京 太大,我熟悉的只有这个地方,下机场就 奔这“老家”来了。三个星期中,肯长途 跋涉来看我们的只有两个朋友:吴方与张 颐武。吴方是自行车来自行车去,怎么说 也不肯留下吃饭,顶着夏日中午的太阳骑 车回去了。与张颐武在饭桌上谈谈笑笑是 很快乐的事,一些北京开始流行的新的文 化现象在他嘴里化成无穷笑料,时针在欢 乐中跳动。与吴方简直是无言枯坐,碰巧 ,吴方读过我在一本地方杂志上写吴宓的 小文字,于是我们大谈一顿吴宓。后来我 读到吴方的书《世纪风铃》,才明白那不 是碰巧。吴方是读几十卷书写一篇文章的 人。他要写吴宓,就把所有关于吴宓的文 字都看了,哪怕我那种破文字。他没有加 以评论,顾我的面子。
一辈子不走运的吴宓,把我们首次见 面的窘迫给救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每 次想起吴方,就想起吴宓--耿直的北方 汉子,黧黑的面目不象知识分子,却是做 学问也象耕田一样执着,决不跟着时风转 ,错也错出个名堂。不巧的是,吴宓也是 自杀身死。
《世纪风铃》的文风,曾经得到我的 一位最挑剔的朋友无保留的的赞美,那位 朋友是周作人的隔代望门子弟,从来没有 说过我的文字一句好话,他在吴方貌似平 淡,实际上极为讲究的的文体中,看到睿 智的沉潜,和对人文精神的执着。
那年在京时间较长,又见过几次,在 会议上,在私人集会上。九二年秋天,好 多人凭政治嗅觉或凭内部消息,认为翻烧 饼时间到了,有几个会开得真是轰轰烈烈 ,听着有来头的话语惊四座,全场兴奋, 第二天就传遍全城文化圈。吴方大部分时 间都默不作声地坐在角落,脸无表情,不 记得他发过言,好象纯是职务所需才来的 。
倒不是他有先见之明,知道这一次, 烧饼只会挂起来两面不沾边,不会有翻煎 的好事。他只是天生不喜欢说话而已。有 一次在研究美术史的朋友尚钢家小聚,《 读书》的编辑吴斌温文尔雅,没有想到她 的丈夫冯统一,竟然是个连相声演员都自 愧弗如的幽默家。我们都听得笑神经不由 控制,吴方更是只有坐在一边莞而微笑的 份。
听说吴方病倒,已是很晚,一九九五 年初。一个来伦敦的朋友说的消息,说是 癌症发现时,已经扩散,肿瘤已经在压迫 脊柱神经,疼痛异常,化疗和理疗更加重 痛苦。夏天我们准备回国一次,临走时顾 晓阳来游历欧洲,带着健康得叫人惊奇的 老母亲。顾又是一位京味语言大师,谈笑 中生生活剥一系列如雷贯耳的名人。我说 到吴方,他高兴地叫起来:“老朋友,老 同学,人大文学社的老战友!我早就带口 信叫他务必坚持到我回去看他!”我说, “行,再给你带一次口信。”心里却挺诧 异,怎么木讷口拙的吴方,交的朋友一个 比一个谈笑风生。
回到国内,就打电话给吴方的邻居兼 好友尚刚,询问吴方什么时候回家--他 是慢性病人,周末是能够从医院回家的。 我们约好一个时间。尚刚建议我们别带鲜 花什么的。“吴方是个本色人,带点水果 还实在”。
过了几天,尚刚忽然来电话。他跟吴 方说了我们将去看望他的事,不料吴方一 听,竟是潸然泪下,要我们别去:不想让 我们看到他的一副惨相。我和虹影听了极 为惶惑:我们当然不愿意给他增加痛苦, 但是他生病已久,北京文学界的朋友去看 过他的不在少数,他们从未见到他情绪上 如此反应。或许是因为我们远隔重洋,在 他的心目中是特殊客人?
久居海外,偶尔回国作访客,到九十 年代中期,情况已经不一样。同行的“怠 慢点无所谓”,刊物的“何妨往后排排” ,出版社的“选题尚须报批”,文艺界半 官儿们的“小心一点不会错”等等。法国 人说“远于目者远于心”,中国人说“人 走茶凉”,本是人世常态。到一九九五年 ,我们碰到此类纯粹操作问题,早已经不 再生气。象吴方这样,还把来客之远,作 为情意殷切来想,而且竟然泪下,的确思 想旧得少见。
不过当时,吴方的异常反应,弄得我 们进退不得。思考再三,决定扛一个大西 瓜和一堆水果,匆匆看望一下,就尽早撤 退,免得大家挨窘。
吴方家至今住在东城一个狭窄的四合 院,各种附加建筑早把院子变成了迷宫。 吴方自己的房间,好象是防震棚时代的遗 迹。坚持保存古城风貌的人,对大杂院情 有独钟,不妨与吴方的孤寡换房。吴方的 文化部第一大刊副主编--国务院的副处 级干部--为官二年真是做得不怎么样。 而且如今,要干部退下,得升一级加一室 ,看来吴方的辞职也是白辞了。
有了精神准备,吴方的外貌巨变,没 有使我们过分吃惊--死神已经在他脸上 抹了重重蜡黄的粉彩,脸颊深陷,颈上皮 肤挂成条。他身子已经很单薄,虽然穿着 白色的单布衫裤,看得出只剩一把骨头, 歪斜地瘫坐在一张单沙发上。“房间”很 小,唯一的一张椅子我坐了,虹影只能坐 床上,尚刚只能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我 们请他陪来,以防应付不了的局面。吴方 的的妻子和孩子都出去购物了,不知是正 巧还是有意安排。
该是我们询问病情,并且安慰打气一 番,用我们对晚期癌症的藐视,来帮助他 战胜疾病。吴方却不等我们开口,立即谈 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上 我那篇“‘后学’与新保守主义”,徐贲 论所谓“第三世界理论”的文章,以及续 后各期上张颐武,郑敏,许记霖等人理直 气壮的反驳,还有我简短的回应。每一篇 文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着实吃了一 惊:我们在京近二个月,见到文学界理论 界不少朋友,无人谈起这场争论,哪怕一 些被我“点了名”的朋友,都绝口不谈此 事。起先我以为是他们给我面子,不便当 面指斥。后来才明白,《二十一世纪》不 容易读到,好多人听说而已,没去找原文 来读。朋友相聚,这题目也太无趣。
吴方滔滔不绝地谈起来。我们三人交 换了一下眼色:太好了,原因虽然不明, 预想的尴尬场面却没有出现。吴方的话音 ,比以前更轻,脸上不时有异样的表情, 陷在沙发里的身体时不时动一下,看来疼 得厉害。但我们都明白,减少他的痛苦的 最好办法是让他谈下去。
我知道,吴方是不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按我的标准来看,吴方就是属于我说的 “保守主义者”。这个词,应当是个夸奖 ,至少比“激进主义者”强多了--他自 己在好几篇文字中直认“保守”而不讳。
吴方在八十年代是先锋文学与新理论 方法的热情辩护者,他的一系列文章至今 仍被人引用。到八十年代末,他却避开当 今,转向文学史。一九九二年结集于《世 纪风铃》中的各篇文字,都是对吴宓,梅 光迪,周作人,陈寅恪等为学为人的击节 赞美;此后他的研究更向前推,转向晚清 人物,从章太炎,王国维,说到一生经营 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吴方个人而言, 是他自己选择的课题,就整个学术界的趋 向来看,我有十足的理由说他是新保守主 义思潮的一个“分子”。
但吴方却不是跟潮流走的人。他写的 那本《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的内容提 要:张元济从官场转向出版业,“此一选 择,未始不是明智的,脱俗的。这使他得 以避免历史的种种是非恩怨,既非庸碌无 为又非风云人物,既未陷身于历史的某种 虚幻之境,又不象“舞台”上的匆匆过客 。”
而吴方对“张元济式”文化人的钦佩 ,不着眼于其“历史贡献”,讲究的是他 们的人生境界:“这样一种‘存在’的意 义,似乎很令人回味。当然回过头去看, 也是人生不易到之处”。
我可以打赌,这内容提要是吴方自己 写的。文笔之从容优雅,国内同辈中很少 人有此手笔,尚在其次。明显这是吴方在 写自己,而不是在写一个收敛锋芒甘心做 实事的文化人。世纪末中国文化人的心路 历程,往往要到世纪初去找,二十世纪的 中轴对称,一至于此。
甚至,从当代文学研究转回世纪初, 在吴方来说,只是眼光投向的变化,他的 立场没有随世风而转动。一九八八年刊在 《北京文学》上那篇妙文《论矫情》,历 数了当时几篇把文坛震得大摇大晃的名作 ,“很象天赋甚高的少年人在人面前说话 ,虽然有锐气,但说话的调门往往过高” 。吴方的评文论世,待己待人,可以说是 一以贯之。
我的性格可以说与吴方正相反,但是 我欣赏任何一以贯之的人,在今日,这是 尤其难得的人品。
那天吴方批评我的观点,还是很小心 地选择字眼,不是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吴方做人一向为别人想得太多,我倒是 很希望他直接指责,那篇文字反正已经给 我添了不少论敌,何不让吴方痛快地臭骂 一顿。他的思路极为连贯,虹影和尚冈简 直无法插进任何话。我这当事人大都只是 点头称善,不是尊重一个面临死亡的朋友 ,而是我明白那种争论不是是非问题,而 是观察角度,或者说,批评立场。我本来 就转变不了任何人的角度,何不让吴方贯 彻始终。
吴方真的说高兴了,忽然开始臧否人 物,一个个地讥评当时批评界风头正健的 人物。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如此放言无忌。 每个能迫使同行注意的人物,我觉得必然 有特别的长处,“风头”本身,不应当受 指责。但是我同意吴方的一个观点:弄文 学艺术,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不能太聪 明,得有点儿傻气。这个世界各行各业都 需要聪明人物,要把文学做到“人生不易 到达”的境界,聪明却是很碍事的。
我至今纳闷,一个肿瘤已扩散到脊椎 ,压迫着神经中枢的临危病人,要靠不断 服用强剂止痛药才能勉强坐起一会儿,他 哪来的闲心关心这种文化界大部分人都不 愿意听一下想一下的问题?或许平时他在 病床上消遣的读物,竟是这种枯燥的文化 讨论?
不管怎么说,吴方的“反常”热情出 乎我们意料,但也让我们非常高兴。我的 文章或许“触到”了吴方的“痛处”,转 移了他的感觉兴奋灶。尚刚说,吴方病了 近两年,从来没有见到他那天谈兴之高, 实际上,以前几年我也没有见到过。可能 这次见面是我那篇惹祸的文字做到的唯一 好事。
“回光反照”,我突然想。一个依然 充满智慧的头脑,依然在活跃地思考,危 乎哉地顶在一个朽败的身体之上,还不得 不跟着身体一起烧成灰烬,世上有比这更 大的悲哀吗?
那天只有一次,吴方说起他的住院。 “我看到从郊区远远赶来的农民,随便给 人打一针止痛药,就让人家回老家等死, 根本不给治!不过真也没法:进口的治癌 药,一针五千!我刚到语言学院没几天, 学校对我算是大方的”。看来吴方老记住 别人好处的习惯没有变。“隔壁病床,就 因为单位付不起这针药,去了”。
或许这医疗巨款对吴方的折磨,比在 他内脏的乱钻的癌细胞更甚。他天生是个 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比别人更高待遇的人 。这样的人,现在真是凤毛麟角,大部分 人总是在抱怨招待等级不够。人心不古, 有权者做的榜样太糟。
我甚至怀疑,他明白这是个不治之症 ,不想再继续白花公家的钱,可能是他提 前结束自己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一定 是崇高的利他主义,我想这是中国读书人 的旧道德,不愿暴殄天物。
坐听吴方畅论,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 多小时,我们很不安,虹影几次丢眼色, 提醒我该走了。我们本想只坐几分钟,尚 刚早就警告我们不能超过二十分钟。但是 吴方不让我们走,他看来还真希望聊下去 ,谈这个所有健康的理论家们都认为太迂 腐的题目--中国文化。
临走,我们说过两个星期再去看他。
象大部分这种承诺一样,很难信守。 虽然我和虹影总在说,什么时候到医院去 一次,一直到这最后一夜,还是没有去。 心里倒是想起的,只好说离京后写封信给 他吧。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他自杀的消 息。
据说他临死前很平静,把家里人打发 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处理一些小事,接电 话的人都说声音极为平静,没有任何情绪 波动的征象。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最后 他打了个电话给正在给他编最近一些文章 的冯统一,说他决定了书名:《斜阳系缆 》。
标题极不祥。家里,医院里,都取消 了他任何死得舒服的可能,只有这个小小 的改良防震棚,还有屋梁可系一缆。
半醉的晚会还在喧闹,阳台上仿佛可 以看到东四十条立交桥,已经安静下来。 我听见背后传来自行车铃声。那种熟,不 用下车,捏一下车闸摆一下龙头就够了。 我知道那肯定是吴方,我倒想知道他匆匆 上哪里,这么晚了,离家而去的方向。于 是我转过头来。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