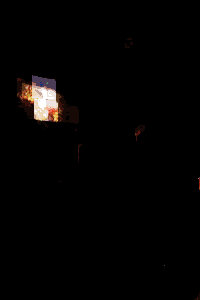
·金海曙·
鼾 声 如 雷
今天我被一阵鼾声操了一顿。这话说 得有点粗,但实际上我就是被它操了一顿 。鼾声一点道理不讲,一点不客气地挤进 门来,象一大早来了一个大块头的修自来 水管的工人,穿着工装裤。我在想,一开 始这个人接到通知说楼上的水管坏了,向 下渗水。正好他今天心里不痛快,今天是 周末,他不愿意一大早出门去修水管。于 是他就勉勉强强出了门。我继续想,忽然 他发现带来的配件也有问题,全是小号的 ,和下水道漏水的弯头尺寸不对。水漏得 实在太厉害了,真是样样事情不称心啊。 我几乎看到,他开始的时候还在水管上装 模作样地敲敲打打,结果一使劲就把我摁 在床上一声不吭操了起来。我这样一想, 就加深了我受迫害的感觉。我是一个受害 者,这没有问题,许多人都是受害者。我 虽然这样想,却并不能恢复我心情的平静 。老头的鼾声正象是一根愤怒的生殖器 ,直挺挺地竖在我的头脑里。我无话可说 。没有我发表意见的余地。这是没有办法 的事。我们每个人因时因地都会偶然地处 在被强奸的位置上。这种事情一点办法都 没有。本来我不会对没有办法的事情随便 发表意见。既然一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了 、不可挽救了,那么我们只有承认它的合 理性,只有承认它是没有办法的、不可挽 救的。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人生观,起码 我认为它是比较正常的。可是不久前发生 了一次不甚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自行车 在我的尾骨附近撞了一下子。我当时以为 没有什么事,不久后我发现这次偶然的小 事故让我整个人变得相当的神经质。也可 能我原来就比较神经质,神经质的因素潜 伏着,均匀地分布在我的神经网络里。自 行车轮胎撞在我的尾骨上,就像我们无意 中揿下了一个开关,神经质就开始在我的 体内乱串起来。我的神经系统现在很混乱 ,植物神经、动物神经还有神经末梢都很 混乱,处于系统崩溃的前夜。
系统崩溃是从植物神经开始的。先是 失眠,接着就是亢奋、不停地亢奋。很多 平常的事情,我不明白有什么可亢奋的, 但我就是抑制不住地亢奋起来。换一个说 法就是我变得非常敏感,极其敏感,神经 末梢很活跃。我不喜欢活跃。神经末梢一 活跃,就降低了我的忍耐力。本来我的忍 耐力还行,默默无声,辛勤工作,现在我 的忍耐力已经很稀薄了,有点象牛奶里面 掺了很多水,又有点象城市里的空气污染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使得今晚的鼾声 变得难以容忍。
隔壁的老头每天晚上八时四十五到九 时之间,必然地、准确地开始打鼾。我不 反对打鼾。但是有个人每天都在你隔壁准 时开始打鼾,这就对生活造成了影响。至 少这让人有点迷惑,到底有什么事让他每 天在这个时候打鼾?虽然我知道这是生理 原因导致的呼吸不畅,我可以从病理学、 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打 鼾,可我还是有点迷惑不解。特别是今天 晚上的鼾声实在是太过份了,它那样肆无 忌惮,那样随随便便、毫无章法,以致于 让我产生了一种错乱,除了一种被强暴的 感觉外,还有一种被劁掉的感觉。我这样 说,就显得我更加错乱了。但感觉不是思 想,我允许了它的错乱。一般来说,思想 的错乱才是真正的错乱,而感觉的错乱则 是暂时的、有限度的、在思想的干预下是 可调控的。再说,反正现在事情已经糟透 啦,反正我已经忍无可忍准备反击啦。我 想得很清楚,可以说已经想透了。
我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 老头的鼾声很有特点。它一开始是逐渐地 、有节奏地展开的,由低向高,然后由高 向低。不急不缓,带有很大的欺骗性,让 你觉得他控制得很好。让你觉得洪水是一 点一点涨起来的,又让你错误地觉得洪水 一点都没有往上涨。这个欺骗性的过程大 概会持续十五到二十分钟。接着会有一个 猛然的停顿。这是一个真正突如其来的停 顿,一个空白,仿佛一本情节紧张的小说 里夹进了几张没有字的纸,这几张纸是在 告诉你情节已经紧张到了无可描述的地步 。随之就是一阵强烈的咯咯咯咯的摇门板 的声音,把情节往高潮推动。我猜测是有 痰在他的喉咙里卡住了。老头开始挣扎, 气氛极度紧张。我是说我极度紧张,并有 一种不祥的预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 口,等这个关口跨过去了,老头的鼾声就 一如洪水出闸,汹涌澎湃。
现在是晚上九时半。老头的挣扎很快 就会过去。如潮的鼾声就要来了。我今天 不准备被迫地、静悄悄地等待这阵无理的 鼾声。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把我劁掉的。 我可以被劁掉,我只是说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来劁一下子。一个老头的鼾声就把我 劁掉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我坚定地打开 门,而恰好这时鼾声的高潮来临了,一个 响亮的鼻音哄然而起。我确实象被人劁了 一记,真正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可抗拒和悲 剧性。鼾声漫过我的身体,塞满了我的房 间。它象一个胜利的宣告,看吧,我来了 。我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永远正确的 ,你狗日的就站在那里被劁掉算了吧。鼾 声发出了一阵欢快的大笑,纵情的大笑, 笑得十分舒服。我在门口站了将近一分钟 ,啼笑皆非。鼾声是不讲道理的、非理性 的、疯狂的,那种身处其中的无能为力十 分巨大,我仿佛经历着一场无能为力的风 暴,它一下子就把我象一张小纸条那样吹 了起来。
我走到厅里。厅,一套体面住宅的门 面,就是这个鼾声的发源地。我住在我们 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它是一套带着一个小 厅的小房间。我们单位在盖房子的时候, 把这套小房间设想成某对年青夫妇温暖的 小窝。现在,我被安排住在这里,住在一 对假想的年青夫妇的小窝里。这让单位感 到有点不合适。原来这套房间预定是两个 人住的,现在只住了一个人,这就不合适 了。而且单位有明确的规定,为了防止年 青人乱搞男女关系,每套屋子里必须住进 两个以上的单身男人。这个规定有点象一 个讽刺,同目前浮躁亢奋的生活环境不相 适应。目前这个规定显然是跟不上形势了 ,它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但我们单位的 主要业务是对全城下水道进行管理,业务 的性质决定了规定的性质是保守的、向下 兼容的、不太灵活的。我的具体问题是单 位里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单身男人了。于 是单位就安排了一个看门的老头住进来。 就住在厅里。老头很和气。刚住进来的时 候我没注意到老头的鼻子。现在我注意到 了,它是巨大的、丑陋的,却有着帕瓦罗 蒂胸腔的共鸣,表现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 内在力量。
我凝视着这个难看的鼻子,这个松松 垮垮的鼻子上记载了一个男人卑微的毫无 意义的生活经历。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疑惑 。就是这样一个丑陋的东西想要把我劁掉 吗?这样一个东西就简单地把我操了一顿 吗?在凝视中,我觉得自己变得有点虚脱 ,无论在体质上还是精神上我都有点虚脱 。我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下虚脱是很丢人的 。被一个难看的鼻子就搞得虚脱了?没有 发生什么实际的事情嘛,为什么就轻而易 举地虚脱起来?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了。 我希望自己好好地过日子,我希望建立一 个幸福的家庭,床上躺着一个匀称的和气 的太太,而不是一个什么看门的老头。
这些胡思乱想让我变得很轻,我很快 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股烟雾飘了起来,从 窗口冒出去。我越飞越高,飘到了一定的 高度后,烟雾团聚起来成了一只气球。不 由自主的力量把我托起来送走。我觉得自 己终于浮到了鼾声的上面,我可以在空中 凝视这个鼾声如雷的老头,凝视我屋子亮 着灯的窗口,凝视这个夜晚覆盖的城市。 它象一只巨大的永远不会开走的船,停泊 在黑暗里,却带着一副随时都要离我远去 的神气。我越过了无数根电线、众多的高 楼,它们有些亮着灯有些没亮。人们住在 各自的匣子里,关上了幸福的小门,关上 了小门外的铁栅栏。门上安装了各种各样 的保险设备,物理的电子的激光的数字的 ,幸福被关在里面万无一失。只有他们自 己才能把幸福打开。没有人会想到有只被 鼾声托起来的气球此刻正从他们的窗外经 过。我飘过一扇亮着灯的窗户时看到,一 个丈夫正把自己的脚浸在脚盆里烫脚,同 时阅读着一本《家庭与健康》。他的妻子 正在安排儿子睡觉。我要巧克力,儿子说 。不行,妻子严肃地说,睡觉前不能吃巧 克力,睡觉前吃了巧克力就会长不大了。 此刻丈夫则平静地把杂志翻过了一页。我 不知道他正在看什么栏目,他看得津津有 味。胆囊炎、艾滋病和保持家庭中爱情的 秘诀都让他津津有味。
这个场面在一个鼾声如雷的晚上十分 无聊又感人至深。我很想停下来看一看, 但是我控制不住风的方向。讲得抒情一点 ,那么就是我在一阵鼾声中无可奈何地飘 了起来。飘啊,飘啊,飘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