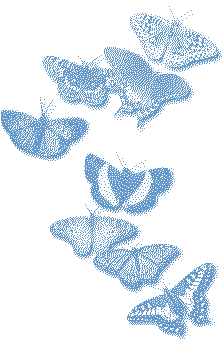
·阿 钟·
梦海幽光录
11我是在别人的安排下成为今天婚宴上 的主角的。来了许多人,绝大多数都是我 不认识的。
酒宴结束后,我被送入一个房间,我 才被告知是怎么回事,房间里的一个女人 是我的新娘。除了我的新娘以外,房间里 还有两位陌生女人。
房间的陈设非常简单,除了一张床, 以及一些随便放置的桌椅以外,没有任何 醒目的东西。但墙壁是做得考究的,墙面 是用一种蜡染的布料粘贴而成。我用手在 上面摩娑了一阵,细细地观察了一番。
既然婚娶已成事实,我也并不反感, 因为新娘也长得颇有姿色,眼睛很大,体 态丰腴,很浓的女性味。看着她,我感到 一阵冲动。
为什么我没有和她尽男女之欢?也许 是因为还有两个女人守在边上。我感到这 仍然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过我也确实没有 那种男女欢爱的欲望,所以很自然地把它 看做为是一次朋友间的聚会,只不过其中 有一位今天是我的新娘而已。
房间总是很暗,只有那新娘的面容可 以让我看清一些,其他两位却朦朦胧胧, 看不真切,但我也没有想把她们看清楚的 欲望。
我们走出房间,经过一个露天的过道 ,然后再经过几级台阶。月光低低地照着 我们,我和新娘隔着一段距离,走下台阶 。前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平台,周围砌着 栏沿,平台的中央有一眼水井,我们在水 井边上站住,随便地说了一些话,这时才 开始出现了一种使人感到轻松的气氛……
我们去参加一个文艺晚会,我的家人 也去了。到场的有许多著名的艺人,我舅 舅彬与我邻座,与我们同桌的是一位已经 很老的过时明星,她手拿话筒,主持着今 天的晚会。她站起来,面向大家,但眼睛 却一直在看着我。她仍然保持着昔日的丰 韵,神情可亲。她手上拿着一些印制得很 精美的纸签,把上面的小方格揭开,便是 今晚对奖的号码。她给我一张,然后分发 给大家。我揭开纸签,没有中奖,但彬却 中奖了。我感到沮丧是因为我觉得我辜负 了这位风采依旧的老明星对我充满特殊意 味的期待。
在人们尽情的欢笑声中,我被遗忘在 一边……
12
这里的空间太狭小,它放不下我的这 颗心。可是心在我的躯体里,我的躯体无 法胜任把这颗心带出重围的责任。爱情是 一个美丽的躯壳,她太娇嫩,也太狭小, 她也容不下我的这颗心。我的心被束缚着 ,试图挣脱。但是,尽管面红耳赤,尽管 已经不成人样,这个牢笼却变得愈益狭小 ,这颗心已被挤压得走样,象一堆血淋淋 的肉酱,模糊难辨。我要挣脱的欲望变成 一种反弹的力,对着我自己,把我打得面 目歪扭。四面是铜墙铁壁,哪一处薄弱一 点呢,我找不到出处,找不到突围的方向 。每一次都以为发现了一个可以冲突出去 的缺口,但每一次也都在使出全力突击这 个缺口的时候发现缺口是严实地封住的死 口,一个更加沉重的力反激出来把我打倒 在地,仍然倒在这四堵围墙的中央。
13
我吃力地驾着一辆大卡车,在一条泥 泞的山道上爬行。我终于把车开到了山上 ,山顶上是一个小平原,路上到处都是泥 浆、黄土。这就是毛泽东的解放区。
许多人都在用铁锹一边挖着泥土,一 边在搅拌着。这是一群瘦弱的人,他们都 是逃亡到这里来的知识分子,一种抽象的 集体概念把他们组织起来。
有一堆砖,堆得很高,但由于是胡乱 地堆上去的,所以摇摇欲坠,很吓人。砖 堆旁边就是正在搅拌的泥巴,我怕砖倒下 来,会倒在上面,便干脆把它向另一边推 倒了。毛泽东象一个朋友一样,走过来和 大家一起吹牛。
我走在大街上,一个陌生女人走过来 对我说:
“哎,你们单位里的那个大胖子死了 。”
开始我还没弄清楚是哪个大胖子,后 来才明白她说的大胖子就是我们店里的那 个女营业员。
据说,大胖子的爷爷是一个老红军, 瑞金时期就是湘鄂赣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14
昨晚上,折来。
折问起芳,我就提到了梅。
我说:
“上次见到她,她的脸看上去很憔悴 。”
折马上说:
“性生活过度了嘛!”
我感到非常震惊,傻了眼看他。
接着,他又说:
“她又没断过男人。你以为她离得了 男人吗?她是一个需要男人滋润的人,她 有一个男朋友你不知道?”
我说:
“她不是没有男朋友的嘛?她在和谁 谈朋友?”
他说:
“不知道。她命里是这种人,没办法 。”
我不肯面对这个现实,说:
“命也有算错的时候,你别瞎说。”
他说:
“这倒也有可能。”
梅的左上唇有一颗黑痣,相命书上说 ,这颗痣“主贱”。我想起相命书上所说 的话,但我没有说出来。
我梦见梅。
奇怪的是,梅竟变成了彬的老婆,彬 是我的小舅,与梅毫不相干。
我问彬,梅这几天怎么不回来?
彬说:
“她在外面和人家搞不清爽。”
后来我看见梅。梅变得十分难看,毫 无魅力,发型也变了。我的心里毫不是滋 味,我在一种异常复杂的情绪纠结中醒来 。
下午给梅打电话,我告诉她,我想和 她见面。她说今晚正好没空,因为已有人 和她约好了,请她今晚去唱卡拉OK。那 么今晚会是谁和她在一起呢?
也许这场游戏该结束了。这场持续了 半年多的游戏,只有我一个人在玩,梅并 没有参与这场游戏,我没权力对她有丝毫 责怪。
我问自己,我是不是可以从中解放出 来了呢?
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在这个无神宇宙中 的匆匆过客。往事已矣,故人星散。人最 终是要孤独旅行的。
15
我的小屋。
门前的地上泥泞不堪,一道篱笆墙和 我的小屋相连。这是我熟悉的梦中情景, 但却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小屋里面的陈设很陌生,屋里挤满了 陌生人,但他们却是我的朋友。梅站在书 桌旁,正翻看着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名 叫“赫索格”,这些书,在我看来,都是 很费懂,很难读的,我以为梅未必读得了 它们。但梅对这些书所表现出来的兴趣, 证明她能读懂它们。于是我就说:
“这些书你想看,就拿去吧。”
她把书放进手提包里。
房间里的气氛很热烈,但我无心参与 他们的谈话,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只在梅的 身上。今天她怎么留着短发呢?她表现得 很安祥、很宁静,充满了柔情。后来我们 都走出去,来到大街上,但我们却好像是 从一个学校里走出来的。宽宽的街道,街 上有许多人,我们这些人都站在一起,互 相道别,但我却不被人注意。街道的另一 头有人在吵架,有几个人便过去观看。我 和她仍然站在一起,但我们仍然没有单独 相处,还有几个人围在我们的身边。我们 谈论着她手上的那几本书,想不到梅的见 解是那么独特。她话不多,主要都是在静 静地听。好像沉入了自己的内心,对外界 的一切都不太注意。梅看上去有一种凝重 感,象一尊雕像而让人感到难以与之交流 。但又确确实实是有着动人的生命感的女 性站在你的面前使你激动。
但是,奇怪的是,我始终只能看见梅 的侧面。而她的侧面却更加动人。
16
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但人们还能在其 中活动,大概习惯了吧。
我和柳在一起,似乎要到什么地方去 。
走到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没有人烟, 好像是一个坟场,或是一个火葬场,总之 ,与死人有关。柳说要到前面去找一件东 西,让我等他一会。他走后,就有一个人 ,非常高大,我只看见他的黑影。他一下 子就把我背起来,走到一个斜斜的山坡上 。这个山坡上横架着一架铁梯,如同煤矿 里高高的输送架。我被扔在了铁梯上,不 ,我被扔在了焚尸炉上。我大为恐怖,头 脑中立刻闪过这几个字:
“死亡之地”。
那个高大的黑影很快就离开了我,走 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总算,柳找到了我,把我带出了这个 充满恐怖、阴森、荒凉和不祥的地方。
17
我闯入了一个房间,一个女性的空间 。其中两位安祥的女士注视着我的到来, 她们是梅和芳。
在我进入房间以后,原先的格局被我 打破了,我羞愧地对她们说:
“我破坏了你们的世界。”
我想说:“我破坏了你们的神话”。 因为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看到的是猫的世 界,猫的安详和猫的和谐气氛被我破坏了 。
我坐下来,和她们形成一种三角态势 ,注视着梅,等待分娩。我说有一个希望 将会分娩,于是我们都无言地等待着。在 等待的过程中我清楚地意会到将有一个婴 儿降生;或者不是婴儿,而是燥热的夏季 黎明之前一股清凉的晨风。这股晨风代表 了一种希望,一种新世界的格局。我在焦 灼地等待着,在这一过程中,我感受到了 一种神奇的心情。我想,就会有一束光亮 透进来。
18
我日益明显地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出现 的一种病态。当一个意念出现,告诉我必 须行动,必须毫不犹豫地向目标冲击,而 且如果不这样做其危险性将更大。但是, 一个强大的内心结构(我找不到更为恰当 的词)却主宰、控制着我,迫使我止步不 前。我紧张得无法呼吸,汗不由自主地冒 出来,但我却仍然动弹不了。我的精神处 于一种自燃状态,我在这种状态中燃烧着 自己,象一堆僵硬的无法运转的废机器, 或仅是一具还在呼吸的死尸,其中潜伏着 暗火,但不能喷发出来。我的影响(这种 影响可以证明其对外界的有效性)瞬息之 间便被自己吸掉。我看到了对方那渴望碰 撞的光芒闪烁,我却无能为力。一个恶魔 、一个高大有力的黑影(就是那个挟裹着 我的黑影)攫住我不放。这时,我只有逃 避的办法,只有从对方的目光里消失。但 同时,一种羞耻感,一种犯下新罪的羞耻 感马上又来补上我一下子变得空虚的内心 。是我杀死了对方,但明知可恶却无可奈 何。我就在这种长久的颓丧中使我的整个 生活笼罩在阴影之中。我没有片刻的安宁 ,我每时每刻都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在内 心膨胀,也许再增加一点我就会被摧毁, 我已预感到自己会在这种压力的爆发中变 为一堆灰烬……
明知恶魔就在心中,这个我人生的最 大的天敌,但我却不能摆脱它的纠缠。最 大的困难在于我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和恶魔 相抗衡的力量?拿什么来与恶魔抗衡?它 又在哪里存在?如果我知道它是什么,我 还可以培植这个势力,找到那个突破口, 我可以使它成为我的同盟者加入到我自身 的对抗中。但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的存在,我又如何看到自我解放的希望 ?
19
在一个俱乐部一样的房子里,楼上, 我看见静坐在那里(静是我上一级单位里 的会计)。她给我的感觉很好,边上还有 另外一些人,大多是女人。静很漂亮,皮 肤很白。突然,我看见从她的鼻子里流出 了血,鲜红鲜红,映衬着白晰的皮肤,显 得很刺目。我很郑重地拿出我的手绢给她 ,我觉得我的这一举动是异乎寻常的。她 把手绢接过去,在脸上不停地擦着,但脸 上总有一小点血迹却怎么也擦不去,这使 我感到很刺激。
我们开始变得亲密起来,我们谈论着 一起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一起。
她说:
“我们坐在一起吧。”
我说:
“好的。”
我看到边上的一群女人在叽叽喳喳地 议论,好像在说我们俩,所以我和她在一 起总有所顾忌。
后来我好像到了一个很荒凉、有一片 没人居住的房屋前的空地上,地上有一条 横向的水泥槽,有许多人围在一起,我和 其中的一个人正在谈着话。这个人好象是 刚,但给我的感觉很平庸,属于市民阶层 的那种平庸。他说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掐死后就扔在这里的后面,连埋都没有 埋掉。我听了以后,并不觉得怎样,好像 这并不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后来我看到我的小舅彬,他平庸透顶 ,琐碎,女人腔,整天责骂他妻子。我对 他的妻子很同情,也有一些人在安慰她。 只见彬抱着他的女儿佳佳,佳佳头上戴着 一个玻璃的玩具皇冠。由于他抱着她的时 候往前倾斜了一下,结果使佳佳头上的皇 冠掉在地上,跌碎了。彬的脸上露出一种 恶毒的表情,从地上捡起已跌成碎片的皇 冠,用力地往佳佳头上套去。佳佳的头被 玻璃的尖角划破,血立刻流了出来。这时 ,我发现佳佳的脸很像行秀(一个日本和 尚),但很清楚的是,她仍然是佳佳,一 个小女孩,甚至是一个婴儿、一个女婴, 但她的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头发。彬又 拿起一块碎玻璃,在佳佳的下巴上使劲地 刮擦,很快佳佳的下巴上也流出了血。彬 用手想抹去佳佳下巴上的血,但他的劲太 大了,不是在擦血,而是在挤压伤口。佳 佳已经疼得哇哇大哭,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这个恶魔,根本没有人性,这个场面使 我震怒,我忍无可忍,捏起拳头,对准他 的脸打了过去……
20
梦中出现的几个人物:
①砚,先锋小说家。
②榕,我家的邻居,妹妹的同学。过 去我一直和她开玩笑,说要她嫁给我之类 的话。她的性格男性化,我不喜欢她。如 果我真想要她嫁给我,她是会嫁给我的。
③覃,我小学时的同学,也是我家的 邻居,著名的笨蛋,外号“脑袋”。我们 的关系不好,每次碰面,如仇人相见。
我和砚在讨论一些诗稿,可能是我们 要搞一本集子。我对他说,我有两首诗, 是很久以前的作品,但唯一的一份底稿在 榕手里,我想问她要回来,不知她是不是 肯给我?我和砚商量,就说派用场,让“ 脑袋”去对榕说,只要把底稿拿去复印后 ,马上就还给她。商量的结果,觉得这样 办是可以的。
后来不知怎么的,“脑袋”却去把榕 狠狠地抽打了一顿,榕被打得奄奄一息后 ,因为不堪忍受,遂以上吊自杀了。
我好像是在床上,或者搁楼的床上看 到她吊在那里(就是说,我可以俯看到) 。我的意念中,既是榕吊在那里,又是一 只马桶吊在那里。但肯定是榕吊在那里, 已经死了。这两个意象交叉着出现,既是 榕,又是马桶吊在那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