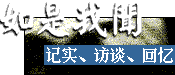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 王一梁·
八十年代的青 春:人和诗
◆我是忠诚的(阿钟)1988年底,《未定稿》使我们再次成 为了工作者,并且学会了仅仅以“工作着” 作为我们的最大骄傲。不久,阿钟与京不 特相约:京不特写《梵尘之问》序章,阿钟 写《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象这样的约定,从前在朋友们之间也 时常发生,默默、京不特和刘漫流将之称 为“口兽主义”,如果这样的工作是在相互 记录彼此的口授诗之中完成的话。但是这 一次,阿钟和京不特的约定却不能再是一 种“口兽主义”了。
这个时刻已经无法避免
往日的美景不再重来
四壁空空荡荡
墙上贴挂的肖像
只有他的目光还显得如此分明
(阿钟《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1989年的春天,到办《未定稿》卷五 时,京不特已经亡命于异国。“我的亡命如 此突然,只为前生的某个预言”(京不特《 流落于风下》)。
对京不特而言,早期的几次流浪是为 了寻找游戏,为了使相聚变得更加欢乐, 而这一次则是“为了前生的某个预言”。但 对阿钟而言,任何流浪对他都是不自由的。
朋友们都已经离开了这块地方
他们渴望的新生活
也是我所渴望的
而我的灵魂会比他们漂泊得更 远吗
(阿钟《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只有精神上的一种漫游伴随着阿钟的 一生,这似乎已经成了他今生注定的命运。
在你我的手中都有无需言明的 契约
和你一样
我也无权撕毁我们的命运
(阿钟《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然而,这“无权撕毁的命运”又是怎样 的一种命运呵。
血一样的黄昏滴洒在我的窗前
阿钟的长诗这样开始,几乎就在作出 一种预言,他的这一场生命的旅程,更多 地将在黑夜中度过。
这黑夜的狂风使我的一生都承 受黑暗
我心里仅有的一线光芒
照出我永世沉沦的结局
(阿钟《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京不特膜拜太阳,“我曾经或正是一个 膜拜太阳的人”(京不特《同驻光阴》)。 京不特迷恋花朵,“在梦里我为明天种花”。 京不特喜欢微笑,“除了微笑之外我没有 为人们带来更多”(京不特《梵尘之问》序 部)。
然而,这些东西对于阿钟而言,却是这 样吝啬与残酷。
阳光来去匆匆
只证明一个虚无的我无形无迹
花呀。你象一个妓女栽种在我的 身边
我的一生中除了微笑都不难得 到
可是,我会死得多么悲惨
因为我已经把微笑忘掉
(阿钟《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1992年,京不特与热带丛林告别,向 北走去。
这一路向北很白
这一路向北
向北走去的地方阳光很少,离开花朵 与微笑盛开的地方越来越远。
上海很远
其实
我并不愿意离开我所依恋的
(京不特《流落于风下》)
这时候,京不特在心中呼唤起了他的 青春同伴,曾经与他有过美好约定的人。
其实我可以象无数人呼唤基督 一样
向北呼唤自己
可以再呼唤阿钟或者刘漫流
就象他们呼唤基督
(京不特《站在冰上怀旧》)
虽然,生活没有给予阿钟太多的阳光、 花朵、微笑,但是,他却把这一切带给了朋 友,使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从此不 怕黑夜。
我是忠诚的
在反叛之中我保持着忠诚
每个灵魂都深藏着她播下的种 子
城墙在我心里加固
空气中鬼魅似的祥和
一个不可思议的早晨呵
我在描述这个思想
他的结构……
(阿钟《昏黯。我一生的主题》)
〔附四〕
抒情诗人
晚上,阿钟跚跚而来。经常是这样,夜 深了,阿钟会突然出现在这间屋子里,然 后,向我谈起了他的白天生活,在天快要 亮的时候,阿钟也就走了。
有时候,黎明,我们也到外面去喝酒。 小酒楼里,经常会看见一些老人,他们在 慢慢地舔着酒。看得出他们喜欢这里,这 是他们一天里最美好的时光。
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底下的世界不属 于老人。他们一张张显出醉意的脸,就象 一群苍白的鬼一样,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渐 渐逝去。
兰波四十岁死了,卡夫卡四十岁死了, 加缪四十岁死了。还有伟大的诗人普希金、 波德莱尔、可怜的坡,这个在美国聚财者 时代升起的灿烂星座。
然而他们都是真正的抒情诗人。在这 个世界上,谁对自己将死于四十岁没有出 现真正的预感,谁的文学中就不可能产生 真正的抒情力量。
但老人的魔鬼是不具有创造力的,已 经不再会使他们成为抒情诗人。
酒楼里,老人们纷纷走尽。这时候,我 和阿钟也分手了。(1992)
◆同行共天日,境况从不议(陈接余)
在茫茫无际的人海中,一本每期仅手 刻油印二十份的《未定稿》,就象漂流瓶一 样被抛入到了大海之中。
它们将漂向何方,谁是它的收信人?我 们不知道。我们仅知道,它们是写给人看 的,也只有人才配读到它、读得懂它。
只要知道了这一点也许已经足够。
没有许诺、没有义务;既不折磨朋友, 也不折磨自己;这有多好!没有大人物、没 有小人物,只有真正的工作者,这有多好! 就象一堆沙子,就象一泓奔放的流水,聚 散无常,飘无所指,如同我们的命运,就象 我们的心。多么亲密,多么自由。
当《未定稿》说“亚文化是一种废墟文 化”的时候,还只有我一个人是《未定稿》 中的真正工作者。而到了能够自豪地说“ 有了亲密的战友就能天翻地覆”时,工作 者中有了阿钟和京不特。
我们把电影《印度之行》中的一句话,“ 我们不过是一群在这无神的宇宙中的匆匆 过客”作为题记,写在《未定稿》卷五上, 这是因为命运已经无法挽回地把离散的结 局判给了我们。
又一个秋天将到了,而这个秋天却没 有果实,这一年的春天早已把中国大地上 的一切改变。
多么怀念这样的话语:“有了亲密的朋 友……”
一天。终于有了这么一天:
| 从卡欣那里知道您和你们的工作
及成果,在看了《亚文化未定稿》卷三、四,
二份文献的珍贵孤本箴言后,我是很振奋
的!一种扬眉吐气的感慨!江海湖汉几多
水……看不见同行,看不见自己,看不见亚
文化,看不见一场文化运动的实际成就,
与其实践后果的关联……终于,看到了你们!
亚文化依然存在:并且工作着!这是何 等激动人心的本土地面生活中的一桩头等 大事呵!有继续革命的战士在;有不甘于 沉沦、力渡彼岸的水手在;有思考与设计 人烟的走向与考察实在(生存)状态的思 想者在。……这样的文献,让我由衷惊喜地 觉到你是我们这个纷乱而又整套完备之时 代--所呼唤且确系被寻找的先导。一个民 间个性再造的工艺师。 保护自己,珍惜思考,教育文青(文学 青年)永葆风华正茂。 一个新大陆在浮动,那是你们的投影, 也是末世纪在新纪元的新生之可能。 让我,一个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邻居 兼文丐,再一次向你们致以敬谢之意。 同行共天日。 --1989年9月17日陈接余 的信 |
呵,“一个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邻居兼 文丐”,是我们的漂流瓶把他带来了。
在我的八十年代的青春岁月里,我没 有认识、拥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伙伴、这 样的战友。
九十年代就要开始,我就将拥有、认识 这一切吗?
〔附五〕
士兵的报酬
结识陈接余是我智力史上的一桩奇迹, 是少数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自1989 年,他写下了《在抽象和具象之间》之后, 我与他的文学对话便开始了。但我们的友 谊并没有就此开始,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是 写那种晦涩、古怪的、为我所不喜欢的“中 国式现代派”作品的人。而在我看来,写得 晦涩、写得古怪、写得不为读者所理解,就 是傲慢,就是在对读者犯罪。私底下,我也 怀疑这样的作者,他们的心灵是否低下? 是否就象传说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一群 被魔鬼所操作、引导的人。
毫无疑问,这样的人不会是我的朋友。
然而,一次偶然的读书经验改变了我 的这种看法。那是一次连续阅读了陈接余 的作品一天一夜的读书经验,而且,还是 两个人在一起阅读的:晚上十点到次日晨 六点,第二天中午再到晚上。
象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作如此激动人心 的读书长跑,是我一生读书经验中唯一的 一次。在由衷的感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注定相遇,这另一个是他的兄弟”中,我和 陈接余的友谊就有了一种真正的开始。
陈接余的《士兵的报酬》,由一封信与 两篇独立的文章组成。在这封信中,陈接 余不仅较为全面地评论了我,而且还引述 了一些我未收入在《朋友的智慧》里的文 章。当时,我想如果能将这封信收录在《朋 友的智慧》里,那么肯定能够成为一种有 意义的补充。于是在想了几个题目之后, 我最后就将它定名为《士兵的报酬》,这取 之福克纳的一篇小说题目。
几天后,我认为应该将我的这种想法 告诉陈接余,便与他联系了。在电话里,他 兴奋地告诉我,他也正打算打电话给我。 原来,他已于昨天完成了一篇论我的文章, 并且打算从今天开始起写另一篇论朋友的 文章。原来他一直在悄悄地关心着我和朋 友们。
见面之后,我问他那篇刚写完的文章 的题目是什么。这一回,他的回答真正使 我感到惊讶了,因为它的题目竟也是《士 兵的报酬》!所不同的在于它还有一个副 标题:“二百条胳膊”。也许这并不奇怪, 因为就在几星期前,他对我说起了福克纳 的《士兵的报酬》。当时,他对我是这样说 的:
“那时候,福克纳正在跟舍伍德·安德 森学小说。一天,在街上遇到了舍伍德夫 人,夫人对他说:‘舍伍德让我转告你,如 果有一天,你再也不想拿你所写的小说给 他看了,那么他就将你的小说拿去发表’。”
说到这里陈接余大大地感慨道:“从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舍伍德是多么的人道。 因为,如果福克纳在写小说的时候头脑里 所想的总是舍伍德将怎样看待他的小说, 那么,他的小说就不会写好了。”
那篇福克纳第一次没有拿给舍伍德看 的小说,就是《士兵的报酬》,也是福克纳 发表的处女作。
然而,不管怎么样,几个星期之后,当 我听到陈接余嘟嘟哝哝地对我说“我在写 这篇关于你的《士兵的报酬:二百条胳膊》 时,我心中一点也没有想到要给你看”时, 我只能是为我们俩在同步性中所达到的共 识感慨万千的。
现在,这封陈接余致我的信,及《士兵 的报酬:二百条胳膊》已经成为《朋友的 智慧》这本书的代跋,我认为这正是适得 其所。(1992年)
◆他成了一个现代派
我疲倦了,终于疲倦了,在沙发上一躺, 整个下午就过去了。太阳在天空上映出最 后一道霞光之后,四周就变得很黑了。他 出现在这间屋子里,身体伏在桌子上,在 轻轻地翻动着这部书稿。
他的背影后面,窗口上,已经隐约地出 现了几点星光。屋外好象很冷,树叶快掉 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4日。
十八年了。
噢,没有,我们只是十三年没有见面了。
而你每年给我寄来的贺年卡我都收到 了。你寄了总有十年了吧?
哦,是的。我心里总是惦记着你,可你 却连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我们在那时感 情是很好的,我是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的。
是么?
你都回忆起来了么?
我们是在一起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当时是谁教我们绘画的?
一个女孩。
你怎么还记得?
我还记得黄毛,她后来属于你的了。
你也知道她?其实这些年来,你没有在 我的视野里消失过。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你的那次画展我本来是打算来的。
我也知道你的情况,听说了你的书。
你今天怎么会来了?是偶然的出现吗, 还是为了作我们青春的最后道别?!
这个十三年没有见面、偏偏在今天出 现的人,就是十八年前的故事中那个“满 脸稚气,一心想跟着两个少年到田野上去 散步”的倪卫华。
他已经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一个“ 现代派画家”,再过几天,他将要以他的“ 老中医”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举行一场“艺 术暴动”。黑格尔和托尔斯泰是越来越不 会同意他的了。
而这些年来,我们虽互不见面却仍然 彼此知道、了解,因为他是我哥哥的妻子 的初中同班同学,又是陈耳的妻子的同事, 总有人在传着话。
这里存在着一种难解的谜,或者说缘。 而他的出现,并在这个时候为我的《朋友 的智慧》设计出了这样的一个封面,对我 来说,其中仿佛又预言着什么。
仿佛有人,或者仅仅是岁月的缘故,使 得“朋友的智慧”的字体出现了剥落的痕 迹。它的粉末正向着大地纷纷飘落,而它 的背后则是一片蔚蓝,好象一无所有,又 好象就是无边无际的天空……
这难道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青春的最后 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