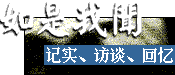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王一梁·
八十年代的青 春:人和诗
◆我可以放弃诗歌写作(孟浪)
从人的热情洋溢程度上讲,他们同
样都是把崭新的感觉和思想带给了我们,
在这里,天才和革命者的确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这种界限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真正的
艺术家必然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必然是
一切腐朽事物的颠覆者,因此,当1986
春天,这块土地上惯于滋生出来的古老的
瘟疫,突然降临到默默身上的时候,朋友
们没有惊讶得目瞪口呆。
其实,只要我们的政治格局没有变化,
国家总是大于社会,政治总是大于艺术,
那么,默默的遭遇事实上也会是我们这里
的每个人迟早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命运。而
这场瘟疫之所以最先光顾了默默,因为在
当时,默默是我们这群人中,一个成熟得
最早的诗人。
而朋友当中,一个最早从行动上明确
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则是孟浪。
198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默
默正坐在他的违章建筑物中聊天,突然,
从窗洞里钻进来了(这间房子的结构就是
这样的,窗子当门使用)一个眉清目秀、
穿着一件汗衫的人。他自我介绍说,他叫
孟浪。
哦,孟浪!我们差不多是一起喊了出来。
作为一个强者诗人,这个名字我们早就听
说过了,而这些日子里,默默和我也正在
四处寻找着他。
从孟浪口中听到的相信,的确令人兴
奋。全国到处有年轻人聚集在一处从事艺
术、写作活动。他在外地已经跑了半年多,
不仅见到了许多正活跃着的诗人,而且还
见到了食指,可惜的是,他是在一家精神
病院中见到这位新中国诗歌圣徒的。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天才的写作常常
伴随着不幸。”
那么,就让我们这一代人去亲手把这
个不幸的写作者故事结束吧,让我们现在
就去从事对整个社会的启蒙:艺术无罪,
艺术永远不会是灾难的同义词,就算艺术
的力量足以毁掉一个国家,可艺术还是人
类最好、最可靠的朋友。艺术独立,这是任
何人、任何政治权力都无法夺去的生存权
利,柏拉图的理想国无权这样做,斯大林
的极权社会更没有这样做的权利。艺术家
自有艺术家的尊严,这种尊严远比国家的
尊严更加值得尊重,因为正是他们,表达
了一个民族的最高声音。
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
动核的念头
手指按着自己上衣的某一颗钮扣
那个人对面前赤裸裸的果实
动核的念头
“如果需要,我可以放弃诗歌写作,
去做一个艺术活动家。”孟浪微笑着说。八
年之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迟早都有
可能遭遇到的命运”降临到了孟浪的身上。
不幸的写作者的故事并没有在这块古
老的土地上结束。
那个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
他在一片空白里
上衣象一束枯萎的花朵
在他无力的臂弯里
--摘自孟浪《那个
人站在一个国家的对面》
〔附一〕
天空中的飞鸟·田野上的百合花
--默默、孟浪印象记
创作《城市的孩子》、《我们的自白》
的时候,也正是默默最渴望去远方流浪的
日子。
当时,默默的作品,其风格类似编年史。
他象说话一样,象讲故事一样地写作。
在1983年的写作札记上,他写出了“桃
花源里正走着一个侦探”、“没有嘴唇的歌
女在歌唱”、“断臂的维纳斯拎起了一挺马
克辛机关枪”。在这些断章里,讲故事的才
能,优雅的幽默感以及对理念世界中秩序
的感觉力,开始放射异彩。
我们这一代人躬逢盛世。在那些日子
里,默默本人的生活方式也象古老的行吟
诗人一样。他在这座城市里到处为家,崇
拜遥远,寻找人群,诵颂他的作品。
怀着天真的执拗,认为这个世界需要
启蒙,人性需要新的解放。这样,在1984
年,便有了《城市的孩子》、《我们的自白》
这两部杰作。那时,他才二十岁。
作为一个早熟的天才,默默的文学之
梦是要将整个世界和人生都写进作品之中,
这是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如果一个艺术
家正被这种意志所震撼所控制,那么在这
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去写呢?哪怕是
司空见惯的东西,哪怕是已被一再重复的
古老思想,再写一次又有什么关系?只要
写作带来了启蒙,只要写作带来了进一步
的自由和解放!
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无畏的世界里的艺
术家,应该是幸福的。因为,它必然要求作
者将他的一生本身作为一部作品去塑造,
从而真正实现其作为人的全面自由。然而,
更多的地方却有可能只是失败,因为,象
这样的写作同时也必然会要求作者与那些
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彻底决裂,尤其是在
中国文化进入了消费时期,越来越具有第
三世界性的时候。
命运看来注定就是失败,必与寂寞和
勇气为伍,却也因此为我们带来了人性高
原上的一派风光。
在这一派风光里,就有一群人的流浪;
一群任何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少年英雄,他
们最后在大象的遗像里找到了最终的归宿。
总归会有一天会有人理解我们
理解我们为什么把大象的脸装进黑
框子里
总归有一天会有人相信我们
相信我们就是她死去的哥哥
她冲进编钟里
向那时的世界发出摹仿我们的哭声
她仰脸问妈妈我们的名字
妈妈将突然放声大哭
--摘自《我们的自
白》
田野上的百合花无力选择自己的生
存空间,她只能在山岭和田野上满山遍野
地盛开,这是其生存性的致命悲剧。如果
一旦离开了泥土,成为了摆设,那么也就
只能是异彩沉沦。然而,飞鸟呢?
认识孟浪,是在84年的一个夏天。他
刚结束了半年外地的漫游生活,他带来的
消息是令人振奋的,全国各地这一代诗人
正在迅速崛起。象我们一样,整个世界都
渴望新的童话、新的神话。这个世界正需
要更多的新实验,更加大胆的行动。
心灵既然燃烧了起来,那么便不会熄
灭。几个月后,孟浪继续从这座城市里消
失了。那时候,他微笑着,说他可以放弃诗
歌写作;只要需要,他宁愿去成为一个艺
术活动家。就象兰波能够放弃诗歌,托尔
斯泰放弃写作,维特根斯坦放弃哲学。
“如果我还不是一个人,我又怎么能够
成为哲学家呢?”(维特根斯坦语)
当整个世界和人生都不值得去体验了,
写作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行动比写作
更加壮美,那么,为何不立即去行动?
飞鸟也许飞得太高,飞往的地方太多,
因此,他必须格外注意路标的诱惑。1984
年,孟浪警告人们:“必须警惕形式的诱惑
”。但是,孟浪自己最后却建立起了一种
诗歌形式。
本来嘛,飞行着的飞鸟,其飞行的形式
本身就在于创造着一种飞行的美。在它掠
过名山大川的时候,旨在尝试飞翔那些云
层不到的时候;在阳光最灿烂的地方,或
者空气最稀薄的地方,飞鸟便敏捷地变换
着姿势。
大地上的观察者也许弄不明白,为什
么飞鸟尽管千姿百态,却仍然摆脱不了它
的流线简单。这时候,也只有最懂行的观
察者才会真正地告诉你:飞鸟的本性其实
追求的仍然是飞得最高,而直线就是飞得
最快的道路。
默默与孟浪,一个挥霍文字如土,一个
惜墨如金。但是,同样写下了他们的青春
故事。作为一个启蒙者、解放者的形象,这
一部值得我们去写的编年史里,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脚印。(1989年)
◆既然相聚了,就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
事业(刘漫流)
暑热难熬的白天终于结束,躺在藤
椅上昏睡了整个下午的我们醒来。从长江
入海口处吹来的晚风,使我们重又变得精
神抖擞。刘漫流站起来,用手指着藤椅,
张开嘴,朝我笑着说:“这两张藤椅其实就
是你和我。那张黑一些的是你,白一些的
是我,一阴一阳。《易经》上说,一阴一阳
谓之道,我们其实是互补的。”
1984年我的学生时代结束了,有意味
的巧合在我的命运中再次扮演起了任何东
西都无法替代的角色。
当我和刘漫流在卡欣家里第三次巧遇
的时候,我们便决定另找一个地方,一起
去酒馆喝酒。
面对这几个月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的巧
遇--他和我,一个去了卡欣家里三次,另
一个去了四次,可偏偏就三次相互遇上--
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都猜想这里面或许
就存在着一个类似斯芬克斯之谜的东西。
上海的亚文化到了1985年,该遇见的
人大都相遇了。
“既然相聚了,就会有一番轰轰烈烈的
事业”。这在当时的朋友们的心中已变成
一种非常普遍、强烈的预感和心愿。
这样,到了1986年的夏天,当刘漫流
在密山新村有了两间空房子,听到他邀请
我和他一起搬去同住的消息时,我也就立
刻想到了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那时候,我已失去工作,正可以象一个
流浪汉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到处住来住去呢。
刘漫流是诗人、学者,还是朋友之中的
一个类似苏格拉底式的谈话哲学家。与他
谈话无疑就象是在经历一次神奇的催眠术。
太阳在照耀着,热浪灼烤着新村的水
泥建筑物。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一天,学
识渊博的刘漫流翻开了一本厚厚的书,指
着上面的字这样对我说道:“阿修罗居于
海上,与诸天斗法。只要发出an音,诸天
便不斗自败。由此可见,阿修罗实际上是
一个艺术家。”
《阿修罗家族》是我在85年底根据三
句格言创作出的一篇寓言小说:“天下越
乱越好,反潮流总是对的,老子就是不信
邪。”那时候,我除了记一些思想片断之
外,什么都不写,《阿修罗家族》实际上就
是当时我唯一的一篇可以算得上是艺术类
的文章。
而我的这群朋友却都是诗人。
于是,我懂得他的意思了,因为在那些
日子里,刘漫流正把他自己以及默默、孟
浪等朋友们的诗歌创作活动称为“海上诗
群”。而创立一种“流派”和“主义”,也正
是我青春年代最大的梦想。
那么,我的青春、我的文学生涯,我的
名字是否能够和这些朋友们联系在一起呢?
在往后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我们是否始终
都能够相濡以沫、荣辱与共呢?
现在,既然一种“虚构的产物”竟然还
有一种“历史的确证”--“阿修罗居于海
上”,这种巧合的发生使我确实应该好好
想一想未来的道路了。
那一天感觉起初象平常一样
白天也没有出现任何奇异的迹象
夜晚来临了
灵魂总是伴随着夜晚到来
我们谈话时,他保持沉默
而当我们沉默时,他说出了第一句
话
正如歌中唱道
“我记住了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将记住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
--摘自刘漫流《通
灵之夜》
〔附二〕
密山的一天
| 阿修罗拯救人的方式,就是什么也
不做;于是,他做了一件顶顶无用的事情。
--题记 |
阿修罗小时候常常对人说:不要讲,
不要讲。
青年阿修罗常常用眼睛瞪着人,沉默
不言。晚年阿修罗才逐渐领悟到了沉默对
于他人拯救的道理。
但当阿弟问起阿修罗什么是沉默时,
阿修罗摇着头说这是思考的前提,说出来
就不是沉默了。
A:阿修罗的奇迹
| 眼睛是看到的东西,耳朵是听到的
东西,鼻子是闻到的东西。阿修罗是不听,
不看,不闻,人们以为这就是沉默的阿修
罗的状态。 于是,阿修罗离开了这个世界。 --阿修罗与世界 |
这时候,阿修罗抠着脚丫,谈论痛
痒辨别之艰难,悲喜交加,从他坐着的椅
子上偏过脸来望着阿弟说:“痛或痒才是
唯一的人的感觉。牛津学派说的都是不关
痛痒,不痛不痒的事情。”
阿弟听到这里,内心一阵激动,他关心
语义学问题已经有数年了。他这才明白过
来,休息是需要的,阿修罗确实并不需要
睡眠。
阿弟在大白天也连续性地看见梦。
B:阿修罗家族的生活方式
| 阿修罗说:星期三、星期四通宵写
作。 本世纪人太懒惰,无法完成巨作。人们 必须付出双倍的时间工作,必须有一天夜 晚不熄灯。 这时候,他们说你的脑子坏了。 --日记 |
京不特已经将一只香蕉吃完了,他
用洗脚布抹了抹嘴,接着又拿了一只苹果。
他说今天不是日子。
听见这句话,阿弟一点思路也没有了。
语言也开始露出它狰狞的牙齿。
我们要用思想践踏语言。
这时候,天大亮了。
京不特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这一
夜,他们枕一个枕头,盖一床被子,据说那
条洗脚布是女人用过了送来的。不流说,
明天,他要好好洗一洗了。
京不特还没有醒来,他在不停地梦呓
着。
冯阿修罗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
刷刷牙。
!!!!!!!! !!打倒衣服!! !!!!!!!!阿修罗每次从海边回来,心里完全想 着的就是京不特的脚是否干净。
京不特高呼完口号之后,就醒来。他坚 决要让世界看见他已经洗过澡了。
阿修罗想到,已经到了应该坚决地不 见外人的时候了。
C:阿修罗如是说奇迹
| 过去的宗教,就是乡下人读了点书。
--日记 |
阿修罗的眼睛,看人非人,非人是
人。阿修罗从来都是两句话一起说的。对
他说过的话,阿修罗应负全部责任。只有
人才不配为自己负责,请看看,他们什么
时候负过责。
阿修罗说:“好久没有听见人说贼是贼
骨头了。”
阿修罗摇着椅子,抬起右腿,想到时代
的变迁,于是仰天大笑起来。
阿弟为大师的喜悦感到内心奔放。几
天后,阿修罗以如此的评价作为酬答:阿
弟不声不响,最近常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有苗头呵。(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