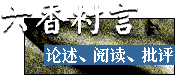現象學小說宣言
1998 年12月12
日下午,北京近郊的無名作家samsa在他自己的那台過時的
Pentium 100的顯示器面前寂寞地宣布了“現象學小說”的誕生。這個在文學史如此重要的事件就這樣靜悄悄地發生了:沒有節日的煙火,也沒有人群的狂歡。其實最初當 samsa
還是一個無知的少年就選定了文學這條不歸路的時候,他就早已預料到:即使是成功,他的成功
也將是闃無聲息的──果然……
當天夜裡,當他想向他的女友(也就是他後來的妻子:婕西婭──蒙古族)通告這個消息時
,他卻已經在朋友的生日“宴會”上爛醉如泥,
結果只說出了那陳腐無比的然而卻又是發自肺腑
(或者說:發自肺腑然而卻又是陳腐無比)的三個字:“我愛你!”
盡管這三個字的表白沒有得到足夠振奮人心的回應,但畢竟這個日子已經銘刻在作家 samsa
的生命中,永遠不可能忘懷了。
在發現(或者發明?)“現象學小說”之前
,未來的作家 samsa走過了一段非常曲折、非常痛苦的道路。圍繞著“表述 什麼”以及“怎樣去表述”兩大問題的探索幾乎
耗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智慧,以致於他的日常生
活簡直被搞得一團糟。他辜負了溺愛他的父母對
他的期待,挫傷了對他寄予厚望的鄰人們的愛心
,也對不起他的老板每個月定期(不管他的工作
成績如何)發給他的薪水(他為這點微不足道的
薪水感到內疚),總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
的一個典型的墮落者、失敗者──盡管對旁人也
許並不是十分明顯,但對他自己而言,這卻是一
清二楚的事實。
然而,這一天,報償終於到來了──不光為
了他付出的勞動,也為了他義無返顧地忍受了的
良心的譴責。作家(盡管他還沒有發表過一行作
品,但由於他忍受過的痛苦和他最近的成長,他
在這個自封的稱號面前已再無愧色) samsa
永遠感謝水木清華 BBS給他
提供了第一批真誠的讀者,如果沒有這一批讀者
,也許他已經象許多這條狹路上的前驅者一樣喪
失了寫作的勇氣。
是這樣的:在這個看起來非常平淡的下午, samsa的筆開始試著描寫一
個不可思議的題材──他描寫了一碗米粉(一碗 “辣雞粉”,也就是他當天中午在中關村
320 終點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米粉妹”裡作為
午餐吃掉的那碗──後來的文學史家關於這碗米
粉做了非常詳盡的考察,並據此就文學與飲食文
化的關系寫出了數以百計的具有相當學術水平的 論文)。
當他描寫這個題材,並剛剛寫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感覺到了這寥寥數百個漢字裡包含著的革
命性力量。這種力量讓他振奮不已──畢竟,漢
語的文學世界沉默得太久太久了,太需要一種振
聾發聵的革新。
不過還是讓我們不要沉迷於空洞的呼喊,讓
我們憑借一種安靜的理智從容道來吧──
說起文學師承來,雖然 samsa
常常自詡為博覽群書,但真正促成他的“現象學小說”的誕生的還是要從他早年(高中
2年級時) ──可以說是過早地──閱讀的那篇《惡心》談
起。這部通常被歸入存在主義的經典作品,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卻與本世界上半葉成為西方哲
學主流的現象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那段著名
的關於樹根的描寫,就是在現象學的方法指導下
的產物:全神貫注的意向性,判斷的懸置,以及
詞語的還原。可以毫不諱言地說:“現象學小說 ”的一切要素已經具備了。
其實這種以全新的、不帶任何成見的、富於
洞察的冷靜眼光重新觀照世界的努力在所有偉大
的藝術家(卡夫卡,裡爾克,卡爾維諾, etc
)那裡都曾經有意無意地出現過,唯一具有創新
意義的是:這一次,這種努力終於自己認識到了 自己。
還是讓我們來具體講述一下所謂“現象學小 說”的來龍去脈吧!
正象前面提到過的,不妨按照“全神貫注的 意向性”,“判斷的懸置”,以及“詞語的還原
”三者的順序一一敘述(雖然實際上這三者相互
滲透、密切相關,甚至在邏輯上根本就是同一的 )。 先說說“全神貫注的意向性”,這是一種真
正的藝術家態度,然而又恰恰是被大多數玩弄文 學這個“意義的藝術”的“藝術家”們所最容易
忽略的。大多數文學家是不屑於觀看這個世界的
,他們只從詞語的層次去認識這個世界,他們對
事物幾乎是“視而不見”──而且越是一種成熟
風格的玩弄者越是這樣,最極端的例子也許可以
舉那位幾乎一輩子沒有下過樓的大詩人 Emily Dickinson吧!──同樣的,一個色盲的作家
照樣可以寫出紫嫣紅,一個對音樂一竅不通的
作家也不妨把諸如“對位”、“賦格”這樣的詞
語驅使筆端,令其奔命不暇。這或許可以看作文
字書寫者的自然優勢和天賦特權,但從另一方面
看來,卻也不可避免地使作家疏遠了他所生活的
世界,以致於最後的極端的結果就是:“能指”
終於失去了“所指”而成為純粹符號運算的算籌 。 可以說,這種把目光重新投向世界努力並不
新鮮(太陽底下無新事),早些的:巴納斯派的
詠物詩,裡爾克受羅丹影響後寫出的《新詩集》
,晚一點:新小說,特別是娜塔麗-薩洛特和阿蘭 -羅伯-格裡耶所進行的卓越探索──這種探索的
價值至今為止還沒有得到閱讀界和闡釋界的足夠 承認。
然而,就象我們曾經提到過、並且為了避免
重復將不再提到的那樣,“現象學小說”的貢獻
在於充分意識到了自己的目的和特點。
因此, samsa提出恢復對世界(事物)的重視,恢復對現象(表象)的直接的、無比耐心的觀照──作家應該象畫家一
樣了解他所要描寫的對象,應該象寫生時一樣注
視他的對象,直到把這個對象看清為止。“現象 學小說”家們所最津津樂道的榜樣是裡爾克的《
豹》,除了這部作品本身的完美,他們更重視它
所借以產生的那個過程──它是在一雙宛如雕塑
家一般敏銳的眼睛的長達三天的耐心注視下油然
生長(是的,生長)出來的:
“只有時眼帘無聲地撩起。──
於是有一幅圖象浸入,
通過四肢緊張的靜寂──
在心中化為烏有。”
這裡,個人的“情緒”沒有位置,抽象的“
理論”沒有位置,所謂的“詩家語”(也就是固
定下來的陳詞濫調)也沒有位置,一切都產生於
一雙眼睛和眼睛後面那些富於知覺綜合能力的大
腦灰質的辛勤勞動了;這裡,第一次,作家(詩
人)成了一個問心無愧的勞動者,當他結束了一
天的工作之後,他可以象一個滿身顏料斑痕的油
畫繪制者一樣心安理得地入睡。
這真了不起!真的,這難道不是一個創舉?
使文學創作者一勞永逸地擺脫不勞而獲的恥辱,
使小說家獲得無窮無盡的創作源泉──這是多少
代文學家們夢想過然而卻始終未能實現的夢想?
由此並且延伸出一種心理學,在這方面,同 樣的,“現象學小說”也可以找到它的師承,它
既否認那種將復雜的(這世界上還有更復雜的事
物嗎?)人類心理現象簡單歸結成若幹概念的傳
統心理,也無法接受雖然富於想象力和創造性卻
近乎人工炮制的當代神話的精神分析學,而是向
以統覺、完形作為基本出發點的格式塔心理學和 建立在“無比耐心”的臨床觀察之上的結構主義
發生認知論(偉大的小老頭皮亞傑永垂不朽!)
致敬:它相信人類精神和肉體的統一,相信瞬間
生理、感官、心理以至理智的全面復合,反對任
何一種分裂,反對任何一種揚此抑彼,任何一種
柏拉圖主義,任何一種形而上學。
正因為“現象學小說”既是一種文學理論又
是一種文學實踐,同時又是心理學、認識論和哲
學(辯証法)──其實本質上只是一件事:我們
怎麼看待世界,因此 samsa
覺得它是一個革命,為了這個革命他決定放棄自
己一向採取的那種頗能取悅於人的謙虛謹慎態度
,大膽為這個革命張目、傳道,在這個使命面前
,他迄今為止在 BBS上取得
的那一點點名聲(這種名聲很可能會因為他現在
所表現出的“狂妄”而失去)簡直不值一提。
前面已經說到,所謂“現象學小說”的三個
特征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從而從第一者即可推
導出第二、第三者。“懸置判斷”事實上既是“ 全神貫注”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帶著滿腦子
的成見,懷著求証先驗理論的目的來觀察的眼睛
注定是浮躁的,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全神貫注 ”,而另一方面,隨著觀察時間的延續,隨著觀
察程度的加深,所有的簡單判斷(事實上,所有
的判斷幾乎都是簡單的,是為了滿足實用需要而
不得不採取的權益之計)必然逐漸破碎、瓦解─ ─隨之,用來描述這些草率的、權益的判斷的“
詞語”也必然不能免於破碎、瓦解(詞語的還原 )。
因此在“現象學小說家”面前世界裸裎,如
同原初時一般新鮮;除去了蒙在一切事物之上的 “先期判斷”的遮蔽,觀察者的眼光可以直達物
體的本身,直接面對物體的形、色、味、質,這
一切都前所未有地充滿活力,滿載著豐滿、原始
、尚未開發的描述可能,從而成為藝術家創作的
無窮無盡的質料源泉。“現象學小說家”擁抱這
個世界,既然所有的先期判斷已經懸置,既然所
有過急的取舍已經放棄,他沒有理由不去擁抱這
個世界,這個世界的一切面貌、一切表現、一切
經驗,都在他的興趣和表現范圍之內──沒有什
麼是神秘的、禁忌的、尷尬的、不可言說的,一
切都可以被說出,也應該被說出:這就是現象學
小說的任務,唯一的檢查官只是作家的審美良知
(這種良知不同於道德良知,它實際上是一種能
力,一種天賦和辛勤工作的贈予的混合物)── “現象學小說家”是普遍型的藝術家(“我認為
一個不是什麼都會畫的畫家是不能稱為畫家的” ──波德萊爾《維克多-雨果》)。
因此“現象學小說家”永遠是在場的,他只
承認此時此刻呈現給他的肉體、感官、心理和理
智的一切:如果他有過去,那只有當這個過去在
此時此刻以鮮活的記憶的方式復現時,他才承認
這個過去;類似的,如果他有未來,也只有當這
個未來在此時此刻以鮮活的可能性的姿態跳動於
他的選擇能力面前時,對他才有意義。他的時間
觀裡事實上只有現在,他的小說裡的時態也將永
遠是現在時──概述原則上只作為當下的一種回
顧和靈機一動的綜合而存在。他在小說裡追求的
將是:抓住那個含義豐富的時刻,把那一刻的經
驗的全部豐富性記錄下來,這個記錄最後綜合成
一個有機體,而時間就包含在這個有機體裡,當
閱讀行為發生的時候,這個時間就帶著它的全部
有機性、全部豐富性在讀者的心靈中復現,就如
同偉大的時間藝術家斯旺-普魯斯特把一塊浸過茶 水的“小馬德萊娜”點心放進嘴裡時所發生的那
樣。
因此“現象學小說家”回避宏大敘事,回避
大而無當的詞語,也即:回避他的經驗不可及的
一切,回避(或者說暫時回避)他的方法和他的
藝術修養不可及的一切。面對大的詞語、大的敘
述,他採取的策略是將其擊碎,把一個詞語分解
成無數更明確、更直觀、更原始的詞語,把一個
概述分解成無數更耐心、更直接、更豐滿的微敘
述(細節);面對遠(這裡的遠指的是“能指” 和“所指”)的詞語,也即:層層相因或者陳陳
相因的詞語,他採取的策略是窮本溯源,一直追
溯到最初的那個從鮮活的經驗中躍出的本原的詞
語,然後,如果有必要的話,再反過來,一步步
順流而下,通過一種小心翼翼的歸納法回到他的 出發點──從這個角度看,“現象學小說”是一
種語言的還原論,而“現象學小說家”所做的工
作則與語言分析學家的工作相近,當然,前者是
經驗的,後者是理論的,前者是特殊的愛好者,
而後者則只關心一般。
因此“現象學小說家”是一個獨立的修養者
和探索者,而“現象學小說”則是一樁緩慢的事
業,在這個事業裡,耐心是最珍貴的一種素質。
不過不可誤會,“現象學小說家”的耐心不僅僅
是表現在斟酌字句和提煉風格的時侯(否則他怎
麼與福樓拜式的自然主義相區別呢?),對他而
言,更重要的是在用一種窮本溯源的歸納法去認
識世界時表現出來的耐心:他觀察,直到敘述從
中躍出;他積累經驗,積累記憶,直到敘述在裡
面自然而然的形成;他積攢自己能使用的詞語,
積攢自己明確知道其所指的詞語,當他使用這些
詞語時,這些詞語所借以發生的鮮活經驗,以及
這些詞語從那個鮮活的經驗出發走到現在這一步
所經歷的全部歷史象一座龐大的冰山一樣潛藏在
他所書寫的文本的深處。
因此對“現象小說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循
序漸進”。他從來不逾越他的藝術素養的當前階
段,從來不勉強去做、去說超越自己當前能力所
及之外的東西,他木訥、謹慎(有時謹慎得有些 討厭──君不見市場上的無知者們多麼擅長對“
國際形勢”發表滔滔不絕的雄辯?),他亦步亦 趨,他──後發制人。他是一個蝴蝶收集者,一
個在田野工作的考古學者,他宰殺牛羊,捕捉鳴
蟬,他是一棵緩慢生長的植物,經過長年累月的
準備,他將擁有無休無止的花期──他的東方式
的心靈是柔韌而且寧靜的。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現象學小說家”將只對
物體發表意見,他雖然以“新小說”作為他眾多
老師的一位,卻並不停止在那裡,他不是“客觀 主義者”(事實上,羅伯-格裡耶也並非所謂客觀
主義者),在他的世界裡,並不只有物體,除此
之外,還有注視著這個物體的那雙眼睛,還有通
過視神經連接著這雙眼睛那個大腦,還有供給這
個大腦營養物質和感覺材料的那個身體,還有人
,還有社會……如此擴展開去,以至無窮。──
但是,這一點是正確的:他從物體──“開始” 。
“現象學小說”照樣可以對政治、經濟、歷
史發言,但那將是在這些詞語在他的字典裡不再
那麼飄忽和含混之後,也許,經過數十年的辛勤
工作和思考,一個“現象學小說家”甚至可以開
始談論(比如說:)“社會主義”,但也可能,
這會需要許多代“現象學小說家”的持續地相繼
傳承的努力。
因此“現象學小說”是一個真正的事業,是
值得我們為之付出的一個事業。它是可持續發展
的,它不是一種曇花一現的文學新潮,實際上,
它根本就不“新”,它只是從一切傑出的藝術家
那裡學到了他們的秘訣,並且充分意識到了自身
,它本質上是一種解除遮蔽後的新的現實主義─ ─無邊的現實主義。
現象學小說家的必讀書目(簡要) 哲學類:
胡塞爾《純粹現象學通論》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
莊子《莊子》 皮亞傑《發生認識論》,《結構主義》 列維-斯特勞斯《原始思維》
《微精神分析學》 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學》 文學類:
安德烈-別雷《彼得堡》 普魯斯特《在斯旺家那邊》
卡夫卡《布雷齊亞觀飛機記》,《日記》
喬伊斯《都柏林人》 裡爾克《馬爾特-勞裡茨-布裡格手記》
梵-高《書信集》 薩特《惡心》 阿蘭羅伯-格裡耶《弒君者》
卡爾維諾《帕諾馬爾》 ■﹝編輯: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