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只夢想著美國"
他們只夢想著美國
能迷失在一千三百萬柱大麻中:
“這東西像蜜一樣香甜,
盡管它會讓喉嚨冒煙。”
躲開谷倉裡的黑暗
他們現在該是大人了
兇手的煙灰缸也更自在了-
湖是一個淡紫色的立方體。
他右手握著一把鑰匙。
“請,”他欣然道。
他三十歲。
那是在我們還能
在晚上開著車穿過藥蒲公英
走上數百裡路之前的事。
當他的頭疼越來越厲害時
我們停在了一個有電報的加油站。
這個時候他只留神征兆。
雪茄算不算一個征兆?
還有鑰匙?
他慢慢走進臥室。
“要是我沒有跌倒在起居室的桌子邊
我就不會摔斷腿。要是在床邊退著
往回走又會怎樣呢?對解放
我們無能為力,只有懷抱對它的恐懼坐等。
沒有你我就迷茫了。”
我的色情替身
他說他今天不想工作。
這沒什麼。這兒在屋後的
蔭涼處,不受街上喧鬧聲的幹擾,
你可以將各種舊日的情感重溫一遍,
去掉一些,另一些留下。
我們之間的嘴皮子
耍得越來越厲害了,裡面可使
事情復雜的情感越來越少。
可會帶出另外的東西來?不會。它已是最後的事物。
你找到的話題總是迷人,常先於夜晚
將我解救。我們乘著夢四處
漂流,就像在一只冰制的駁船上,
滿是星光的疑問和分歧
讓我們保持警覺,當那些夢降臨時
老想著它們。一些發生的事。你這樣稱它們。
我這樣稱它們但我可以將它們掩藏起來。但我沒有選擇這樣去做。
謝謝你。你一直是一個讓人愉快的人。
謝謝,你也一樣。
一個年輕姑娘的思緒
“真是美好的一天,我不得不從高樓上
給你寫封信,以表明我沒有發瘋:
我只是在空氣這塊肥皂上滑了一跤,
淹沒在世界這個浴缸裡。
你人太好了,不能為我過多傷心。
我現在就讓你走。署名,侏儒。”
下午快盡我還沒有留意。
微笑仍然在她的嘴角閃露,
仿佛已有好幾世紀。她總是知道
怎樣十足的興高採烈。噢,我的女兒,
我的甜心,已故老板的女兒,金枝喲,
你不會在路上走多久吧?
四十年代片子
軟百頁帘投在粉牆上的影子,
蛇樣植物和仙人掌的影子,石膏動物的影子,
將那凝視的明眸中的淒惻悒鬱
聚到了虛處,一個太空黑洞般的洞裡。
只穿著胸罩和內褲,她徐徐走到窗前:
嗤 !揚起窗帘。一段脆弱的街景自動呈現,
薄餅般的行人,天知道要到哪裡去。
窗帘緩緩垂下,百頁板緩緩向上合去。
為什麼總要這樣結尾?
一個露台,有個女人在讀書,頭發飛舞,
這與她身上所有未交待的內容將我們拽回她那裡,與她一道
陷入夜晚本身無法解釋的寂靜中。
書房的寂靜,蹲在底座上的電話機的的寂靜,
但我們也不是非要重復發明下面這些呀:
它們已消失在故事的情節中,
“藝術”那一部分─明白哪些重要的細節必須略去,
人物性格應該怎樣發展。那些太真了
不敢多看的東西,因而也是假裝的、然而現在卻充斥
書本的東西,
那些老呆在戶內的人,而你已離不開戶外
當你發現自己從來沒有停止過嘲笑死亡,
它的背景,門廊邊上的的晦暗籐蔓。
兩個場景
1
行為本真時我們能看到自己:
從每一個角落我們得到不同的饋贈。
火車載著歡樂駛來,
濺出的火花照亮了桌子。
命運引導著引航員,這就是命運。
好久我們沒有聽到那麼多消息,那些噪音了。
日子既溫暖又愉快。
“我們在你的發間看見了你
空氣擁著山尖憩息。”
2
好雨在給運河機械塗油。
或許這是總體上都很誠實的一天
在世界的歷史上都沒有過前例
盡管它的氣息並沒有特別的權威性
反倒很枯燥很貧乏。
最好的部位在一個老人那裡
處在一些塗料桶的下流影子裡
一個皮條客笑道,“晚上每樣事
都有它的安排,就看你能不能發現那是什麼。”
悖論和逆喻
這首詩只關心非常普通層面上的語言。
看著它正在跟你交談。你看著窗外
或裝作很煩躁。你有它但你沒有它。
你未覺察它,它未覺察你。你們互相沒有覺察。
這首詩很悲慘因為它想成為你的詩,卻不能。
什麼是普通層面?就是它和其他一些東西,
將它們的體系帶進了戲劇。戲劇?
唔,的確,沒錯。但我將戲劇視為
更外在的東西,一種人們想扮演的角色模式,
就像處在優美的分界處的這些八月的漫長日子
未加驗証。是沒有結論的。你還沒弄明白
它就煙消雲散,在打字機的喀嚓聲中逝去了。
它已又被演了一次。我覺得你存在著就是
為引誘我去做它,在你的層面上,然後你又不在那兒了
或者態度又不一樣了。而這首詩
已把我輕輕地放在你的身邊。這首詩就是你。
新現實主義
她說話暗含著沉醉。
也許我不會再讓那些玩笑
到頭來總是針對我而來。
拔掉所有窗戶的插銷
光進入她的妝奩時有某種
寧靜。酒從大海中提取__他們
不知道我們永遠都是很輕鬆地來的
我們雙腳離地因為你得到點香水太難
時可以到生活中去提取。
一只海豹出現了接著是其他的
在烈日下發黃
一只看門狗忠於職守而它們卻進來了
天色陰霾__冰代替了空氣
孩子們對以往音樂的認同
代替了笨蛋的嗥叫。
這就是她所能行及的地方__
一個帶綠地的酒肆。
在地平線上炸開
接著又是一次,然後一片混亂。海豚不願
上灘。成排的推土機
破土開挖地基,而她死於狂笑
因為好運僅讓你有一次逃脫了
在你門前的台階上她常常解釋道
若商人們早晨歸來將如何危險得像扒貨車。
而晚上一個人讓自己犯錯誤又有多快。
都是敲定了的。百日草
不可能看上去更好__紅的,黃的,藍的,
它們就是那樣。勿忘我和大麗花
起碼有六十個不同品種。
濃蔭升起
救護車軋著新一天的塵土
開來,太陽月亮星辰
冰山緩緩沉入
火山大海奔向遠方
炙熱的沙灘金黃,綠如綠樹。
惡化的形勢
他說,紛亂的色彩像暴風雨一樣
席卷了我,無可救藥。又像一個在宴席上
什麼也不吃的人,因為熱氣騰騰的菜肴
讓他挑花了眼。這只被隔離的手
代表著生活,隨心所欲四處漫遊,
走南闖北,它一直是一個與我
並肩趕路的陌生人。呵季節,
貨攤,酷熱,市郊鄉村晚會上
戴黑禮帽的遊醫,
你無意說出的名字千萬別說是我的,是我的?
總有一天我會告訴你一切是怎樣耗盡的。
我是為了你可同時我還得繼續
雲遊。每個人都渴望雲遊,
似乎如此。除此之外,還會有什麼?
是年賽嗎?的確,有那麼一些
專門為白制服和一種
諱莫如深的特殊語言存在的場合。酸橙
被適當切成幾塊。這我都知道
卻似乎無法不受它的影響,
每天如此,天天如此。我已厭倦了重復的創作
夜半苦讀,乘火車旅行
和羅曼蒂克。
一天當我外出時有人來訪
走時留下話“你從頭到腳都把
事情搞糟了。有幸的是,現在改正還
為時不晚,但是行動要快。
若方便盡早來見我,而且請
不要告訴任何人。你生活中的其他許多事全靠它了。”
當時我根本沒想這件事,過後
我一直在看那些老式樣的肩巾,摸摸
那些漿過的硬領,心裡想是否有辦法
使它們潔白如初。我妻子
還以為我在法國的Auslo-Auslo,就這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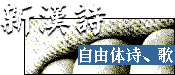
橄欖樹文學月刊◎
二零零零年九月期
編輯:馬蘭
編輯:馬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