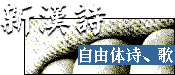1
在李白神秘主義的酒後夢遊和莎士比亞沒完沒了的獨白中
找不到魏爾侖,阿波裡奈爾和羅伯-格裡耶的小舌顫音。
一個在葡萄酒的長廊裡飛快遊動的短小尾音
彬彬有禮地為女士讓路,親吻著香氣四溢的纖纖玉手
或者飯後甜點。從那燕尾服的分岔裡,一個詞綴
滿懷心事地走出。(就是他調亂了所有的手表和掛鐘,
讓鬧鐘在午夜唱起激動的詠嘆調。)哦,時間
這錯誤的鏡像,把我塞進一輛陰差陽錯的班車,
又在一個陌生的小站中途停車,在半睡半醒間
我起身下車,茫然四顧,不小心碰響了
一串異國的音節,生鏽的耳朵要在打磨之後支起天線
才能聽懂這段優美流暢的法文:“歡迎大家來上法語課。”
2
昨天是巴黎的夕陽,是廣場上善解人意的白鴿。
昨天是葡萄酒,是浪漫華爾茲中旋轉的腳尖。
但今天是鬥爭,是菜市場上無休無止的討價還價。
哦,法蘭西!當她戴起花鏡,一絲不苟地撰寫回憶錄,
其中必定會有幾章,在每一頁上都用香水寫滿這三個字。
而那時她的血壓和心跳會頻頻向她發出警告,
不要過分激動,不要再沉湎於苦咖啡和開胃酒,
粗糙堅硬的現實要在回憶的乳汁裡泡得更久些,
否則會難以下嚥,會讓懷舊的胃思念起異國的奶酪。
這時她總會推開臨街的窗子,俯瞰照瀾院熙熙攘攘的人群。
哦,昨天是索爾邦大學裡聰穎好動的異國女生,
昨天是辦公室裡埋頭抄寫的三等文員,但今天
她就是我的命運女神,攥緊記分冊,站在我面前。
3
初學者充滿語法錯誤的一生,無法避免被紅筆刪改,
不及格的答卷即使再做上一遍,也無法擺脫鮮紅的分數
在記分冊上沖你呲牙微笑(它起初像一個斑點,
然後開始像癌細胞般迅速擴散)。
頭發花白的命運女神,她微弓的腰身承擔著
太多的偶然。也許一場不期而至的課堂測驗
會將你美夢中與佳人相會的豪華客輪撞個粉碎。
也許一個單詞的拼寫就會改變你的一生。
l還是r,思考這問題時你的神態會酷似
簡裝本莎士比亞全集中那張拙劣的哈姆雷特畫像。
一陣暈眩使你感到這間教室就像一間監獄,
而你正需要鄰座的紙條來扭轉乾坤。
4
與遺忘作對,就是將背過的單詞再背上一遍。
在記憶破舊的保險櫃再加上幾道封條。
而這死亡的微觀形式以千萬只螞蟻的細小腳爪
攻擊著理智形同虛設的銅牆鐵壁,
這些狡猾的盜賊夜夜光顧我的頭顱,
將塵封的記憶洗劫一空:一個舊友在消失,
一段時光被榨幹,只剩下幾次酒醉後的嘔吐物。
“而死亡也不能戰勝萬物”狄蘭﹒托馬斯天啟般的嗓音
在時間的侵蝕下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雜音。
是誰曾如此肯定,是誰在溫柔地告誡:
“至少要將課文背誦上三遍。”
5
她不相信辭典,就象不相信化妝品能將她臉上的雀斑
消滅幹淨。“智慧也有保質期”,尤其當它來自胡須花白的
教授們:他們衰老的肺不再會為氧氣偶爾興奮,或者頹唐。
能言善辯的人總會為自己找到理由,正如叫聲動聽的小鳥
遲早會找到買主。所以她的遲到一定與懶惰無關。
不過,她的發音倒總是比她的手表準確,
或許她在課前已把重音用螺絲釘牢牢固定,
並用砂紙磨光了那些拌腳的音節--它們
卻總是令我步履蹣跚,把歡快的小步舞
打成一套太極拳。哦,誦讀課文總是讓我如此恐懼,
就象害怕鄰座那張布滿雀斑的臉,害怕她會在夢中出現。
6
他和她的愛情懸掛在一根計時收費的電話線上,
雖然偶爾佔線,但多數時候暢通無阻。
他那隱身於八位數字後面的妻子,相貌平平,
卻精通於烹調的政治學和笑容的修辭術;
並懂得如何讓他安於現狀,又不時沉湎於幻想
--不得不承認,這方面她比一個政客做得更為出色。
在而立之年,這位志得意滿的小官僚從自己的生活中
抽身而出,懷揣婚姻的帳單混進祖國的心臟。
這裡,過去是皇家的園林,如今成為“知識的殿堂”,
但他的滿腔豪情無非是想撬下幾塊磚頭,
作為升遷的墊腳石。在喬裝打扮之後,
他溜進課堂,小心的藏身在一群年輕的信徒中間
--不得不承認,他們的虔誠與專注同樣不堪一擊:
當愛情的呼叫器打斷了法語的激情,
被那根細線扯動的不只是那個遠離家鄉的丈夫,
還有我們不斷張望的心和開始躁動的胃。
■〔寄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