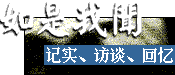對世界文化的眷念
--毛燄訪談
〈毛燄簡介:湖南湘潭人,1968年出生,1991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現任教於南京藝術學院。中國油畫學會理事。〉
吳晨駿(以下簡稱吳):先談談你本人的創作,你除了畫人物之外,還畫不畫風景、靜物?
毛燄(以下簡稱毛):這一階段沒有畫過。很多人從一種表面的層面上,比如從畫種啦、題材啦等方面來看待這個問題。實際上對一個畫家來說,各種選材的方式之間不存在區別。我畫的人物與傳統意義上的人物、肖像或人像有截然的不同,完全不是一碼事。在我的腦子裡面,從來就沒有想過我是在畫某一種東西,比如說我是在畫肖像、人像。我只畫我關注的東西,而不是說我必須要畫某種東西。有一種畫家很多,他們必須什麼都要畫一畫,這樣的想法對於我沒有任何意義。
吳: 在畫人物時,你是否選擇對象,比如選擇畫什麼樣的人物?
毛: 肯定是有選擇,但是我的選擇也不那麼明確。有時這一選擇很確定,有時也很隨意,沒有經過太多的設想。
吳: 你的畫上散布著一些大大小小的光斑,但我同時也感到畫面具有立體的效果,你是如何把這兩方面處理在同一張畫中的?
毛: 大概是靠我自己的一種情緒、一種靈感性的東西,把這兩者聯結起來,而不是靠一種技法。這個問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技法、語言那個層面上去,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還是我的認識或我的情緒。我現在不大可能考慮要用什麼技法來把某種東西結合在畫中。我的那些人物形像塑造出來便有非同一般的、或者至少有一種特殊的效果,這效果當然也包括技法、語言、結構等等。
吳: 你畫人物的衣服偏向於選擇什麼顏色?
毛: 原來偏向於棕褐色的衣服,近期我的作品幾乎都只注意臉部的發揮。相對於頭部、耳朵、面孔來講,衣服的重要性沒有以前那麼強了。臉部給人的感覺近乎一種呈現,一種實實在在的、一目了然的呈現。我也不是說臉部能帶來更多的東西,但它最起碼是一種呈現,與我們通常所見的一切不一樣的呈現。
吳: 你至今畫了多少張油畫?
毛: 沒有統計過,不算多。畫的時間很長,至少也有十五年了,現在回想當初剛開始時對油畫的認識,跟我現在相比,那是有天壤之別的,恍若隔世。
吳: 除了藝術的情感因素之外,你的繪畫語言與繪畫的理念、觀念有關嗎?哪一方面的觀念對你影響比較大一些?
毛: 有關系。但是現在“觀念”這個詞用得太多了,所有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會扯上“觀念”。實際上觀念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觀念對藝術家來說是具體的,是藝術家對藝術的基本認識和他對自我的一種判斷。觀念也許是他的願望,也許是他的情結或者他的立場,所以藝術作品裡面必須要有很明確的觀念因素。但是我個人的作品與純觀念性的作品那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有比較純粹的觀念藝術,方式上相對比較新穎比較前衛。現在我們經常講的觀念藝術,很大程度上與潮流有關系,與時尚有關系,與當代有關系,與波普文化有關系,相對於這個來講,我的藝術更多地是建立在對古典藝術的理解上,我作品中帶有一定靈敏度的東西,也可以說是我對某些古典藝術裡面某種我熱愛的東西的一種不自覺的流露,或者一種懷念。所以我作品更多的是與過去有關,而不是現在、今天。
吳: 剛才談到的那種觀念藝術,我感覺其藝術技巧是為其觀念服務的,相對於觀念,其技巧在繪畫上的作用就顯得很淡。對觀念藝術,你是如何看待的?
毛: 我對此是有自己的認識。觀念藝術中很多東西也是我很喜歡的,但是可能因為我很喜歡,反而讓我沒興趣。比如像那種裝置性的東西,都是一次性的,你喜歡就可以了。它的話說得很清楚,它想要的東西也很清楚,它的價值也很清楚,它觀念的指向也很清楚,這種東西也只能就是到“喜歡”這個地步而已,跟我沒有太多的關系,跟我現在畫的東西、作品,跟我的追求沒有關系。實際上一個藝術家個人化的創作,不可避免所要面臨的是他所能要的一切東西,眼前的、記憶中的、想象中的,但是每個人的能力有限,每個人對時間的把握也是有限的,藝術家最終的東西說來說去都很簡單,就是一種對時間的體驗。有的人生活在今天,有的人生活在明天,甚至有的人生活在過去,他們的處境、背景,他們的興趣和能力都完全不同。從這方面來講,藝術是沒有意義的。反過來有人會說只有藝術才是有意義的,這樣說也是天經地義的,因為一個藝術家面臨的東西太多了。
吳: 你怎麼看待在油畫這個領域中批評家的作用?
毛: 現在不存在油畫這個方面的批評家,因為現在的批評家似乎什麼都幹。我感覺批評家是在幹一些事情,但我不太明白他們到底想要幹什麼。我對這些一點沒興趣,他們在發出聲音,在說話,而他們在說什麼或者說得好不好,我沒有太多的感覺。那肯定是因為他們說得不那麼精彩,不那麼有特點,不那麼動聽,沒什麼誘惑力。他們老在說,老在說可能比說得好不好更重要。
吳: 我感到批評家似乎承擔了經紀人的某些作用,是這樣嗎?
毛: 有這樣的批評家,他們可能也是客觀上的藝術代理人。
吳: 在藝術界,純粹的經紀人有嗎?
毛: 當然也有。我也認識一些。但是大多數是以商業為目的的,那些真正有審美趣味的、有眼光的人極少。中國未來的批評家,包括藝術家、經紀人,他要體現一種綜合素質,比方說我們可以提到栗憲庭,他不僅僅是批評家,不僅僅是策劃人,更重要的方面是,他所具有的綜合的能力。
吳: 你是怎麼看待更年輕的畫家和他們在藝術方面的成績?
毛: 這樣的畫家其實還是有一定的數量的,做得比較好的畫家還是很多,包括我對我自己的認識--現在沒有任何問題,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經相當棒,相當成熟,相當好了,相當有價值或意義了,問題就是他十年以後怎麼樣,或者他是不是能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內,能夠很清楚地認識自己的那種優勢或者劣勢,這很重要。然後他還有能力去擁有一種自律心理,他有能力去發揮自己,因為確實有一些畫家在某一個階段特別棒,但很快地他就變了,這很奇怪,或者有一個很明顯的滑坡,那就很難講清楚他的腦子是怎麼想的。當然最終他肯定是與環境有關系,受潮流的影響,受現在這種文化的氣氛影響,所以最終真正能夠做得最好的只是少數。南京這樣的人也很多,這還是藝術家的素質問題。
吳: 在繪畫藝術中你最喜歡的是哪幾位畫家?
毛: 在古典藝術中,法國的德拉克洛瓦、德國的丟勒、西班牙的戈雅。這三人是我最喜歡的,他們三個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他們都是自己所屬的那個民族的藝術的最傑出的代表。
吳: 目前中國的油畫狀況是否很正常?
毛: 肯定是正常的。即使它再糟糕,它也是正常的。我現在對純粹的油畫界怎麼樣,根本就不關心。談到油畫界,可能更多地要談到學院派或者什麼很無聊的話題,我覺得這沒什麼意思。
吳: 在中國的藝術品市場,你覺得油畫的價值與市場最終呈現出來的價值是否很一致?
毛: 畫賣得好的、賣得價格高的、機會多的人,當然會認為這是一致的。賣得不好的、機會少的,當然會認為這不一致了。談到錢的問題,我喜歡杜尚的一句話,他說在錢的方面主要是看你能花多少錢,而不是看你能掙多少錢。你能花多少錢這很重要。嚴格來講,藝術家創作出的作品在社會中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也就是其價值也好、價格也好,是極其微小的。從社會的角度講它就是商品,產品,其價值或價格,是不可能讓藝術家過上真正豪華的生活。一個畫家可能很瀟洒、很洒脫、很揮霍、很奢侈,但是他絕對不是因為他富有了才揮霍,揮霍僅僅是他的一種需要。當然藝術家也不能太貧窮,貧窮會使畫家變得瘋狂、狹隘。
吳: 你是否了解中國藝術品拍賣的大體情況?
毛: 賣得好的都是老的或差的,像陳逸飛這樣的。一個差東西永遠賣得很好,一個老的東西,像古董一樣的東西,永遠有市場。相對來說,年輕藝術家能獲得的支持和經濟上的認可,就微乎其微了。
吳: 你經常去國外辦畫展,能否請你談談國外美術界的狀況,以及國外的藝術品市場主要靠什麼來左右?
毛: 那肯定與那個國家的整個文化需求和文化制度是相關的。實際上在國外,藝術品的商業化色彩遠遠高於我們現在所能理解的范疇。它其實非常商業,即使大師的東西也是商品。在美國、歐洲,那種商業色彩、商業運作的高度發達遠遠強於我們這裡。但是由於它良好和非常健全的商業機制的運轉,反而能夠把那種文化的東西帶動起來,移植到社會體制之中、社會的各個層面上。比如畫廊、文化中心、博物館、還有各種各樣的博覽會和展覽活動,甚至非常普遍的中產階級的家庭,都有非常強的收藏能力,所有文化的東西都是商品。在國外,你甚至可以在大公司的大樓的大堂裡看到大師的原作。也就是因為商業,反而讓美國社會的文化色彩非常強烈。而某種好的藝術品在我們生活的空間裡,幾乎是被當成垃圾,而在美國、歐洲,優秀的藝術品代表著精英文化,它們肯定會被留在很好的位置上,決不會被放在垃圾堆的一旁。
吳: 中國的文學界與國外的文學界交流時總是處在一種卑下的位置上,那麼在美術界,這種情況是怎樣的呢?
毛: 這肯定是差不多的。現在我們的文化對整個世界、對人類的文化的發展是不是有真正的推動,我們先不談這個。只是說,從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老百姓需要的是什麼東西,我們就能得出一個結論。在這個環境下所能產生的東西,它的作用與它的能量一定是極其有限度的。那麼這個能量的大小就決定了你是否具有文化影響力,我們不具備這個能力。就像我們在自己家裡無法開一個 PARTY ,就得到人家家裡去開 PARTY ,到一個更大的更豪華的人家去開 PARTY ,在那個地方 PARTY 才開得有點意思,才好玩。毫無疑問,中國的當代藝術可能跟文學的某些方面一樣,至少目前它在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仍然處於一種邊緣狀態。當然偶爾它也介入西文文化,有一個展示的機會,但這也是很有限的。
吳: 中國的藝術家在面對世界時應該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心理?
毛: 可能我們現在實際上的心理,恰恰與應該具有的心理相反,恰恰是很不融洽,是對立面的關系。因為按照我們傳統文化,中國人是具有超脫的、淡泊的心態,他的要求也是很有限的。現在恰恰相反。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我們文化所處的邊緣的狀態,其實也恰恰是因為我們這些人的那種普遍的心態而導致的,這種心態導致了我們在某些方面處於卑劣的地位。中國人現在整個的框架是非常不牢固的,它是一個沒有文化建樹的東西,再加上中國人的傳統的很超脫的、很通靈的東西已經在當代的中國文化當中體現的層面越來越小,體現的力量越來越微弱,那導致了中國人心態的普遍的微弱感。這是很可怕的。表面上來說,中國藝術的機會越來越多,另外一方面一些極其小的機會也會讓中國的藝術為之興奮一陣子,極小的機會也像一個強心針,也像一個興奮劑。實際上對西方文化中心的認同,以及對西方文化的介入的渴望,其實這種心態已經病入膏肓了。其實所有的人都有這種心態,但是這恰恰不是我們剛才說的應該具有的心態,大家都很願意把自己放在一個被選擇、被挑剔、被強奸、被利用、被獵奇的位置上面。
吳: 在國外從事藝術的華人與國內的藝術家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
毛: 我記得我去年在美國辦畫展,是幾位大陸去的藝術家和幾位在美國生活的華裔藝術家的聯展。當時有記者與我談到對中國當代藝術的認識問題,也談到你提的這個問題。其實在國外生活的很多華人藝術家和我們生活在國內的藝術家的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在作品中體現出的調調完全不同。我就說過其實他們與我們不太一樣,他們也有他們非常明顯的一致性的東西。因為他們生活在西方的那個環境下,應該說他們進入到西方語境當中的願望更強烈,但又由於他們的那種心態,導致他們的作品我認為是極不成功的,當然有個別的非常棒。文化的問題,還不簡單是日常生活的問題,它不斷地告訴你要以你特定的東西介入它的那個文化體系裡去,這在國內的藝術家看來好像很荒唐。說起來,我們這麼多年來積累起來的經驗、審美和所有的認識,都要介入到另外一種體系中,還希望能夠立足,這就好像雜種一樣的東西,是終就會搞出很多文化雜種出來,很奇怪的雜種,你沒見過的雜種。當然漸漸地大家彼此也在接受,這可能也是未來文化的一個趨勢,大家彼此都在相互接受。其實他們起的作用也相當大,不管怎麼講,他們在國外以他們的身份、以他們的能量,在各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在我看來我是無法想象,無法設想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
吳: 你本人目前參加了哪些比較重要的畫展?
毛: 對我個人來講,我參加的展覽對我都挺重要的,至於其他人我不清楚,我的確參加了很多展覽,而且還會參加很多展覽,但是重不重要我就不知道了。
吳: 國外的藝術節與國內的藝術節有什麼區別?
毛: 如果你是指西方的大型的展覽,藝術雙年展之類,那麼區別就大了。國內的這種所謂的國際藝術節,每個城市都在搞,辦得就像趕廟會似的,都是在翻跟鬥、舞獅子、說相聲、歌舞,純粹學術的藝術性的展覽幾乎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一出鬧哄哄的肥皂劇。因為中國的國情確定了這種藝術節是建立在中國的波普思想上面,中國的波普思想就是平民文化,讓平民的身心感到愉快。而國外的如威尼斯雙年展所體現出的精英文化,那肯定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一種所謂精英文化的國際節。
吳: 你目前的藝術所到達的程度,以及在藝術之河中所處的位置,你有沒有明確的認識?
毛: 如果這是建立在我個人的畫史上,我對自己的藝術當然是有認識的。但是如果放在我個人的畫史之外,出了家門,在大街上面,我就不知道了。尤其是放到歷史的長河中,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吳: 你對與你不同風格的作品持有什麼樣的態度?
毛: 這個方面經常是矛盾的。有時候我特別容易接受很多東西,這與我的愛好有關系。我的愛好和興趣比較廣,而且我從小從事繪畫導致我對繪畫有一種迷戀,從這一點來講,我對很多不同風格、不同意識的呈現都有某種興趣。但從相反的方面來講,越是這樣我就越對這一點有些疑惑,到現在為止我骨子裡面真正迷戀的東西,我發現越來越少。我越來越不可能獲得一種滿足,這導致我對繪畫的理解越來越簡單純粹,導致我的迷戀越來越沒有根據,這是矛盾的一種東西。最後這變成很不規律的心理反應,一下子清楚一下子又不清楚,一下子喜歡一下子又覺得很討厭。
吳: 你喜歡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是怎麼樣的?
毛: 每個人其實都有演戲的願望,我也不例外。我在生活中扮演各種角色,有時是這樣,有時是那樣,我喜歡豐富多變的生活。
(根據1999年8月31日下午3點30分至6點30分的採訪錄音整理)■〔寄自江蘇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