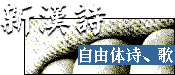老吳看著老張頭的孫子,小強,走過來,
在水泥桌前停下,欲言又止,伸手
把老張頭的老將輕輕拿起,反扣回中宮,
老吳便曉得,等了大半晌的這盤棋
已無對手,十幾年來這風雨不改的棋盤上的老交情,
也到此為止,已不可多得。
老吳一邊聽著小強低聲訴說他爺爺昨晚的事兒,
一邊看著地上一些早落的樹葉,被秋風倏倏刮走。
剛才,當小強把手伸向棋盤,老吳心裡還想,
這小子,該不是也想學他爺爺,要跟我大殺兩盤?
但他衣袖上的一小綹黑紗,讓老吳看到晴朗日子裡
突然出現的黑洞,被卷進去的人,再不會浮現。
小強到來之前,老吳的心情像天氣一樣晴朗。
他想,有什麼事情能比在秋清氣爽的公園裡
穩穩坐下來,靜靜等待一位老朋友慢慢露臉
來得更愜意,更自在,更圓滿?
他還想,要是碰上刮風下雨什麼的,
他們會轉移到湖對面的亭子裡去楚漢大戰,逐鹿中原,
今天天氣這麼好,老張頭肯定是
讓家裡什麼雜事兒給絆住了一會兒,
呆一兩支煙的工夫就會出現。
老吳於是點上一支煙,瞇起眼,對著棋盤
盤算起老張頭慣常的中宮炮開局,以及自己
上馬,拱卒,出車等一步步應對的手段。
小強走了之後,留下老吳一個人獨自面對
水泥桌上這盤棋。老吳替反扣著老將的老張頭
來了個中宮炮開局,跟自己廝殺了幾個回合。
然後,老吳停下來,輕輕點上一支煙。
透過陣陣煙霧,老吳繼續審視這盤棋,
這盤人人面前都擺著卻永遠下不嬴的棋。
在老吳周圍,秋天的太陽明亮、溫暖,
把滿地的落葉照得明晃晃地發嫩。
這些光,有的也照到老吳的心裡,
照見老吳日後得另想法子來打發的空白時間。
老吳輕輕吸著手上這支煙。
老吳眼看著自己手上這支煙也要燃到盡頭。
(1999年9月4-13日)■
二 流 詩 人
其實,二流詩人是一些不錯的詩人。問題是,他們不大承認自己。
作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說一說我們的問題。
是的,二流詩人是一個不能確認自己的群體。
一部分二流詩人自命為一流,
而大部分始終以為自己不過是三流。
前者才華橫溢;
後者,也才華橫溢,但少了一點點心理優勢。
二流詩人喜歡用一些大詩人的名字做題目來寫詩,
喜歡用他們的詞語,或者詩句,作為副題,或者題記。
這樣一來,二流詩人和一流詩人就顯得有點關系,
有點親密,但顯然也有點距離。
二流詩人基本上說不出太多的東西。
所以他們在“怎麼說”的技法上大作文章,渾水摸魚。
但問題是沒有魚!
所以,二流詩人應該被貶到魚塘裡去養魚。
到時候,養魚人家自然會大聲告訴他們:
我們都在岸上好好活著,你們又何必老泡在水裡?
二流詩人努力學習。他們學習外國詩人,
主要進口他們的形式,例如頭韻和十四行詩。
所以,朋友來訪時,二流詩人會拿起
一個精美的空酒瓶子斟酒給客人吃。
當人家問,酒呢?
他說,難道我的酒瓶子還不夠精美嗎?
所以,二流詩人也應該發配到酒廠去研究一下釀酒問題。
二流詩人的想像豐富。但不奇特。
二流詩人的比喻眾多。但不新穎。
二流詩人經常寫詩,但多數並不必要。
二流詩人寫詩,一般有拉長來寫的意思。
當然,二流詩人也偶有短作。
但短作也依然太長。因為本來可以寫得更短。
也有人寫得很短,比秦朝的古文還短,還艱難。
其實,短,是要平易近人和更加簡單。
二流詩人讓自己的聲音在事物的表面爬來爬去。
他們無法進入事物的內部,
更加無法抵達詩歌內部的憂傷。
二流詩人基本上停留在自戀、戀物和戀人這些熱情上面
反復打滾。你看,他們把戀歌唱得多麼動情,
但既不動人,也不動聽。
二流詩人的思想飛揚,情緒激昂。
他們經常在自己的夢幻中看見事物的本質。
其實,更重要的是讓自己平靜下來,
打開心靈的門窗,讓心靈的火球閃光。
也有人這樣做了,但發現自己的心靈不夠明亮,
就四出尋找標價更高的電燈泡。
二流詩人把詩寫出較大的情緒和聲響。
他們的詩足以媲美流行歌曲,但始終缺少一點旋律。
二流詩人慣於站在聽眾面前張著嘴巴高聲朗誦,
但卻不知道該怎樣輕輕走進人們的心中輕輕歌唱。
二流詩人的語言大多比較漂亮。
他們下過苦工夫鑽研語言,主要是鑽研口語。
口語好玩一點。
玩書面語的人,被他們認為是三流的行當。
二流詩人信奉“詩到語言為止”。
當時,這確實是一條不錯的宗旨。
但現在的問題,是一些“詩到語言而不止”的工作,
到底還要留待給誰?
二流詩人在自己的想像中積極鍛煉身體。
他們主要鍛煉腿部以下的筋肌。
他們準備隨時一腳就跳到一流詩人上面去,
好像一條躍過龍門的鯉魚。
然而,跳過龍門的魚,其實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始終認為,我們二流詩人
應該適當放棄一些多余的動作和心思,
就像放棄一些多余的情感和修辭。
我們二流詩人應該堅定不移,繼續用
心血和時間,喂養信念和一些簡單事物的真諦:
通過持久恆常的寫作和一點點皈依,
我們的臂膀,即便長不出豐滿的羽毛,
我們留下的詩行,這些青青的籐蔓,
也會緩緩向人們的心間伸延,然後糾纏。
(1999年8、12月)■
今天,我的皮鞋閃著光
這場關於競爭研究經費的研討會,實在悶。如果不是皮鞋閃著光,
這些講者的經驗,簡直一無所長。
昨天晚上,十一周年結婚紀念日,
看完電影回來,她又給她的新鞋上油,
把我的舊鞋也拿來刷了刷亮。
當時,我好像端著啤酒,在看網球,
她坐在電視機旁邊的地板上,
低著頭,專心致志,給她的鞋子上口紅,化妝。
看電影之前,我們走在大街上,
她抬起腳問了我兩次她的新鞋怎麼樣。
去年,她多次堅持我在學生面前要穿西裝。
今天,在這燈光昏暗的課堂,我看見我的皮鞋在閃光。
我覺得,她的新鞋不錯,她的人也很好。
當我這麼想,她在我的鞋面上,又微微發亮。
(1999年9月15日)■
旅遊船上,挪威
驗票之後,遊客們紛紛上船。他們紛紛上到船頂。
他們搬開疊放的膠椅子,找個有利位置坐下。
聽說,待一會兒,船的兩邊
會有一邊,能夠看見海獅和他們可愛的孩子。
當時的情形有一點亂。
不過,我們都是外國人,也就是
有教養的人,禮貌和距離基本保持一致。
起碼,沒有人拿椅子碰掉任何人的鼻子。
當然,幾把椅子在一些人的頭頂上搬來遞去,勢在難免。
當時的形勢,確實有一點點亂。
人們找到船頂兩邊的有利位置陸續坐好之後,
局面慢慢得到控制。
找不到上好位置的人,退而求其次,
坐在船頭和船尾,也相安無事。
船下一泓清冽綠水,
船邊兩面青山陡立,懸崖峭壁千尺,
山頂繞幾朵白雲,山頭堆幾攤積雪,
風景多麼優美!
山腰上還掛著一些大大小小的瀑布,
大的飛流直下,一瀉千裡,
小的牽絲掛線,滴滴淅淅。
它們的差異,好比人的內心、外貌和脾氣。
遊客們坐好之後,船長開船。
船頂上,人們的頭發首先被風吹起。
接著,他們的面頰和脖子也遭到了風寒的侵襲。
於是,有人系緊外衣的扣子。
有人從包裡掏出大衣,披在胸前擋風,
反起衣領蓋住嘴巴、鼻孔和脖子--那可是寒風們愛鑽的空隙。
有人披上頭巾,但一面頭巾被大風戲弄成幾面亂飄飄的三角旗。
後來,有一頂帽子吹落到甲板上,翻了兩翻,然後翻落到水裡。
人們首先聽到那位丟了帽子的東方女士的一聲驚喊,
然後看見她水裡的帽子。
驚喊的時候,她的嘴巴是圓形的,象一個小寫的o字。
驚喊之後,她一手掩著失態的嘴,一手掩著丟了帽子的頭,
還有一只手則連忙按下被陣風卷起的裙子。
她惶惑地瞧著七八米外的水面,望洋興嘆了一秒,也許半秒,
然後大夢初醒撲向欄桿,攤開所有的手指--
這時候,誰都看得出,她是多麼希望她的雙手能夠伸得再長一點!
不過,除了她身邊的幾個伙伴,
她對欄桿的普遍拍打,似乎並沒有引起遊客們太多的同情。
四周俏麗的風景,也沒有得到他們太多的欣賞。
他們在風中的堅持,已經有了一段時間。
時間越長,這樣的堅持就越顯得困難。
於是,漸漸有人往下層的船艙裡轉移。
然後,更多的人往船艙裡轉移。
首先是年老體弱的人,然後是帶小孩的人,
然後是不太留戀風景的人,然後是耐不住風寒的人。
船頂的人漸去漸少,樣子顯得孤立、有點無以為繼。
當然,也有人在風中繼續堅持。
他們象山頭溶剩的白雪,那麼珍貴、不可多得,
但了了無幾。
但也足以代表我們人類的某些品德。
下到船艙之後,人們發現
船艙裡的風景和船頂上的一樣好。
起碼,相差無幾。
雖然照相,相對來說,的確有一點兒問題。
但船艙裡空氣,比較友好。
何況,還有香噴噴的咖啡和暖氣
在一絲一絲升起。
後來,人們還發現,
當他們從船頂紛紛走回到船艙裡,
外面的太陽也一樣照到下面的船艙裡。
噢,外面的太陽也一樣照到下面的船艙裡!
這是多麼美好的事情,
多優美的哲理,
誰也不用再丟帽子。
這時,一位香港來的中國詩人,
已經坐在船艙裡面記下了一首旅遊詩的稿子,
用他古怪的東方文字。
(99年6月11日)■〔寄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