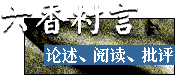◆白色聲音
今天,有許多曾經讓我們熟視無睹的名詞和事物正在離開世俗功利的詞言范
疇,同樣,有許多曾經欺騙和污辱了我們生命情感的名詞與事物正在漸離開它們
出賣自體靈魂得以憩身的場所。這些詞語正在遠離偽裝,正在走下裝幀秀美、字
體堂皇的書本。它們作為活生生的鮮花或是尖刺,作為滿足的欲愛或是張開的咀
唇,正在不經意的仿佛中來到我們的眼前。對於這些讓我們耳朵早已熟悉但很少
親身體觸的事物與名詞,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能及時找到它們重新回歸的故裡,它
們就有可能從我們的指間、唇下滑落得無影無蹤。
為了它們自身及我們的將來,我們必須成為這些走下偽裝書本聲音的氣管和
喉舌,我們必須讓這些聲音傳達得更為清晰與嘹亮。
《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是一本出人意料地在許多大城市圖書暢銷榜上長
時間名列前茅的純粹文論書籍。當劉小楓以一副極富使命感的學者面目出現在書
中不可回避的歷史的傾於政論的批判領域時,這一切告訴我們一些重要的新的變
化已經產生。這樣一本十分理智化的帶隨筆性質的評判書籍的出現與它普遍暢銷
的事實是十分耐人尋味的:一方面,我們可以機械地認為丹尼爾﹒貝爾在《資本
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談及的“藝術家造成觀眾”這一現代文化現象在我們周圍
正在演變成為現實,“敵對文化”以及它的體系(創造和吸收體系)正在我們這
個社會悄息而頑強地成長出現。(特別注釋:丹尼爾﹒貝爾是從與資產階級傳統
文化相對的角度來闡釋“敵對文化”的,他簡單地告訴我們,“敵對文化”的支
柱就是自由創作精神。在我們目前的具體情況下,將之稱為另類的“獨立文化”
也許更為符合我們特色的國情。)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具有遠見膽識
和智慧予以他無比勇氣的理論者正在婉約告曉我們許多不只專屬於他個人思想和
人生體驗所能包容的東西,這些東西在他的作品之中也更真實存在於此中之外的
大千世界。那裡,劉小楓客觀擔當了許多失落聲音的代言,他勇敢指示出的許多
東西,一旦被語言所揚起,它們便急速離開了最初現身的文本與印刷字符,走下
書本成為正在生長的語言、正在生長的交談。王家新1993年在倫敦寫作他著
名的《回答四十個問答》,當被問及“在你1989年以後的詩中,經常出現‘
詞’這個詞,最近你的長篇散文詩更叫做《詞語》,這是否包含了你對‘詞’的
發現的一種喜悅?”提這個問答時敏銳察覺到:從“詞”入手而不是從所謂抒情或
思考進入詩歌,導致的是對生命與存在的真正發現。這種回答語義是詩學的,從
深層角度而言我認為也是歷史批判的。正是站在這種詩學與歷史批判的交叉和邊
緣,我寫下“白色聲音”的標題和片斷。
歐陽江河在他那篇文獻價值遠遠大於詩學價值的《89後國內詩歌寫作》中
談到了今天的詩人與他們語言的背叛。如同我們不能錯誤地把“中年寫作”描述
和理解為一種時間序列一樣,當我談及“白色聲音”時,我站在自己的某首詩歌
之中,在那裡,我想通過詩的言說告訴自己和別人:在與“詩在”的對話中,白
色聲音並不是某種(某些)帶有異於詞類及“詩在”內含情感色彩的言說角度,
在這種(這些)言說角度中,人們別有用心或是想當然把許多情緒、政治、宗教
等等的主觀意象、是非評斷甚至生死存亡強加於清白的名詞和它標指的純粹事物
之上,人們在那種“名利場”中習慣於給名詞穿上不同尺寸、規格、樣式與顏色
的外套,給他們配上不同的工具和標簽,讓它們成為牛棚囚徒的影子、高貴理論
的光環、怒氣沖天打手的咆哮;成為溫順職員的諂笑、低賤匠人的汗珠、手舞足
蹈藝人的喃語;成為有些人瘋狂陰險的精神運動、變態敵對的犧牲祭品,對於這
所有的偏見和危險的誤識,“白色聲音”不僅是一把打碎和破解的鐵錘,它重要
的還是一種自身重建和延續的狀態--一種與其自身指向息息相關的寫作及文本
狀態。從世俗的角度而言,在歷史的真實逐漸得以顯露的今天,“白色聲音”正
是要走向人們期待已久的純白聲音響動的真理界面:
在一扇門打開所有的門,
從一座城市走遍其余的鄉村,
用一粒塵埃顯現宇宙無邊的面貌:
我現在的面貌,我們生命真實的面貌,
此時存在此地的面貌,
此地托負此生的面貌。
以今天重復往昔,
用一日見証未來。
(《白色宣言》)
愛爾蘭詩人西穆斯﹒希內在《歡樂或黑夜:W.B.葉芝與菲利浦拉金詩歌
的最終之物》一文中寫到:詩歌的重要性在於它提供的現實視域應具有改造之物,
他堅定告訴我們:“在大部分充滿創造力和啟示性的詩歌中動作著的是一種精神
能力,它可以籌劃一副關涉自身的嶄新藍圖,一種自我活力的嶄新疆域。”真實
的創作與指向的超脫,正是“白色聲音”的旨意所在。在這種旨意的觀照下,我
和我所言及的對象就真實存在於我的身邊--現在,它們也許正以我頭頂上一朵
雲的形式伴隨著我,抑或,以我手旁一陣風的氣態包圍擁擠著我,我相信因為它
們,我正變得大。而我當下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盡力捕捉到它輕快易變的身影,
與它們充分的交談和彼此聆聽,在這些交談和彼此聆聽中許多事物正在我們的四
周悄然變化,悄然產生。
身處過渡與轉型,作為一名真正而真實的詩人,除了等待,只有寫作。在這
種狀態中,我們親切詩歌,傾聽“白色聲音”在夜晚彼此之間因走動互相碰撞發
出的孤獨回聲,這些回響因孤獨而癒發高貴,因高貴而癒發崇高,它們在黑夜發
出的光芒就是我們稱之為“真理”的神聖之物:
我行走於我的筆下,行進在
一切需要的聲音間:
舌頭代表傷口說話,代表苦難
說一生的話。
我的咀唇是堅定的石塊,
詩句是升騰的火燄,聲音
撒落大地結出
水洗不掉的血斑。
終生生眠水的噩夢,整夜發出
閃光的疤痕。
◆記念碑
在我內心深處,一直想把我的長詩寫成具有“記念碑”性質的作品。這並非
由於我個人對自身抱有什麼強烈的功利思想(與此恰恰相反,我一直對所謂的“
投稿”與“發表”抱有一種與世俗追命逐利觀點水火不容的敵視和恐懼,這種近
似病態的擔驚受怕使我這麼多年以來一直盡力回避與抵抗著來自外界的各種色彩
斑斕的誘惑。)--而是基於這樣一種詩人面對的存在的現實與職責:我們的詩
與民眾都已經沉陷得太久,現在,對於詩界而言,一切太需要真正站在高處的聲
音了。把“記念碑”作為一種可能鞭策自己,也正是因為於此之上,一切才有可
能抵達高處才有可能成為高處的聲音。這種目標對於我確實太巨大了,我從開始
就徹底深知與清醒自己先天的不足與自我後天四處彌漫的落後。不僅如此,對於
“詩在”而言,一首真正的詩最後只歸屬於它自身隱秘的世界,在那裡,它自在
呼吸走動,自身歡笑悲傷。過多將某現在看來還屬於外界存顯的東西強附於詩的
本真之中,於詩於我,都將是一場無法彌補的災難。基於這些想法,我明白“記
念碑”對於我也許就像生命對於“詩在”一樣,一切不過是另一場遙遠的夢景,
而我們在本真面前永遠年青,永遠困惑。
我第一次從詩的角度知曉“記念碑”這一詞匯是在十多年前閱讀艾略特的《
荒原》時,翻譯出版這本書的那個出版社在封底作者簡介時把《荒原》稱為西方
現代詩史上的“記念碑”。但讓我被這三個字所震撼,是在其後某年的一個夜晚,
夜深人靜,我一個人躺在床上翻看一本詳細記述墨西哥畫家西蓋羅斯傳記的畫冊,
畫家一生都專心於創作自稱為具有“記念碑”意義的作品:露天自由展示的巨幅
壁畫,原始充滿生機的油彩,為民眾所熟識的人道遍布其間的思想,這一切藝術
的形式與畫家一生為真理而鬥爭,一生因鬥爭而飽受苦難與折磨的獨特人生經歷,
所有這一切深深打動了我。《新民主》、《資產階級肖像》、《人類進行曲》這
些色塊豪放、喻意深遠的巨型壁畫出現在墨西哥城的街口、廣場、博物館及教堂
內廳。在他的繪畫中,“記念碑”這個有著花崗石般堅強正直的質地的名詞告訴
了我們其自身的精髓:吶喊與真理。在這兩點的背後,其它的形態與顯現都已變
得其次而隨然。因為首先,相對於真理而言,美只是真理顯現的一種方式,換言
之,真理之言說,必是言說美之所在;而吶喊,不僅本身就是表達,它還是這種
表達的背叛與背叛表達的言說的存顯,是“白色聲音”存在化身的一面,它們和
真理一同從舊巢中掙紮而出,從陳腐的書本上彈跳而下,它們一起發出自身全新
的聲音,闡釋聲音全新的內涵。
從時間而言,期待“記念碑”性質的作品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並不只是囿於
當下處在一個世紀的結尾,新的未來即將破門而入。歲月對於我們,當下的苦難
仍在持續,面對這種連綿的痛苦,如果現在我們不會歌唱,將來我們必將喪失真
切觸摸歌聲的耳朵。這種未來的悲哀才是我們現在必須戰勝的悲劇,一個詩人與
他任何一首詩歌面對這種悲劇,馬上顯得渺小而無足輕重。托爾斯泰曾告之世人:
“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也抵不上一雙皮靴。”物質自有其低俗腐朽的一面,精神
也必有其永遠對立和輕鄙物欲的一面,但是,如果不能使我們的白晝完全叛逆黑
夜;不能使我們的笑容真正源於心靈、我們普通的尊嚴像山峰挺立,哪怕最為卑
下的人內心深處也有鳥羽扇動的音樂,如果這些沒有成為現實,津津樂道於某位
詩人與一首詩,又有什麼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人們胃中的黑暗、飢餓,我怎能
撇開這一切來談論我自己?
(王家新《帕斯捷爾納克》)
面具與油彩覆蓋我們面容和表情的過程太久,這種狀況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改
進,我們的藝術最終只能留下一堆陳舊的程式化臉譜。我現在的寫作沖動,我在
詞語與文本之間盡力捕捉的是與之完全相左的圖景,是一些能發出真正響動的言
詞。它們真切,因為它們來自我的靈魂與其它同類飢渴靈魂的撞擊;它們高亢,
因為它們代表了花朵與種子、森林和海洋的良知:
……
我,一位孤獨的遊吟詩人,
所以能夠歌唱,
是因為我瘦小的身軀每時顯影
這個世界廣闊的圖像:
在盆地建築高原通天的海拔;
在大陸挖掘海洋地核的深淵。
我,一位穿越世紀末黑暗的見証人,
所以必須歌唱,
是因為在歌唱的不是
唱歌的聲音,而是
唱歌的靈魂。
(《一九九九年,三幅速寫》)
對於我們漫長的生命而言,真切與真實在完全不同的層次也毫無二致,正義
與神聖所共處的意義正在於:神聖一旦可以言說,神性的傳達就由此出現,換而
言之,神聖之所在正在於神性的能在。詩與詩人的共在,就是詩歌與言說的共在。
追思與交談,批判與抒情,存在之詩如此存顯神奇,如此存顯美妙;凸顯與自解,
去蔽與言說,存在者如此存在真理,如此存在天堂。
1950年,西蓋羅斯在座無虛席、雅雀無聲的加拉加斯大學熱情演講時說:
我是說:除了我們的道路,別無它途。這決不意味著,我想侵犯別人的自我表現
自由。我不是要把墨西哥記念碑性繪畫的道路強加於人,而是要捍衛這條道路。
◆兩種可能
今天,中國詩界“白色聲音”言說的現實是建立在兩種可能的基礎之上:對
現實生活的重新認識及於此認識中在唾棄虛假的“政客政治”的同時堅定而真實
地使自身置於人本(人道)的政治領域之中;自身的人本(人道)言說成為使藝
術創作身分及形態成熟做最為現實與可靠的航標。這兩種可能勾勒出當下“詩歌
需要”在其得到最大滿足的地域所依據的條件或實現條件的一些依據。這些條件
與可能,既是詩學的,也是人學的,既是語言的,也是靈性的,既是理想的,也
是生活的。
首先,政治就是我們的現實,就是一切作家的現實--生活與創作的現實。
漠視這一點,與將“政客政治”重疊於藝術創作之上一樣危險。“政客政治”(
文革是其典型代表)及其顯現可能與“人本政治”是我們當下詩人們及需重新認
識辨別的兩類世界。從後者出發,我個人認為,今天,我們面對的應是在一個更
為理性與寬容范疇中的切入。從真正的人本政治的角度來審視歷史與創作歷史,
這是中國詩歌走向成熟化的諸種條件及可能中屬於特殊范疇的基本元素。在許多
作家(甚至普及於大眾)那裡,真正政治的本質已經受到歪曲,人本政治與藝術
的關系受到他們深刻而病態的敵視。這一完全歧誤的意識使他們的作品遠遠離開
了藝術最渴求的那些深厚的語言、營養和聲音,離開了能使他們真正發芽的土壤
和世界。這種遊離狀況至今仍在詩界彌漫與廣布。讓人感到可喜的是,有少數理
智與現實的詩人(評論者)已經認識到並強烈自責於自身的這一迷誤,他們正在
從思想、意識及創作中走出縹渺的象牙之塔、玻璃書齋,他們正在把自身的現實
寫作與寫作的現實結合起來,他們正在把自身長成一棵真正紮根於真實之中的樹
木。
另一方面,人本的政治是從未離開真實與實際而被虛幻的理論大家寫進僵硬
的教材、論著和文件的存在。作為一名當下的詩人,我們必須真實地表達這種真
實,自然地表達這種實際。真理總是簡單的,我們追求的東西如果在我們的眼前
變得癒來癒朦朧、變得更為陌生,歲月將証實我們道路的錯誤。“現代詩歌的個
性不是來自詩人的思想和態度,來自他的聲音;來自他聲音的韻律。”換言之,
我們筆下的言說就是我們思想最為可靠的導航,而韻律、節奏、意象這些看似歸
納於單純技巧范疇的手法,都是最為真切代表我們靈魂深處的可能。只有我們將
眼下認為專屬於藝術形式的那些技巧,完全溶進我們生活的歷程與現時之中,我
們才可能說自己真正開始面對歷史在進行寫作。
王家新在《中國現代詩歌自我建構諸問題》一文中,談及中國現代詩歌的“
無身分性”及在此困境、焦慮下中國現代詩歌如何建構自身的問題。這兩個問題
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尋覓到中國現代詩歌的身分,同時意味著中國現
代詩歌真正找到了與它曾經大面積引進、接受、“誤讀”和改寫的西方詩歌相對
的自身真實的存在,這種真實的存在就是它成功建構自身的因果,在那個特定時
空的地位之中,中國現代詩歌正在成熟建構自身,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所進行
的一切,正是中國詩歌建構自身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在那些真正從使命和職責
出發掌握自身言說命運的詩人手上,中國詩歌的身分正在變得清晰、變得完整,
在此圖景中出現的將是與自身傳統和西方詩史重建關系的詩歌的“少年中國”。
“白色聲音”在詩歌建構和身分確定過程中的作用是重大的。它使我們找到
自身真正言說的對象,找到自身言說對象的根系。朦朧詩中後期對早期朦朧詩的
背叛是毀滅性的,如果前期朦朧詩透露出無窮生命力的鮮明指向性在以後的寫作
實踐中得到發展與延續,我們今天的詩界決不會是如此的蒼白與淒戚,我們絕大
部分詩人決不會自我長期幻覺於意象、詞句可悲的語義學范疇內的結木似造句遊
戲。和我們自我的個人情感、意識、幻想相比,在我們生命存顯的世界有許多更
為廣大和意義深邃的東西--一朵花期待我們吐出陽光的咀唇;一塊石頭渴望我
們張開彩虹的眼睛;一個人--我們的同胞,期待我們串起所有人靈魂的身影。
這一切的需要就是“白色聲音”的需要,這一切誕生的土地就是“白色聲音”躍
起的地方。從此出發,當下詩歌已經與許多用詩難以包裹的重要而廣闊的歷史話
題聯系在一起,這些話題有時直接鋒利地從詩歌語言的皮囊中脫穎而出(例如天
安門詩抄及早期部分朦朧詩歌),明顯刺激了大眾麻木的眼睛和神經;但在更多
的時候,它們深刻埋伏進詩歌抒情的溫和形式之下,就像旺盛的魚群穿行在大海
平靜的海平面之下。
真正的“記念碑”能告訴我們的應正是這些平凡與普遍,正是在這些平凡與
普遍中需要捍衛的空氣和氧粒,正是在苦難中沉默的堅定行走者。認識這一切後,
做個詩人與寫詩的過程,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因為,如
果時間和真理不能擔當起平常、自然流程的角色,詩歌便已在它開始的地方變質,
詩人就已在成就之所腐爛。這也就是說:對於未來,我們不能把並不屬幹詩歌的
東西放置於詩的存在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從這種目的出發,我在一首詩的題記
中寫下:捍衛詩歌,就是捍衛自由。如果我們的詩人們當他們在雪白的稿子上,
在一個個如同處女侗體般誘人的方塊字中埋下他們身影與思想時仍不能深刻認識
到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們的寫作就還沒有進入代表將來日出的地域,換
而言之,對於當下,可怕的不是沉默,而是安靜。
起來同我一道生長吧,兄弟!
我站在這裡,我的名字
作為道路舖展在你們的身下。
作為道路我與你們站在這裡,
作為前進與你們走在一起:
一面召喚立體旗幟的風,
風噴射旗幟運動的擺。
我腳下大地吶喊的根莖,
就是你們大家歌唱的方向,
就是大家手和足
自由伸展的天空。
◆一次發言
就像八十年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詩人”一樣,現在,任何一位寫詩的
人,仿佛都可以成為一位評論家。在眾多的“對活”與“研討”的背後,事實的
真相是:關於目前中國詩界的狀況,還沒有一種或是幾種比較恰當的評論手段與
方法能全面而客觀的掌握當下詩界的動態,有許多領域及相關構成還沒有引起充
分注意,甚至少有評論涉足,沒有誰能從當下現存的分析中較為可靠清醒闡釋出
漢語詩歌在下一個世紀所切入的領地及在此領地實現的輝煌與苦難。這一方面是
說明當前的詩界仍處在一個深刻變化的階段之中,另一方面它告訴我們廣大詩人,
關於評論,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還遠遠不夠,我們中的絕大多數詩人還不具備一
種真正成熟的符合詩本質范疇的界想,他們中許多人甚至還不具有達到這種范疇
的能力與個人修養,毫不客氣地說:許多被認可為“詩人”的人,他們還根本算
不上是一位真正的詩人。
關於我們目前身處的時代與生存的境況,每一位存在的人都在認識的界面
上有著或深或淺的不滿與期望,幾乎可以共同的是,在現在:一個徘徊的流浪漢
與一名憂傷的詩人;一個拾垃圾為生的文盲與一位滿腹經綸的教授,他們都認同
我們今天的時代是一個在物欲中墮落的時代,物質無所不在的萬能功能所帶來的
深刻享樂感,把我們徹頭徹尾變成物的奴隸、異化的商品狂、焦慮的變態者,變
成無所事事的廢物、答非所問的文字遊戲者。就在前不久的某份報紙上,一位詩
人還激昂表達了上述觀點:“20世紀對於全世界從事寫作的人,是一個必須用
全部的生命才能承受和對話的世紀。苦難的徹底性,生存狀況改造的速度和廣闊
感,話語方式不斷革命和解構帶來的困惑,以及個人命運如此巨大的懸空和無法
把握,加之我們民族的特殊命運和文化歷史的嬗變,注定中國作家成為人類文學
群體中的最一孤獨者和堅韌者。”
1963年,薩特在布拉格的一次講話中面對東方華沙陣營對西方所謂沒落
資本主義的沒落資產階級的作家的沒落藝術的洪水洶湧般的集體攻擊,清醒而客
觀地否定了“墮落”這一概念,他說:“如果在東方,人們把弗洛依德、卡夫卡、
喬依斯視為資本主義墮落的作家,那麼,西方知識分子涉及人的全部文化就被剝
奪了發言權。”同樣,當今天我們的大眾與大部分詩人在用“墮落”這個帶有傳
染毒性的名詞打量我們身處的世界時,他們在意識中就先入為主地剝奪了我們這
個世界存在者在場的那種神聖性,剝奪了“詩在”在場所言的那種神聖性,換言
之,上帝、真理與詩,這一切從未離開過我們(所謂“重建詩歌精神”的論調是
可笑而荒謬的)。病態而自卑地把自身放置幹一種幻覺中混亂無措的景地,對於
一位終身不停言說的詩者,這是一種多麼自欺欺人的愚知。《聖經》上說:人心
有光,全身光明;中國佛教也認為人心所是即世界所是。一位詩人,如果不能從
普遍的世俗中聆聽感受到神聖所在的足音;不能從苦難中遠眺到精神金剛不摧的
光芒;不能在物欲的合理性背面看到“詩在”更為崇高、廣大的身影,他就還不
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詩者。如果現在我們一味媚俗強調外界的“墮落”,我們就
是在壓抑自我內心對神性的潛在渴求,我們就是在和罪惡一同虛構存在面對的“
偽”所在的虛幻真實性。
中國詩歌的現代化是每一位中國詩人內心最為關切的課題。因為,這從根
本的意義上講,意味著詩人與他們身處時代的現代性。在這種現代化的進程中,
“民族性”是一個誰也無法超越的尖銳問題,我們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圍之中,
在用一種特定的語言言語著身處的特定的世界,這種神奇的偶然性毫無知覺地被
包裹於“民族性”的必然之中,任何意義上的“先鋒”與“實驗”都必須認識到
此:在我們這樣一個尊崇傳統的國度中,在這樣一種深厚文化背景及沉澱之下,
詩歌的今天不可能不面對自己漫長的過去,在未來的文本范疇與現時寫作中它不
可能不時刻體現自己作為東方詩歌的與往昔古典主義一脈相承的內涵與詩化精神。
但這種民族性與現代融合的詩歌,對於當下的詩人而言,不可否認仍是一個“兩
難”的命題,一方面,古典主義的精神在大多數詩人的認識中就簡單等同於“古
體詩”,而現在,仿佛只有老者才對此寫作津津樂道,對於大多數青年詩人而言,
古典主義是隨唐詩宋詞一同隕落的巨星,對於當下寫作毫無意義;另一方面,從
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來看,“白話新詩”已經越來越遠離自己新文化運動初期誕
生時的初旨,它也癒來癒成為與“舊體詩”所代表的古典詩學完全矛盾和敵對的
文學工具,成為正在與我們談及的“民族性”產生裂縫隔閡的另類思想背景下存
在的世界及言語大地。簡而言之,新詩正在走向背叛。我想,作為詩人最為重要
的立場是:在此過程中,不僅要勇敢死亡,而且,更要努力復活。
成熟的中國現代詩歌必然與自我的“民族性”有著一體的流通性,而中國詩
歌的“民族性”的新生必須建構在它嶄新的現代性之上。
對於整體性的中國詩人與詩歌而言,今天我們的一切並不成熟,也不強大。
清醒認識到這一點,可以使我們更好面對那些打著“詩歌”旗號在詩界漂浮著的
與詩之本在並無關聯的事物。這些事物以皇堂的官僚面目出現在公開的報刊之中,
用“大獎”、“桂冠詩人”、“詩歌晚會”等功利的虛名掩蓋自身物欲貪婪的手
爪;這些事物以商品的金錢萬能法則出現在協會組織之中,它們的存在使“貨幣
萬能”成為當下詩歌語法生存的第一條寫作原則。正是這些東西玷污了詩,正是
這些東西玷污了詩人,正是這些東西玷污了詩界。詩人們,如果現在我們就為了
這些東西而挖空心思、急功近利;為了這些東西拋棄做人的原則、寫作的真理,
我們就是在拒絕那些真正能幫助我們這群漫流者於黑夜達到目的的召喚,我們就
是在放棄自我真正回歸家園的路途。
對於今天許多中國詩人而言,學會在新條件下如何做人和生活,比他們學會
寫詩更為重要。一個人性低劣修養粗俗的人,我不相信他能傾聽到純潔的神性,
我不相信他能成為一名真正的詩人。
即使我們現在身處虛幻之中,虛幻對於我們也是漫長的。只有用同樣漫長
的時光與寫作,我們才能最終戰勝虛幻,就像我們在用這一切去戰勝苦難和生命
的空洞一樣。
詩的過程,就是“去偽存真”的過程,就是本真與“詩在”漸漸去蔽的過程,
就是詩的形態與人性走向圓全的過程,就是生命戰勝的過程。
(1999.3,選自《焦虎三詩學文論集》)■〔寄自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