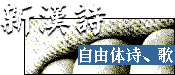第一天
葉落到要去的路上
在一個夢的時間
周圍像朋友一樣熟悉
我們,卻隔得像放牧一樣遙遠
你的眼睛在白天散光
像服過藥一樣
我,是不是太粗暴了?
“再野蠻些
好讓我意識到自己是女人!”
走出樹林的時候
我們已經成為情人了
第二天
山在我們面前,野蠻而安詳
有著肥胖人才有的安詳
陌生閃了一個回合
你不好意思地把手抽回
又覺得有點庸俗
就打了我一個耳光
“要是停電就好了
動物園的野獸就會沖破牢籠
百萬莊就會被洪水沖走!”
第三天
太陽像兒子一樣圓滿
我們坐在一起,由你孕育它
我用發綠的手指撥開蘆葦
一道閃著金光的流水
像月經來潮
我忍不住講起下流的小故事
被豎起耳朵的行人開心地攝去
到了燈火昏黃的滿足的時刻
編好謊話
拔幹褲腿上的野草刺
再來一下
就飛跑去見衰老的爹娘……
第四天
你沒有來,而我
得跟他們點頭
跟他們說話
還得跟他們笑
不,我拒絕
這些抹在面包上的愚蠢
這些嗅東西的鼻子看貨物的眼睛
這些活得久久的爺爺
我再也不能托著盤子過禮拜天了
我需要遺忘
遺忘!車夫的腳氣,無賴的口水
遺忘!大言不慚的胡子,沒有罪過的人民
你沒有來,而我聽到你的聲音:
“我們畫的人從來不穿衣服
我們畫的樹都長著眼睛
我們看到了自由,像一頭水牛
我們看到了理想,像一個早晨
我們全體都會被寫成傳說
我們的腿像槍一樣長
我們紅紅的雙手,可以穩穩地捉住太陽
從我身上學會了一切
你,去征服世界吧!”
第五天
看到那根灰色的煙囪了吧
就像我們浮淺的愛情一樣
從那個沒有帶來快樂的窗口
我看到殘廢在河岸上捕捉蝴蝶
當我自私地溫習孤獨
你的牙齒也不再閃光
我們都當了真
我們就真的分了手
第六天
你說的都是真的?
真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這麼想?
從開始。
你真的不愛了?
真的。所以可以結婚了。
你還在愛。
不愛。結婚。
你只愛自己。
(想著別的事情,我點了點頭)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一直都在欺騙你。
(街上的人全都看到了
一個頭戴鴨舌帽的家伙
正在欺侮一個姑娘)
第七天
重畫了一個信仰,我們走進了星期天
走過工廠的大門
走過農民的土地
走過警察的崗亭
面對著打著旗子經過的隊伍
我們是寫在一起的示威標語
我們在爭論:世界上誰最混賬
第一名:詩人
第二名:女人
結果令人滿意
不錯,我們是混賬的兒女
面對著沒有太陽升起的東方
我們做起了早操--
(1972)■
我寫青春淪落的詩
(寫不貞的詩)
寫在窄長的房間中
被詩人奸污
被咖啡館辭退街頭的詩
我那冷漠的
再無怨恨的詩
(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我那沒有人讀的詩
正如一個故事的歷史
我那失去驕傲
失去愛情的
(我那貴族的詩)
她,終會被農民娶走
她,就是我荒廢的時日……
(1973年)■
當他敞開遍身朝向大海的窗戶
向一萬把鋼刀碰響的聲音投去
一個故事中有他全部的過去
當所有的舌頭都向這個聲音伸去
並且銜回了碰響這個聲音的一萬把鋼刀
所有的日子都擠進一個日子
因此,每一年都多了一天
最後一年就翻倒在大橡樹下
他的記憶來自一處牛欄,上空有一柱不散的煙
一些著火的兒童正拉著手圍著廚刀歌唱
火燄在未熄滅之前
一直都在樹上滾動燃燒
火燄,竟殘害了他的肺
而他的眼睛是兩座敵對城市的節日
鼻孔是兩只巨大的煙鬥仰望天空
女人,在用愛情向他的臉瘋狂射擊
使他的嘴唇留有一個空隙
一刻,一列與死亡對開的列車將要通過
使他伸直的雙臂間留有一個早晨
正把太陽的頭按下去
一管無聲手槍宣布了這個早晨的來臨
一個比空盒子扣在地上還要冷淡的早晨
一陣樹林內折斷樹枝的聲響
一根折斷的鐘錘就擱在葬禮街卸下的舊門板上
一個故事中有他全部的過去
死亡,已成為一次多余的心跳
當星星向尋找毒蛇毒液的大地飛速降臨
時間,也在鐘表的滴嗒聲外腐爛
耗子,在銅棺的鏽斑上換牙
菌類,在腐敗的地衣上跺著腳
蟋蟀的兒子在他身上長久地做針線
還有邪惡,在一面鼓上撕扯他的臉
他的體內已全部都是死亡的榮耀
全部都是,一個故事中有他全部的過去
一個故事中有他全部的過去
一個瘦長的男子正坐在截下的樹墩上休息
第一次太陽這樣近地閱讀他的雙眼
更近地太陽坐到他的膝上
太陽在他的指尖冒煙
每夜我都手拿望遠鏡向那裡瞄準
直至太陽熄滅的一刻
一個樹墩在他坐過的地方休息
比五月的白菜畦還要寂靜
他趕的馬在清晨走過
死亡,已碎成一堆純粹的玻璃
太陽已變成一個滾動在送葬人回家路上的雷
而孩子細嫩的腳丫正走上常綠的橄欖枝
而我的頭腫大著,像千萬只馬蹄在擊鼓
與粗大的彎刀相比,死亡只是一粒沙子
所以一個故事中有他全部的過去
所以一千年也扭過臉來--看
(1983年)■
從死亡的方向看總會看到
一生不應見到的人
總會隨便地埋到一個地點
隨便嗅嗅,就把自己埋在那裡
埋在讓他們恨的地點
他們把鏟中的土倒在你臉上
要謝謝他們。再謝一次
你的眼睛就再也看不到敵人
就會從死亡的方向傳來
他們陷入敵意時的叫喊
你卻再也聽不見
那完全是痛苦的叫喊!
(1983年)■
歌聲是歌聲伐光了白樺林
寂靜就像大雪急下
每一棵白樺樹記得我的歌聲
我聽到了使世界安息的歌聲
是我要求它安息
全身披滿大雪的奇裝
是我站在寂靜的中心
就像大雪停住一樣寂靜
就連這只梨內也是一片寂靜
是我的歌聲曾使滿天的星星無光
我也再不會是樹林上空的一片星光
(1984年)■
雪鍬鏟平了冬天的額頭
樹木
我聽到你嘹亮的聲音
我聽到滴水聲,一陣化雪的激動:
太陽的光芒像出爐的鋼水倒進田野
它的光線從巨鳥展開雙翼的方向投來
巨蟒,在卵石堆上摔打肉體
窗框,像酗酒大兵的嗓子在燃燒
我聽到大海在鐵皮屋頂上的喧囂
啊,寂靜
我在忘記你雪白的屋頂
從一陣散雪的風中,我曾得到過一陣疼痛
當田野強烈地肯定著愛情
我推拒春天的喊聲
淹沒在栗子滾下坡的巨流中
我怕我的心啊
我在喊:我怕我的心啊
會由於快樂,而變得無用!
(1985年)■
四只小白老鼠是我的床腳
像一只籃子我步入夜空
穿著冰鞋我在天上走
那麼透明,響亮
冬夜的天空
比聚斂廢鋼鐵的空場還要空曠
雪花,就像喝醉酒的蛾子
斑斑點點的村莊
是些埋在雪裡的酒桶
“誰來摟我的脖子啊!”
我聽到馬
邊走邊嘀咕
“喀嚓喀嚓”巨大的剪刀開始工作
從一個大窟窿中,星星們全都起身
在馬眼中濺起了波濤
噢,我的心情是那樣好
就像順著巨鯨光滑的脊背撫摸下去
我在尋找我住的城市
我在尋找我的愛人
踏在自行車蹬上那兩只焦急的香蕉
讓木材
留在鋸木場做它的噩夢去吧
讓月亮留在鐵青的戈壁上
磨它的鐮刀去吧
不一定是從東方
我看到太陽是一串珍珠
太陽是一串珍珠,在連續上升……
(1985年)■
憂鬱的船經過我的雙眼
從馬眼中我望到整個大海
一種危險吸引著我--我信
分開海浪,你會從海底一路走來
陸上,閑著船無用的影子,天上
太陽燒紅最後一只銅盤
然後,怎樣地,從天空望到大海
--一種眩暈的感覺
好像月亮巨大的臀部在窗口滾動
除我無人相信
如果我是別人
會發現我正是盲人:
當一個城市像一位作家那樣
把愛好冒險的頭顱放到鋼軌上
鋼軌一直延伸到天際
像你--正在路程上
迎著朝陽抖動一件小衣裳
光線迷了你的雙眼呵,無人相信
我,是你的記憶
我是你的愛人
在一個壞天氣中我在用力摔打桌椅
大海傾斜,海水進入貝殼的一刻
我不信。我汲滿淚水的眼睛無人相信
就像傾斜的天空,你在走來
總是在向我走來
整個大海隨你移動
噢,我再沒見過,再也沒有見過
沒有大海之前的國土……
(1985年)■
北方的海,巨型玻璃混在冰中洶湧
一種寂寞,海獸發現大陸之前的寂寞
土地呵,可曾知道取走天空意味著什麼
在運送猛虎過海的夜晚
一只老虎的影子從我臉上經過
--噢,我吐露我的生活
而我的生命沒有任何激動。沒有
我的生命沒有人與人交換血液的激動
如我不能佔有一種記憶--比風還要強大
我會說:這大海也越來越舊了
如我不能依靠聽力--那消滅聲音的東西
如我不能研究笑聲
--那期待著從大海歸來的東西
我會說:靠同我身體同樣渺小的比例
我無法激動
但是天以外的什麼引得我的注意:
石頭下蛋,現實的影子移動
在豎起來的海底,大海日夜奔流
--初次呵,我有了喜悅
這些都是我不曾見過的
綢子般的河面,河流是一座座橋樑
綢子抖動河面,河流在天上疾滾
一切物象讓我感動
並且奇怪喜悅,在我心中有了陌生的作用
在這並不比平時更多地擁有時間的時刻
我聽到蚌,在相愛時刻
張開雙殼的聲響
多情人流淚的時刻--我注意到
風暴掀起大地的四角
大地有著被狼吃掉最後一個孩子後的寂靜
但是從一只高高升起的大籃子中
我看到所有愛過我的人們
是這樣緊緊地緊緊地緊緊地--摟在一起……
(1984年)■
我們反復說過的話它們聽不見
它們彼此看也不看
表面上看也不看
根
卻在泥土中互相尋找
找到了就扭殺
我們中間有人把
這種行為稱為:
愛
剛從樹叢中爬起來的戀人
也在想這件事兒
他們管它叫:
做愛。
(1985年)■
北歐讀書的漆黑的白晝
巨冰打掃茫茫大海
心中裝滿冬天的風景
你需要忍受的記憶,是這樣強大。
傾聽大雪在屋頂莊嚴的漫步
多少代人的耕耘在傍晚結束
空洞的日光與燈內的寂靜交換
這夜,人們同情死亡而嘲弄哭聲:
思想,是那弱的
思想者,是那更弱的
整齊的音節在覆雪的曠野如履帶輾過
十二只笨鳥,被震昏在地
一個世紀的蠢人議論受到的驚嚇:
一張紙外留下了田野的圖畫。
披著舊衣從林內走出,用
打壞的田野捂住羞恨的臉
你,一個村莊裡的國王
獨自向鬱悶索要話語
向你的回答索要。
(1986年)■
當我從茅坑高高的童年的廁所往下看
我姨夫正與一頭公牛對視
在他們共同使用的目光中
我認為有一個目的:
讓處於陰影中的一切光線都無處躲藏!
當一個飛翔的足球場經過學校上方
一種解散現實的可能性
放大了我姨夫的雙眼
可以一直望到凍在北極上空的太陽
而我姨夫要用鑷子--把它夾回歷史
為此我相信天空是可以移動的
我姨夫常從那裡歸來
邁著設計者走出他的設計的步伐
我就更信:我姨夫要用開門聲
關閉自己--用一種倒敘的方法
我姨夫要修理時鐘
似在事先已把預感吸足
他所要糾正的那個錯誤
已被錯過的時間完成:
我們全體都因此淪為被解放者!
至今那悶在雲朵中的煙草味兒仍在嗆我
循著有軌電車軌跡消失的方向
我看到一塊麥地長出我姨夫的胡子
我姨夫早已系著紅領巾
一直跑出了地球--
(1988年)■
十一月入夜的城市
惟有阿姆斯特丹的河流
突然
我家樹上的桔子
在秋風中晃動
我關上窗戶,也沒有用
河流倒流,也沒有用
那鑲滿珍珠的太陽,升起來了
也沒有用
鴿群像鐵屑散落
沒有男孩子的街道突然顯得空闊
秋雨過後
那爬滿蝸牛的屋頂
--我的祖國
從阿姆斯特丹的河上,緩緩駛過……
(1989)■
他們在天空深處喝啤酒時,我們才接吻
他們歌唱時,我們熄燈
我們入睡時,他們用鍍銀的腳指甲
走進我們的夢,我們等待夢醒時
他們早已組成了河流
在沒有時間的睡眠裡
他們刮臉,我們就聽到提琴聲
他們劃槳,地球就停轉
他們不劃,他們不劃
我們就沒有醒來的可能
在沒有睡眠的時間裡
他們向我們招手,我們向孩子招手
孩子們向孩子們招手時
星星們從一所遙遠的旅館中醒來了
一切會痛苦的都醒來了
他們喝過的啤酒,早已流回大海
那些在海面上行走的孩子
全都受到他們的祝福:流動
流動,也只是河流的屈從
用偷偷流出的眼淚,我們組成了河流……
(1989)■
當教堂的尖頂與城市的煙囪沉下地平線後
英格蘭的天空,比情人的低語聲還要陰暗
兩個盲人手風琴演奏者,垂首走過
沒有農夫,便不會有晚禱
沒有墓碑,便不會有朗誦者
兩行新栽的蘋果樹,刺痛我的心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蘭
使我到達我被失去的地點
記憶,但不再留下犁溝
恥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個英格蘭,沒有一個女人不會親嘴
整個英格蘭,容不下我的驕傲
從指甲縫中隱藏的泥土,我
認出我的祖國--母親
已被打進一個小包裹,遠遠寄走……
(1989-1990)■
我們過海,而那條該死的河
該往何處流?
我們回頭,而我們身後
沒有任何後來的生命
沒有任何生命
值得一再地復活?
船上的人,全都木然站立
親人們,在遙遠的水下呼吸
鐘聲,持續地響著
越是持久,便越是沒有信心!
對岸的樹像性交中的人
代替海星、海貝和海葵
海灘上散落著針頭、藥棉
和陰毛--我們望到了彼岸?
所以我們回頭,像果實回頭
而我們身後--一個墓碑
插進了中學的操場
惟有,惟有在海邊哭孩子的婦人
懂得這個冬天有多麼的漫長:
沒有死人,河便不會有它的盡頭……
(1990)■
我始終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裡
在風聲與鐘聲中我等待那道光
在直到中午才醒來的那個早晨
最後的樹葉做夢般地懸著
大量的樹葉進入了冬天
落葉從四面把樹圍攏
樹,從傾斜的城市邊緣集中了四季的風--
誰讓風一直被誤解為迷失的中心
誰讓我堅持傾聽樹重新擋住風的聲音
為迫使風再度成為收獲時節被迫張開的五指
風的陰影從死人手上長出了新葉
指甲被拔出來了,被手。被手中的工具
攥緊,一種酷似人而又被人所唾棄的
像人的陰影,被人走過
是它,驅散了死人臉上最後那道光
卻把砍進樹林的光,磨得越來越亮!
逆著春天的光我走進天亮之前的光裡
我認出了那恨我並記住我的惟一的一棵樹
在樹下,在那棵蘋果樹下
我記憶中的桌子綠了
骨頭被翅膀驚醒的五月的光華,向我展開了
我回頭,背上長滿青草
我醒著,而天空已經移動
寫在臉上的死亡進入了字
被習慣於死亡的星辰所照耀
死亡,射進了光
使孤獨的教堂成為測量星光的最後一根柱子
使漏掉的,被剩下。
(1991)■
十一月的麥地裡我讀著我父親
我讀著他的頭發
他領帶的顏色,他的褲線
還有他的蹄子,被鞋帶絆著
一邊溜著冰,一邊拉著小提琴
陰囊緊縮,頸子因過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讀到我父親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馬
我讀到我父親曾經短暫地離開過馬群
一棵小樹上掛著他的外衣
還有他的襪子,還有隱現的馬群中
那些蒼白的屁股,像剝去肉的
牡蠣殼內盛放的女人洗身的肥皂
我讀到我父親頭油的氣味
他身上的煙草味
還有他的結核,照亮了一匹馬的左肺
我讀到一個男孩子的疑問
從一片金色的玉米地裡升起
我讀到在我懂事的年齡
晾曬谷粒的紅房屋頂開始下雨
種麥季節的犁下拖著四條死馬的腿
馬皮像撐開的傘,還有散於四處的馬牙
我讀到一張張被時間帶走的臉
我讀到我父親的歷史在地下靜靜腐爛
我父親身上的蝗虫,正獨自存在下去
像一個白發理發師摟抱著一株衰老的柿子樹
我讀到我父親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馬腹中去
當我就要變成倫敦霧中的一條石凳
當我的目光越過在銀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1991)■〔寄自香港。作者現居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