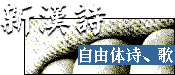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田曉菲﹒
回 鄉
我又一次來到這裡--我曾在此等待過許久的地方:
破舊的家具,就象衰弱而忠實的老狗 ;
印花窗帘依然謙卑地垂落,
好像被重復的厄運征服了的頭。
那些童年的日子
曾經在這裡被無限拉長,
仿佛廉價肥皂清洗之後變形的毛衣,
又仿佛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每個父親或母親探頭俯視,
都只能望見水的表層上
他們自己的面龐。
在那些長蛇一樣蜿蜒的白晝,
靜寂的樹蔭藏著無數私語,
使孩子的目光一次次迷失。
在那些總是熬不到盡頭的黑夜,
每個不可理喻也不可克服的恐懼
都是一顆閃耀白光的冷硬星辰,
缺乏言語表述它自身。
還有那只永遠上鎖的書櫃,
現在頹然放棄了自衛,顯示它的貧乏 。
好像一個被歲月的暴徒劫奪走神秘魅 力的
初戀情人。
還有那個黑暗的壁櫥
曾經收容我,為了得到呼叫和尋找。
在那裡我養成了等待的習慣,直到今 天。
隨你說這是固執,或是愚蠢--
但也許,也許,也許不知何時,
就象那只壁櫥被驟然開啟,
白色的光潮洶湧而入,
裡面所有的物件都被照亮:
拋棄幽暗的形狀、危機四伏的陰影,
呈現我等待已久的,最終的真實。
■
三月十一日,紐約,森林小丘
雨水使一切散發荒涼的氣息。無人的小花園裡,一條搭在繩上的褲 子
模仿著腿的樣子搖盪著,給過往的鴿 子
展示風的形狀。倒在濕綠草根上的
是一只黑鐵烤肉架,一柄褪色的陽傘 。
從蠟筆畫裡走出的孩子,粉色的外套
蹣跚地消逝了。鬆鼠驚疑地
凝神不動,小心地捧著
被風吹落的午餐。
路邊,一輛汽車的名字
叫做“非洲草原”。它固執地停泊著 ,
然而它載我去了那裡。我突然意識到 ,
我們同時存在,同時呼吸著--
我,和非洲大草原上那頭威嚴的獅子 。
如果沒有我,它的威嚴不會顯現
在文字裡--它不自知也不需要的
一種品質。它矯健,雄壯,放任地愛 和屠戮,
這兩者對於它乃是一體,是生命的顯 示。
它低聲的咆哮穿透非洲草原最濃厚的 夜色,
使我在都市無人的街道上顫栗。
鬆鼠和鴿子都不見了,我只看到自己 ,看到
洗衣繩上一條無人收容的褲子,荒蕪 而孤獨地
搖盪著,絕望於腿的形狀,風的漠然 。
■
酒吧間裡的一點聯想
是的,死亡是一種遺棄。但死亡首先
是一種距離。
坐在一家暗淡的酒吧間裡,
我遠遠地凝視著
好象手中的酒杯一樣
旋轉不停的吧女--
她的體溫睡著了,
她的嘴唇紅腫,
殘留著
被時間打過耳光的痕跡。
死亡是一個被時間遺棄的空間。
充滿古典棄婦的荒蕪與哀怨。
在這個靜寂,純粹,不可測度的絕對 空間裡,
我們的存在不過是
水晶酒杯並撞時
發出的清澈回聲而已。
是什麼樣的手握持著杯子?
是什麼激烈的事件
使酒漿潑洒?
坐在一家暗淡的酒吧間裡,
我矜持地幻想
天上的神需要用這種回聲
娛樂自己--
也許,他們正在慶祝一場聖戰;
也許,為了紀念一顆星辰的逃亡輾轉 ,
他們在冷冷燃燒的白色火燄之間,
擺下了一桌沒有主人的宴席。
■
女 王 之 死
我夢見女王死了。小白楊樹的儀仗隊
歡迎每個吊喪者。
山脈在風中舞蹈,好象一群河馬,
一群在海浪上奔騰的泡沫。
甲虫在玻璃般柔脆的陽光中做愛,
生命的呻吟使每束光線顫抖不停。
我夢見女王死了。這只是星期三,
(為什麼是星期三?一個沒有面具、
也沒有面孔的日子,與它擦身而過,
已經不再相識了。)眾幡飛舞,
如潔白的鶴群扶搖升起,
渴望著天空。
女王的死
隨著子夜的鐘聲回響。
--夢以外的事物
漠然地進入星期四:茶桌上的杯子, 杯墊,
洗碗池裡傾斜的托盤,
掃把絕望地靠在牆上,牆靠著
失去邊際的虛無;電話單已經付掉,
日歷上用紅筆標出的字樣漸漸暗淡,
就象血跡漸漸幹涸。
沒有悲劇,沒有
劇--在一個輝煌而荒誕的夢裡,
女王死了。
■
紐 約 教 堂
誰記得住他的名字?聖派屈克,聖約翰,或者聖保羅?
但一見他,我便認得,因他有別於世 間一切男子:
巍峨有如雄鹿,靈巧有如掛角之羚羊 。
且永遠低垂雙眼,永遠在悲悼;
永遠悲悼,因為永遠相思。
(有生以來,有生以來呵--
那個最愛我的男人。)
但我總是不顧而去,
留下他孤獨兀立,
有如象牙之塔,風中之旗。
誰記得住他的名字?
派屈克,約翰,或者保羅?
捧在他手中我是一枚碩果,
黑暗,馥鬱,
咬透一層又一層荒涼的果衣,
才能嘗到那枚狂喜的果核。
他的愛強悍如叛軍,荒蕪如死,
河流不能淹沒,火不能熄。
--而我只願他那白羊一般的牙齒
輕輕嚙我的乳房。
那個沉重的紅塵世界
懸掛在風雨飄搖的枝頭,
發出開始糜爛的芳香。
原諒我不顧而去,我的愛,
--在它墜落之前,
我不能不嘗。
■
古鏡記--詠物之一
這是一面曖昧的古鏡。明亮的花紋
曾經穿行此中,逐漸暗淡,
逐漸泯滅,逐漸
歸於黝黑的青銅。
然而,如果拂去流塵,依然可以
窺見盤踞的蛟龍。
(她側身回視鏡中--
一面飄搖的卷旌--
他的手比風隱秘,
比雨矯行。)
古鏡的悲哀
是無法拒絕。
無論廣笑--還是那一縷哀怨的煙視 --
它只能收容。
在許多寂寞的朝代裡,
它守候著她的守候。
在那些重疊的面影當中,
它保持著原始的清明。
當青色的雲鬢
落入無底的黑暗,
它依然擁有
--是報復嗎,抑或只是淡漠--
虛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