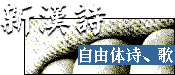﹒陳東東﹒
煉丹者巷22號
……永囚於自我……--加繆
……………………
白晝顯形的土星是憂鬱的
像一盞弧光燈空照寓言
像一顆佔卜師刺穿的貓眼
它更加晦暗,隱秘地劇痛
縮微了命相的百科全書
當我為幸福委婉地措辭
給靈魂裹一件灰色的披風
它壯麗的光環是我的疑慮
是我被寫作確診的失眠症
不期而來了巨大的懊悔
它甚至是虛無,像我的激情
像激情留出的紙上空白
※
它因為猶豫不決而淡出
或者它從沒有現身於白晝
那麼我看見的只是我自己
是我在一本中國典籍裡
在一面圓鏡,在一出神跡劇
陰鬱的啟示下看見的我自己
--啊土星--!漩渦
它壯麗的光環是我的幻視
是我混淆記憶的想像力
不期而來了意願的雪崩
它甚至是悖謬,像我的精神
照耀我拒絕理喻的書寫
……………………
航空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劃過晴天
那漫長的弧線是一條律令
它延伸到筆尖,到我的紙上
到我為世界保持安靜和孤獨的
夜晚。--我坐在我的半圓桌前
我頭上的星空因我而分裂
那狂喜的弧線將貫穿一顆心
如一把匕首在其中剜轉
它是極樂的,並表現為痛楚
表現為持誡的全部苦行和背棄性
仰望。--我坐在我的半圓桌前
航空公司的噴氣式飛機掠過樂園
※
我頭上的星空因我而分裂
仿佛金錢豹內部的貓性破膛而出
而一只大張開翼翅的灰背鴉
其飛翔的骨骼被提前抽象了
--我坐在我的半圓桌前
一個筆尖劃出一條新的弧線
我沉溺於我的現實生涯
幻化生涯,那雙重面具和
兩難之境。我四周的風暴
來自我匕首剜轉的內心
--我坐在我的半圓桌前,上面的
星空,因我而像一副對稱的肺葉
……………………
然而我倦怠,在那些下午
古董打字機吐出又一份
應急文件。透過辦公室緊閉的
鋼窗,或者透過那形式開放的
夏季鋼窗,我仍舊看見
烏有的土星在黃昏天際
下面是城市帶鎖的河流
--那滯澀和纏繞
翻卷起夜色的只言片語
我知道是打字機將它們吐出
而吐出打字機鏗鏘鍵盤的
是公務神額角豁開的裂口
※
家神卻更甚於至尊的公務神
他吐出有關真理的碎片
他令我快活,當我是恭順的
我會於絕望間看到我夢中
喪失的可能性,我會以為
他給了我足夠的世俗信仰
因而在一根虛構的手杖上
我刻下過--反面的野心和
征服的銘言,它或許能支撐
我在灰燼中蘇醒的欲望。當欲望
是我的全部存在,那真實的手杖
就是我死後才到來的晚年
……………………
一匹怪獸將獲得速度,將變形為
往還於記憶和書寫的梭子
它織出了我的顫栗和厭惡
我的罪感,對往昔的否決
它黃鼬般大小的身體疾掠,像一把
掃帚,魔幻女裁縫騎著它飛回
它不僅是時間,是刻骨的虛構
是童年噩夢的精神性異物
在環城路口的聖像柱下
它又帶給我最初憬悟的性之
驚懼。女裁縫升起大蜥蜴面龐
自行車磨圓了拐向成長的懦弱街角
※
那怪獸也將獲得翼翅,自行車將飛越
小學校唯一的瀝青籃球場
朝向過去的龍頭一偏,它又飛越了
夏季旗桿、招展的香樟樹
紅瓦屋頂下空寂的教室
和我在綢布店獨享的挫折
鋼圈急旋,啊急旋的表盤
急旋的指針抹去了隱秘
而另一根聖像柱指針之下
時間被歪曲、歪曲地重現
仿佛土星中變形的暗影
那黃鼬般大小的、我內部的異物
……………………
教育卻不是一對剎把,可以被捏緊
控制一個人向往疾病的發瘋速度
教育虛設,像怪獸自行車鏽死的
鈴,像女裁縫多余的第三只乳房
在一朵壓低的金雲之下
少年時光被平庸覆蓋
被假想的常識和禁忌光環
圈定於蒼白、森嚴、點綴貧乏的
神聖無知。自行車又穿過午後廣場
它撞翻了花壇、教堂玻璃門
晾曬著妓院風信子被單的竹頭架陣
它再快一點,像體育課鍍銀的沖刺哨音
※
禮儀課浸泡於苦澀的酒中
禮儀的冰塊,在社交歡宴間
溶化為喧嘩。--我能夠聽到的
仍然是晴天下鍍銀的哨音
呵斥的籃球迅疾重擊我坍塌的
肩。用以抵御的也許是詞語
是作文簿裡的扯淡藝術
或者,無言,窘迫地挺立
像一幅舊照片展示給我的
仿佛孤獨和稀有的麒麟
古板、腆、局促不安直到顫抖
--在眾人之中我自我隔絕了
……………………
一陣旋風也許塑造了環形樓梯
伸向混亂的通天塔高處。那裡
渾濁的月亮蔑視著我,而我卻因為
存在的過錯,被罰站在冬夜的危樓陽台
一陣旋風,扭結冷卻於胸中的火燄
父親的火燄則如同旋風眼
是幽藍深奧的訓示之火、寂靜
之火、震怒中到來的判決之火
它也是神聖的無名之火。啊無名
神聖,向上的途徑是絆索鐵絲網
是蠻橫的否定和迎頭痛擊,是我在
陽台上,被旋風卷入的孤寂煉獄
※
我忍受的姿態趨於傾斜
在適於夢遊的陽台圍欄前
我有更加危險的睡眠。而睡眠
深處,我缺少一種必要的平衡力
我缺少父親的閃電品質、雷霆品質
一個宇航員征服土星的自信和
狂妄。當一陣旋風實際上摧毀了
通天塔理想,那向上的樓梯也伸向
懲罰,伸向更深的意志黑暗和
權力迷宮。我相信我正一腳踏空
跌進了傷口,我豁開的額角滲出烏鴉血
將污染--神聖父親額頭的尊嚴
……………………
於是我歌唱受辱的青春
那也是甜美中發育不良的
受控的青春。一只手怎麼能
如一柄利斧?破開內心悠久的
冰海;一只手以它色情的撫弄
在走廊暗角,採擷少年的
向日葵童貞。流動的大氣
又梳理出一個短暫的晴夜
--於是我歌唱夢之摩托
騎著它我馳過水塘、遊樂場
倒向混同於陽光的草垛……並且
寫作,像一條姑娘蛇纏上了我
※
精神分裂的語言宿疾纏上了我
它不僅是青春病,是寓言中
奔向死角的貓之獵獲物
因未及改變方向而斃命
它有如性隱患,歡樂的高利貸
仿佛寫作者一寸寸靡爛的
全部陰私。它也是通天塔高處
另一路蜿蜒,另一根絆索
晴夜裡另一只撫弄的手。於是我
要一行咬人的詩、刺殺的劍
--要一記悶棍!於是我歌唱
受辱的青春、甜美中發育不良的青春
……………………
流動的空氣。任意隨波逐流的光陰
有一天世界將轉變為驚奇
有一天下午,我醒於無夢
日常話語的青色果實被拋進了
老虎窗。天井裡盆栽的大麗菊上
一個中年婦女的嘮叨,是果實酸澀
清新的汁液。--母親,她搭著話
而我正起身去迎接黃昏
我看見光陰隨波逐流
流動的空氣裡青春更瘦削
我看見我所歌唱的,在紙上
被透進老虎窗的土星光芒快速一閱
※
而屋子裡,走廊上,潮濕的石塊
散發一陣陣月亮氣息。它曾經被稱作
光芒之水汽,在比喻中由一個形象
代替。--屋子裡,走廊上
潮濕的石塊散發一陣陣青橙氣息
我的蘇醒再重復一次,我喃喃重復
仿佛大麗菊展示互相摹仿的花瓣
影子在迎來的黃昏裡變暗
--母親,她搭著話。她賦予我
書寫而不是講述的能力,在紙上
嘮叨。我看見我所疑慮的詩行
被透進老虎窗的土星光芒快速一閱
……………………
繼續夢遊?--為什麼要加上
猶疑不確定的手杖問號
--在手杖上,新的銘言
已經被刻寫,如一只烏鴉
(錯誤的海東青)成年,換上了
新的更黑的羽毛。在飛翔這夢遊的
絕對形式裡,無所依托的翅膀掀動
表明一個歷程的烏有。那麼為什麼
繼續夢遊?為什麼不加上
猶疑不確定的手杖問號?如果
空氣是肺葉翅膀的不存在現實
而我的絕對雄心是棲止
※
絕對確定的僅只是書寫,就像
木匠,確定的只是去運用斧子
--他劈開一截也許的木材
從木材中顯形的桌子難道
並不是空無?--猶疑不確定的
手杖問號又支撐我一次, 令夢遊
繼續,--穿越我妄想穿越的
樹林;捕獲我妄想捕獲的
群星;而當我注目對街,如
眺望彼岸,……一座山升起
並讓我坐上它悲傷的脊背
去檢討不確定的人之願望
……………………
光的縫紉機頻頻跳針
遺漏了時間細部的陰影
光線從塔樓到教堂尖頂,到
香樟樹冠到銀杏和胡桃樹
到對稱的花園到傾斜的
台格路,--卻並不拐進
正拆閱一封信簡的小書房
我打開被折疊的一副面容
她也是一座被折疊的城市
如一粒扇貝暗含著珍珠
她用香水修飾的肉花邊
呈獻陰蒂般羞恥的言辭
※
那女裁縫咬斷又一個線頭
她帶翅膀的雙腳從踏板上抽離
--光的縫紉機停止了工作
女裁縫沿著堤壩向西
她經過閘口,又經過咖啡館
她經過暗色水晶的街角
寬大的裙幅兜滿了風
她從郵局到法院的高門
到一家雜貨店到我的小書房
挽起的發髻將映上窗玻璃
她扮演夢遊人身體的啟蒙者
呈獻陰蒂般羞恥的性
……………………
我設想,我將累垮在一封信中
--先於綠衣人遞送的呻吟
在女裁縫腿間呼嘯的沼澤裡
我累垮過一次,又累垮
一次。震顫的字跡還原
回到它最早發出的地址
被折疊進--土星誓言和
戲語撫弄的漩渦城市
而那些已經被劃去的部分
又再被塗抹,為了讓急於卻
不便表白的成為污漬
忍無可忍地--吐出那話兒
※
“但信即是性”,摹仿羅曼司
交歡的節奏,卻企圖變成
盲眼說書人彈唱給光陰的生殖
史詩,每一聲問候裡有一次死亡
“但信即是性”,每一次抵達裡
有一個誕生。鋼筆舌尖捅破陰私
郵遞員進入我一個又一個
無眠之夜。--又一夜無眠
一夜無眠裡我期待門環第二次
叩響,那不同的抵達和問候
不同的誕生和死亡,不同的信中
共同的性:出自幾乎已累垮的手筆
……………………
叩響門環的卻不是綠衣人
甚至也不是--恭歉友好的
瘦弱年輕人,或者那擁有
無邊權力的命運佔卜師
--那佔卜師此刻也許在
雲端,在一座有著無數屋頂和
眾多庭院的星宿禁城裡
他是否能突圍?他是否將
到來?下台階的姿勢仿佛舞蹈
像一架推土機!要奮力擠開
潮湧向通天塔遺址的人類
--汗濕了揣進胸懷的天啟
※
那麼是風在叩響門環,是風
造訪這煉丹者巷。它不僅叩響
它撼動小書房,它的鋒刃
割破燈頭上火燄的耳朵
--“那不過是風”,我鎮靜地
寫道,“然而我上面的光芒
搖曳”。光芒搖曳
光芒熄滅。--我聽到絕對
我聽到了絕對寂靜的回聲
如割破的耳朵滴濺開黑暗
“那確實只是風”,我還在書寫嗎
風中我寫下我看不見的文字
……………………
緩慢的城市。緩慢地抵達
建築物彌留如一輛街車朝終點
蠕動,時間是其中性急的乘客
這性急的乘客曾咆哮在馬車裡
曾大聲催促過有軌電車
其嗓門卻壓不下震顫轟鳴的
柴油機客車,而當一輛空調車
被阻於交通的半身不遂
他默然其中,一顆心狂跳
城市因為他則已經行進到滯澀的
中午。建築物移開堤壩枕頭
其實是江面上陰影在收縮
※
其實是江面上一群鳥轉向
它們從靈魂長出的羽毛沾染
瀝青,負重掠過輪船和舊鐵橋
而我在它們巡警般多疑的盤旋上
試探,企圖以高出倦怠的困惑視點
統覽這中午的緩慢和性急、彌留
和抵達、意志之死和波瀾般
活躍的欲望之蔓延。我企圖站在
標志性建築象征的屋脊,去迎候
突如其來的天啟。土星呼拉圈
偏離軌道--被臆想成瞬間永恆的
超脫--一架飛機卻低於期許
……………………
也許,我繼續上升,到更高處
俯瞰,--但已經被戲稱為
膝蓋的斜面我無法去攀爬
那是塊脆玻璃,是薄薄的一層
冰,經不起沉重的精神性跪壓
那膝蓋斜面只適合安放我
夜半的四開本、滑翔的羽毛筆
無法繞道而行的詩句,和直到
黎明才略有起色的疲憊的
書寫。--這書寫成為我
真實的攀升,就像死亡
靈魂在其中真實地誕生了
※
城市又展現在書寫之下。在書寫
之下,城市的膝蓋斜面被俯瞰
統覽,仍舊經不起精神性跪壓
但它有空空盪盪的品質,有空空
盪盪的明信片景觀:環形廣場
空無一人,街道穿過空寂的屋宇
延伸進空洞靜止的集市,那裡的
咖啡館座位空置,亮的空杯盞
反射陽光,反射陽光中空寂的
小書房。--小書房裡,語言空自
被書寫所書寫,--在煉丹者巷
22號,我正空自被書寫所書寫
……………………
幸福是飄忽不定的降落傘
要把人送回踏實的大地
誰又在半空中選擇落腳點
像詩人選擇恰切的詞
事物的輪廓正越來越清晰
誰又在下降中提升了世界
像身體在沉淪中純潔愛情
像一個寫作者,以無端的苦惱
客觀化苦惱。現在誰又從小書房
拐出,披衣散步,在煉丹者巷
誰的頭腦中一架樂器正被試奏
帶來跳傘般飄忽不定的音樂啊幸福
※
那樂器會試奏出誰的生活
那被設想的、在紙上也無法確立的
生活。--現在誰拐出煉丹者巷
迎面進入了純青之境?城市或
宇宙,僅只是足夠累贅的共鳴箱
可究竟誰是撥弄火燄者
他其實也撥弄著寫作的琴弦
可究竟誰是那不安的跳傘者
他跟我一樣,真的能踏上那
幸福之地嗎?啊爐火!在爐火上
誰會是這個世界的煉丹者?他的
現身,在於從生活升華那虛無
……………………
而純青之境!純青之境又正好是
他的虛無之境。煉丹者爐中的
火燄更抽象,如音樂抽象了
這個世界的時間和時間
他向我展示的,他以為我
覺悟的,也僅只是作為虛無的幸福
在他的幸福裡我孤僻自我
在他的虛無裡我營救自我
一個人散步,到更遠的境地
騎馬、遊泳、劃船、打短工
以木匠的手勢斧劈本質烏有的黃楊
--令書寫的半圓桌顯形於技藝
※
--令一行詩句顯形於無技藝
半圓桌上空的土星迂回融入又一夜
我頭腦中試奏的樂器停歇,音樂
寂靜,時間則依然。純青之境裡
顯形的詩句是一次艷遇……是
煉丹者巷口一個小蠻腰女郎的嫵媚
“我跟她有甜蜜的風流韻事”,“我
完全陶醉於她的節奏”,饕餮郵筒
生吞明信片,卻無法消化我寧靜的
醉意,我醉意背後寧靜的厭倦
而半圓桌上空,詩行本身是守口如瓶的
只字不提那純青之境的虛無啊幸福
……………………
因此神跡劇演變為喜歌劇
弧光燈空照寓言樂池裡斷弦的
豎琴。因此愛情是必要的放逐
是贖罪的寫作忍受的鞭撻
--出現在紙上,那語言的驚愕
也將被文刺進克制的驚愕
引起一個精神戀愛的夜女郎
驚愕,驚愕地投入一個人羞愧的
人性懷抱,將色情理解為歷煉的
懷抱,無非是驚愕之驚愕的懷抱
因此弧光燈空照命運,空照愛情
--當愛情是命運深處的恐懼
※
--但愛情是命運深處的溪流
它流經太多的骯臟和貧乏。如此
艱難,虛榮被逼迫,陌生的同情和
膽怯的肉欲,卻要從速度加劇的
血液循環裡抽取力量,抽取純潔
也抽取意願。留下的只會是一紙
婚約!婚約的神跡劇演變為寓言
一個丈夫將遊離於事外:他注定是
蠢才,隨風飄逝。--而在他
遺憾地幸免的獨身生活裡,他也許
成聖,也就是著魔。不過他盡管會
戴上冠冕,結果也一樣,在床上了結
……………………
當一個炎夏展示它僅有的七天春光
像糾纏的未婚妻同意從熱烈
暫且退步,我會獲得我想要的一切
美景無我和書寫無我,以及另一根
支撐夢想的夢想手杖--那正好是
一些夢,讓我能夢見他,如夢見
不能復活的死人。或許他只是
白日飛升,從煉丹者巷到
城堡上空--在越來越縮微進
藍天的遲疑裡回看夢遊者
回看夢遊者即將醒悟的漩渦城市
漩渦城市的炎夏裡僅有的七天春光
※
此刻是否已經是第六天?已經是
第六個黃昏此刻?純青第六次
轉變為幽藍。一個不能復活的死人
注定會更暗,他貫穿城市上空的倒影
跟我的弧形筆劃交叉,是否構成了
多余的判決?判決必然的武斷和草率
美景無我和書寫無我繼續擴展
夢卻要將夢還給無夢,如同春光
終於把自己還給了炎夏。“也許我又
捕獲了自己”--繩索或鐐銬
則正好是我的命運解放者……在
第七天,熱烈又復活了我的沉溺
……………………
復活。再生。從一種空靈還原為肉身
欲望又成為漩渦城市裡帶鎖的河流
垂暮的日光,牽扯不易察覺的土星
--這講述的不是我
--這講述的只是我偶然看見的
隱約幻象,浮泛向晚,在
明信片反光的景觀一側,打上了
郵戳的紅色印記。七天以前,我將它
寄出,如今那綠衣人已將它送達
……由於送達,它更加被証明是一個
幻象,是我從幻象中終於獲得的想像的
真實:想像的復活和想像的再生
※
那麼這想像的力量在生長
像幾只灰背鴉飛回了舊地;像所謂
永恆,從枯枝催促一棵新樹
一棵新樹對風的招喚;像土星周圍
月亮們壯麗,窒息公務神可能的感嘆
我沉溺在我的多種生涯裡
我不曾遇見的想像的煉丹者比我更
沉溺,一半欲望托附給性(也就是
信),另一半欲望是徹夜寫作,徹夜讓
神跡劇,在想像的寓言航線上飛翔
再飛翔,直到紙上的喜歌劇轟鳴(劃去
余生),像航空公司的噴氣式飛機
……………………
局部宇宙,它大於一個未被筆端
觸及的宇宙。土星局部的光芒內斂
在我書寫的局部時間裡。這書寫的
時間,也是一個人抵達局部聖潔的
歷程,也是一個人精神化局部器官的
意願,--有如懸浮於黑暗的球
那面向燈盞的一半裸露,並且因裸露
成為大於黑暗的善;這又像
尚屬完好的一半肺葉,承擔了我的
全部呼吸,包括額外的另一類
書寫,另一些宇宙,滿布陰霾的
--另一半肺葉的充血急喘
※
那額外的一半肺葉卻並不多余
它的烏雲和殷紅晚霞幾乎是必要的
局部的病痛命定,因為終於要
致命,要在我背後跟一個意願
秘密幽會。這幽會帶來局部復蘇
一瞬間幸福,清新涼爽的少許良夜
--紙張上局部的詩篇完美
而完美即純青,即煉丹者爐中
單一的虛無。詩句蘊含的純青火燄
又將被吐出,被詩句表述為
局部死亡。它大於--全體
如終極夢幻大於夢遊人漫長的一生
……………………
或許我僅僅缺少我自己
我捕獲的只是我靈魂的局部
--局部靈魂掩蓋著我
一件披風,從灰色到荒蕪
掩蓋我寫作的精神面貌
而那匹黃鼬般大小的怪獸
出入其間,或奔走於小書房
奇怪地顯現在父親的嗓音裡
驚嚇已經被催眠的兒子
它成為佔卜師又一個依據
表明末日還沒有來到。還沒有
來到……還在行色匆匆的路上
※
死亡則早已來到了紙上,它被筆尖
播洒進詩篇,不再是一個
灰色的局部。它迅速擴展為
耀眼的白色,封住繼續吟唱的
喉嚨。死亡是更為無視的怪獸
黃鼬般大小的兇兆之貓
被佔卜師刺穿了劇痛的眼睛
死亡的變形記更為直接
如弧光燈照亮的那一半黑暗
被黑暗隱去的,也仍然是
死亡--每一種邪惡、每一種
罪孽、劇痛中每一種巨大的安祥
……………………
現在你來到這幽藍的門牌,變幻之
貓,黃鼬般大小的土星之異物
現在我也重回這門牌,它的純青
鏽成了暗紅。一陣風輕撫,一陣風
睡去。正午的烈日像煉丹者不慎傾倒的
八卦爐,澆淋一個回首的幽靈
一個喪失了形象的詩人。現在你來到的
幾乎是煉獄,我來到的是一座
地上樂園。--火燄的蓄水池悠深
清澈,火燄的噴泉則殘忍而激越
火燄是佔卜師揭示的天啟
--令我的倒影……是你的無視
※
--令我的倒影是你被刺穿的
無視之貓眼,隱秘的黑暗電擊趾爪
你更為盲目,從門牌到屋檐,到
我的小書房,到鳥籠空懸的老虎窗啞然
你的皮色在夜晚混同於金錢豹星空
你的貓性負載大於宇宙的不存在
--啊當我已不存在,你縱身一躍
你掠過的仍然是我的半圓桌,是
半圓桌上,我仍未合上的中國典籍
而當你仍然無視這典籍,無視這寓言
--請殺死我吧--悖謬的典籍
說--否則你就是……你就是兇手
……………………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