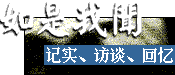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趙毅衡﹒
一度好斜陽
--追思吳方其實我無法謬托吳方的知己,想為吳 方寫篇悼文,卻總懷疑自己是否有資格。 吳方的及身著作,我雖然讀得不少,萍蹤 異鄉,手頭只有寥寥幾篇復印件,無法給 他的理論或文學成就作個總結。猶豫再三 ,想想不寫也罷:吳方生前從未托我寫什 麼,至今也沒有哪位編輯向我征稿。忽忽 然已經過去一年半,寫悼文的理由越發不 存在:“時間早過了”。
每年都聽到國內一二位學界或文壇大 人物去世的消息,而且不久後就會有單位 出面編紀念集之舉,也常有被征稿的榮幸 。坐下想想,卻只是在某某年月聽過一次 課,或在某某會上聽過一次演講,我只是 芸芸聽眾中的一個,沾到一點智慧的恩澤 。就靠這些,也有資格列於憑吊者之中?
毛主席去世的大悲時刻,我正在一個 煤礦接受改造。某副書記的夫人,為她的 丈夫應當站在第幾位,到黨委狠吵了一場 。那天全礦工人連家屬小孩共同努力,就 是沒能哭出一個氣氛。肅聽天安門城樓上 的排列順序時,我竟然為治喪委員大人們 的安危犯愁起來。恭送偉人,本很容易出 亂子的。
吳方絕對算不上任何等級的人物,也 無人會編記念集,也不存在治喪排第幾位 的問題。我給吳方寫這麼一篇太晚的文字 ,怕也不會有人責我僭越吧。
聽到吳方的死訊,正是一九九五年夏 天離京前一夜,記得是八月十六日。一個 朋友借送我和虹影的由頭,找了一些同行 喝酒。文人聚會,氣氛少不了歡快熱烈, 說話少不了放言高論。忽然從機場來了二 位不速之客,嚴歌苓和她的丈夫
Larry Walker。Larry 曾在沈陽任美國領事多年,北方話說得油 極了,聲調準到能裝傻,把妻子的名字叫 出幾種意思絕倒的聲調變體,滿堂為這個 洋鬼子喝彩哄笑。
有一個人在我耳邊說,下午吳方懸樑 自盡。
我正在沒命地大笑,突然剎車,一下 子嗆住了,驚得雙眼發直。
“唉,安樂死的機會也不給一個!” 旁邊一位聽見了,插上一句嘴,搖頭嘆息 。顯然他們早知道了這個消息。
我想追問一點情況,每個人給我介紹 了幾句,就被別人搶去了話頭:作協黨組 正在提拔“跨世紀人才”,有的新領導幾 乎比在座人兒子的年齡還小,那個消息當 然更吸引注意。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客 是好客,天下多的是有趣談資。天下每秒 種都有人死去,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會死去 ,誰也不能保証,死後人們會為他悲哀多 長時間。葬禮還沒有開始,夜還沒有星移 鬥轉。吳方把繩圈套到脖子上的時候,如 果想到朋友,恐怕是希望我們為他終於得 到解脫擊缶而歌吧。
我嗆得氣順不過來,只好走到陽台上 去。
一九九五年夏,我雖然是有思想準備 而回。但整個中國忽然變成了一個特大市 場,無時無地不在喧鬧囂騰塵土飛揚,依 然給我猛烈的“文化震撼”。友人這個樓 不高,看不遠,但是朝哪個方向看都是熙 熙攘攘有買有賣,賺錢的自由使舉城若狂 。而在這烈火油烹的“美好日子”中,若 有些知識分子自願杞人憂天,苦惱於責任 感,當然只是應了堂吉訶德的雅謔。不過 我那時突然落入的淒涼心境,與此無關, 只是為古老而淺薄的人世無常感慨。
我第一次聽人鄭重其事地說起吳方, 卻是一位知識界的重要人物說話。文化部 文藝所辦的《文藝研究》雜志,吳方在一 九八八年底成為第四個副主編,到一九八 九年秋天的大換班時,竟然還在。“這就 是希望所在!”那位朋友以他特有的熱情 說道,“這就是証據:石縫裡會長出樹來 ”。
翻一下那幾年的《文藝研究》,覺得 吳方的留任,恐怕不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特 別提拔吳方,也說不上是某個方面借此發 出什麼信號。這個表情沉重嚴峻的“大刊 ”,八十年代的最後兩年的確編得很不一 樣,文章短小而精彩:李銳論現代派,汪 政曉華論間距,陳曉明論拆除深度,蔣原 倫提倡批評的攻擊性。這些是不是吳方的 “新政”,我說不清,八十年代末,一些 最僵硬的人物都“咸與維新”,自稱“容 忍”,不一定吳方才能組這些稿子。到八 九年第五期起,此刊就全套“主旋律”, 吳方的留任也一樣不起作用。
但是那朋友眼睛中的希望之光,也使 我朦朦朧朧產生了希望。我就把一篇論文 《中國小說中的回旋分層》給了吳方。那 個氣候中,討論形式問題也是犯忌。雖然 吳方來信表示欣賞,刊出卻是一年之後的 事。九一年第四期該刊的正副主編名字全 部消失,明擺著在清理了。下一期就不再 有吳方名字。吳方後來說我的那篇是他做 這個撈什子副主編簽發的最後一篇文字。 一九九二年,他在雜志已經呆不下去,辭 了職,去文研所作清靜的研究人員。又過 了一年,他離開文化部,到語言學院任教 。
我沒有問他什麼原因。如果吳方的留 任是個小小的錯位,他的去職恐怕不是。 他並不是個激進的前鋒,他只是一個誠實 的知識分子,但是中國常有誠實的知識分 子不能做副主編的時候。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回北京做一年的研 究,一時找不到地方,在東郊機場路的社 科院研究生院招待所住了三個星期。北京 太大,我熟悉的只有這個地方,下機場就 奔這“老家”來了。三個星期中,肯長途 跋涉來看我們的只有兩個朋友:吳方與張 頤武。吳方是自行車來自行車去,怎麼說 也不肯留下吃飯,頂著夏日中午的太陽騎 車回去了。與張頤武在飯桌上談談笑笑是 很快樂的事,一些北京開始流行的新的文 化現象在他嘴裡化成無窮笑料,時針在歡 樂中跳動。與吳方簡直是無言枯坐,碰巧 ,吳方讀過我在一本地方雜志上寫吳宓的 小文字,於是我們大談一頓吳宓。後來我 讀到吳方的書《世紀風鈴》,才明白那不 是碰巧。吳方是讀幾十卷書寫一篇文章的 人。他要寫吳宓,就把所有關於吳宓的文 字都看了,哪怕我那種破文字。他沒有加 以評論,顧我的面子。
一輩子不走運的吳宓,把我們首次見 面的窘迫給救了。不知為什麼,我現在每 次想起吳方,就想起吳宓--耿直的北方 漢子,黧黑的面目不象知識分子,卻是做 學問也象耕田一樣執著,決不跟著時風轉 ,錯也錯出個名堂。不巧的是,吳宓也是 自殺身死。
《世紀風鈴》的文風,曾經得到我的 一位最挑剔的朋友無保留的的讚美,那位 朋友是周作人的隔代望門子弟,從來沒有 說過我的文字一句好話,他在吳方貌似平 淡,實際上極為講究的的文體中,看到睿 智的沉潛,和對人文精神的執著。
那年在京時間較長,又見過幾次,在 會議上,在私人集會上。九二年秋天,好 多人憑政治嗅覺或憑內部消息,認為翻燒 餅時間到了,有幾個會開得真是轟轟烈烈 ,聽著有來頭的話語驚四座,全場興奮, 第二天就傳遍全城文化圈。吳方大部分時 間都默不作聲地坐在角落,臉無表情,不 記得他發過言,好象純是職務所需才來的 。
倒不是他有先見之明,知道這一次, 燒餅只會掛起來兩面不沾邊,不會有翻煎 的好事。他只是天生不喜歡說話而已。有 一次在研究美術史的朋友尚鋼家小聚,《 讀書》的編輯吳斌溫文爾雅,沒有想到她 的丈夫馮統一,竟然是個連相聲演員都自 愧弗如的幽默家。我們都聽得笑神經不由 控制,吳方更是只有坐在一邊莞而微笑的 份。
聽說吳方病倒,已是很晚,一九九五 年初。一個來倫敦的朋友說的消息,說是 癌症發現時,已經擴散,腫瘤已經在壓迫 脊柱神經,疼痛異常,化療和理療更加重 痛苦。夏天我們準備回國一次,臨走時顧 曉陽來遊歷歐洲,帶著健康得叫人驚奇的 老母親。顧又是一位京味語言大師,談笑 中生生活剝一系列如雷貫耳的名人。我說 到吳方,他高興地叫起來:“老朋友,老 同學,人大文學社的老戰友!我早就帶口 信叫他務必堅持到我回去看他!”我說, “行,再給你帶一次口信。”心裡卻挺詫 異,怎麼木訥口拙的吳方,交的朋友一個 比一個談笑風生。
回到國內,就打電話給吳方的鄰居兼 好友尚剛,詢問吳方什麼時候回家--他 是慢性病人,周末是能夠從醫院回家的。 我們約好一個時間。尚剛建議我們別帶鮮 花什麼的。“吳方是個本色人,帶點水果 還實在”。
過了幾天,尚剛忽然來電話。他跟吳 方說了我們將去看望他的事,不料吳方一 聽,竟是潸然淚下,要我們別去:不想讓 我們看到他的一副慘相。我和虹影聽了極 為惶惑:我們當然不願意給他增加痛苦, 但是他生病已久,北京文學界的朋友去看 過他的不在少數,他們從未見到他情緒上 如此反應。或許是因為我們遠隔重洋,在 他的心目中是特殊客人?
久居海外,偶爾回國作訪客,到九十 年代中期,情況已經不一樣。同行的“怠 慢點無所謂”,刊物的“何妨往後排排” ,出版社的“選題尚須報批”,文藝界半 官兒們的“小心一點不會錯”等等。法國 人說“遠於目者遠於心”,中國人說“人 走茶涼”,本是人世常態。到一九九五年 ,我們碰到此類純粹操作問題,早已經不 再生氣。象吳方這樣,還把來客之遠,作 為情意殷切來想,而且竟然淚下,的確思 想舊得少見。
不過當時,吳方的異常反應,弄得我 們進退不得。思考再三,決定扛一個大西 瓜和一堆水果,匆匆看望一下,就盡早撤 退,免得大家挨窘。
吳方家至今住在東城一個狹窄的四合 院,各種附加建築早把院子變成了迷宮。 吳方自己的房間,好象是防震棚時代的遺 跡。堅持保存古城風貌的人,對大雜院情 有獨鐘,不妨與吳方的孤寡換房。吳方的 文化部第一大刊副主編--國務院的副處 級幹部--為官二年真是做得不怎麼樣。 而且如今,要幹部退下,得升一級加一室 ,看來吳方的辭職也是白辭了。
有了精神準備,吳方的外貌巨變,沒 有使我們過分吃驚--死神已經在他臉上 抹了重重蠟黃的粉彩,臉頰深陷,頸上皮 膚掛成條。他身子已經很單薄,雖然穿著 白色的單布衫褲,看得出只剩一把骨頭, 歪斜地癱坐在一張單沙發上。“房間”很 小,唯一的一張椅子我坐了,虹影只能坐 床上,尚剛只能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我 們請他陪來,以防應付不了的局面。吳方 的的妻子和孩子都出去購物了,不知是正 巧還是有意安排。
該是我們詢問病情,並且安慰打氣一 番,用我們對晚期癌症的藐視,來幫助他 戰勝疾病。吳方卻不等我們開口,立即談 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上 我那篇“‘後學’與新保守主義”,徐賁 論所謂“第三世界理論”的文章,以及續 後各期上張頤武,鄭敏,許記霖等人理直 氣壯的反駁,還有我簡短的回應。每一篇 文字,他都記得清清楚楚。我著實吃了一 驚:我們在京近二個月,見到文學界理論 界不少朋友,無人談起這場爭論,哪怕一 些被我“點了名”的朋友,都絕口不談此 事。起先我以為是他們給我面子,不便當 面指斥。後來才明白,《二十一世紀》不 容易讀到,好多人聽說而已,沒去找原文 來讀。朋友相聚,這題目也太無趣。
吳方滔滔不絕地談起來。我們三人交 換了一下眼色:太好了,原因雖然不明, 預想的尷尬場面卻沒有出現。吳方的話音 ,比以前更輕,臉上不時有異樣的表情, 陷在沙發裡的身體時不時動一下,看來疼 得厲害。但我們都明白,減少他的痛苦的 最好辦法是讓他談下去。
我知道,吳方是不會同意我的觀點的 。按我的標準來看,吳方就是屬於我說的 “保守主義者”。這個詞,應當是個夸獎 ,至少比“激進主義者”強多了--他自 己在好幾篇文字中直認“保守”而不諱。
吳方在八十年代是先鋒文學與新理論 方法的熱情辯護者,他的一系列文章至今 仍被人引用。到八十年代末,他卻避開當 今,轉向文學史。一九九二年結集於《世 紀風鈴》中的各篇文字,都是對吳宓,梅 光迪,周作人,陳寅恪等為學為人的擊節 讚美;此後他的研究更向前推,轉向晚清 人物,從章太炎,王國維,說到一生經營 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就吳方個人而言, 是他自己選擇的課題,就整個學術界的趨 向來看,我有十足的理由說他是新保守主 義思潮的一個“分子”。
但吳方卻不是跟潮流走的人。他寫的 那本《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的內容提 要:張元濟從官場轉向出版業,“此一選 擇,未始不是明智的,脫俗的。這使他得 以避免歷史的種種是非恩怨,既非庸碌無 為又非風雲人物,既未陷身於歷史的某種 虛幻之境,又不象“舞台”上的匆匆過客 。”
而吳方對“張元濟式”文化人的欽佩 ,不著眼於其“歷史貢獻”,講究的是他 們的人生境界:“這樣一種‘存在’的意 義,似乎很令人回味。當然回過頭去看, 也是人生不易到之處”。
我可以打賭,這內容提要是吳方自己 寫的。文筆之從容優雅,國內同輩中很少 人有此手筆,尚在其次。明顯這是吳方在 寫自己,而不是在寫一個收斂鋒芒甘心做 實事的文化人。世紀末中國文化人的心路 歷程,往往要到世紀初去找,二十世紀的 中軸對稱,一至於此。
甚至,從當代文學研究轉回世紀初, 在吳方來說,只是眼光投向的變化,他的 立場沒有隨世風而轉動。一九八八年刊在 《北京文學》上那篇妙文《論矯情》,歷 數了當時幾篇把文壇震得大搖大晃的名作 ,“很象天賦甚高的少年人在人面前說話 ,雖然有銳氣,但說話的調門往往過高” 。吳方的評文論世,待己待人,可以說是 一以貫之。
我的性格可以說與吳方正相反,但是 我欣賞任何一以貫之的人,在今日,這是 尤其難得的人品。
那天吳方批評我的觀點,還是很小心 地選擇字眼,不是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吳方做人一向為別人想得太多,我倒是 很希望他直接指責,那篇文字反正已經給 我添了不少論敵,何不讓吳方痛快地臭罵 一頓。他的思路極為連貫,虹影和尚岡簡 直無法插進任何話。我這當事人大都只是 點頭稱善,不是尊重一個面臨死亡的朋友 ,而是我明白那種爭論不是是非問題,而 是觀察角度,或者說,批評立場。我本來 就轉變不了任何人的角度,何不讓吳方貫 徹始終。
吳方真的說高興了,忽然開始臧否人 物,一個個地譏評當時批評界風頭正健的 人物。我從來沒有見到他如此放言無忌。 每個能迫使同行注意的人物,我覺得必然 有特別的長處,“風頭”本身,不應當受 指責。但是我同意吳方的一個觀點:弄文 學藝術,不管是理論還是創作,不能太聰 明,得有點兒傻氣。這個世界各行各業都 需要聰明人物,要把文學做到“人生不易 到達”的境界,聰明卻是很礙事的。
我至今納悶,一個腫瘤已擴散到脊椎 ,壓迫著神經中樞的臨危病人,要靠不斷 服用強劑止痛藥才能勉強坐起一會兒,他 哪來的閑心關心這種文化界大部分人都不 願意聽一下想一下的問題?或許平時他在 病床上消遣的讀物,竟是這種枯燥的文化 討論?
不管怎麼說,吳方的“反常”熱情出 乎我們意料,但也讓我們非常高興。我的 文章或許“觸到”了吳方的“痛處”,轉 移了他的感覺興奮灶。尚剛說,吳方病了 近兩年,從來沒有見到他那天談興之高, 實際上,以前幾年我也沒有見到過。可能 這次見面是我那篇惹禍的文字做到的唯一 好事。
“回光反照”,我突然想。一個依然 充滿智慧的頭腦,依然在活躍地思考,危 乎哉地頂在一個朽敗的身體之上,還不得 不跟著身體一起燒成灰燼,世上有比這更 大的悲哀嗎?
那天只有一次,吳方說起他的住院。 “我看到從郊區遠遠趕來的農民,隨便給 人打一針止痛藥,就讓人家回老家等死, 根本不給治!不過真也沒法:進口的治癌 藥,一針五千!我剛到語言學院沒幾天, 學校對我算是大方的”。看來吳方老記住 別人好處的習慣沒有變。“隔壁病床,就 因為單位付不起這針藥,去了”。
或許這醫療巨款對吳方的折磨,比在 他內臟的亂鑽的癌細胞更甚。他天生是個 無法心安理得地享受比別人更高待遇的人 。這樣的人,現在真是鳳毛麟角,大部分 人總是在抱怨招待等級不夠。人心不古, 有權者做的榜樣太糟。
我甚至懷疑,他明白這是個不治之症 ,不想再繼續白花公家的錢,可能是他提 前結束自己生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不一定 是崇高的利他主義,我想這是中國讀書人 的舊道德,不願暴殄天物。
坐聽吳方暢論,不知不覺地過了一個 多小時,我們很不安,虹影幾次丟眼色, 提醒我該走了。我們本想只坐幾分鐘,尚 剛早就警告我們不能超過二十分鐘。但是 吳方不讓我們走,他看來還真希望聊下去 ,談這個所有健康的理論家們都認為太迂 腐的題目--中國文化。
臨走,我們說過兩個星期再去看他。
象大部分這種承諾一樣,很難信守。 雖然我和虹影總在說,什麼時候到醫院去 一次,一直到這最後一夜,還是沒有去。 心裡倒是想起的,只好說離京後寫封信給 他吧。不料就在這個時候聽到他自殺的消 息。
據說他臨死前很平靜,把家裡人打發 出去,打了幾個電話處理一些小事,接電 話的人都說聲音極為平靜,沒有任何情緒 波動的征象。死對他來說並不可怕。最後 他打了個電話給正在給他編最近一些文章 的馮統一,說他決定了書名:《斜陽系纜 》。
標題極不祥。家裡,醫院裡,都取消 了他任何死得舒服的可能,只有這個小小 的改良防震棚,還有屋樑可系一纜。
半醉的晚會還在喧鬧,陽台上仿佛可 以看到東四十條立交橋,已經安靜下來。 我聽見背後傳來自行車鈴聲。那種熟,不 用下車,捏一下車閘擺一下龍頭就夠了。 我知道那肯定是吳方,我倒想知道他匆匆 上哪裡,這麼晚了,離家而去的方向。於 是我轉過頭來。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