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晨駿﹒
城市和鄉村
我從鄉村來到城市,放棄了貧窮和落 後,也放棄了原始的活力。我30歲以後 ,尤感活力對我的重要。在漫無邊際的蒼 白的日子中,我的體力在緩緩下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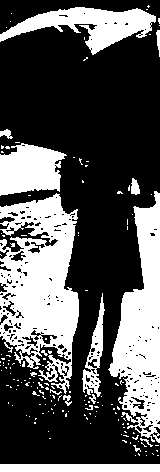 當
我偶爾伸出頭,從自家的門口,看向灰蒙
蒙的天空,我的視線和天空一樣疲軟。
當
我偶爾伸出頭,從自家的門口,看向灰蒙
蒙的天空,我的視線和天空一樣疲軟。年初,我搬到現在的地方,在收拾房 間時,隔壁老頭拖住我的衣袖悄悄問,房 租多少錢?後來又問過好幾次,但我都沒 有告訴他。我不懂他為什麼老是追問我房 租的事。與他貼身站著,我厭惡他嘴角的 涎液。隔壁這一家,除了老頭,還有三個 人:老太、女兒和外孫。時間久了,我對 他們不像剛來時那樣處處躲避了,我甚至 認為他們都是好人呢。我在門口看天空時 ,老頭也正在門外澆他幹癟的盆花,嘴唇 無聲地囁嚅。
實際當我的視線與天空接觸時,我接 觸的並非天空。我接觸到的是被我的經歷 過濾了的天空的概念。我早就與我幼年時 的藍天遠離。我跟隨著另一個我,拋棄了 鄉村來到城市,而另一個我也並不比我更 多地了解城市,不比我聰明,也不比我更 適應城市的汽車尾氣和街道上毫無感情色 彩的行人。他的任務就是帶領我向城市進 軍,把我丟卻、拋進、扔在一個虛幻的城 市裡,迫使我接受城市的教育,接受努力 做人的訓誡,不管徒勞與否。
我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以為這就是城 市最好的時刻了。我無錢乘坐的士,只得 步行回家。街燈淡黃的光照著商店櫥窗, 也照著我的軀體。風在穿梭,彈奏著我緊 張了一天的神經。我是一個具有某種職業 的人,這是我的身份。即使此時街道上只 有我,我的身份也不會遺失。我和我的身 份一起在街旁享受著城市的夜晚。在城市 ,只有流浪漢沒有身份,流浪漢受人歧視 是因為他沒有身份。而沒有身份之人,名 義上便不屬於城市了。
我無法從城市歸回鄉村。我懷念鄉村 ──我活力的源頭,卻寧願在城市中衰老 和枯竭,我不斷消耗著鄉村對我幼年的滋 養,卻不能重新去體會鄉村的益處。鄉村 生了我,而城市改造了我。
在這個租來的房子裡,我住了近一年 了,我越來越感到隔壁那家缺少了一個人 ,即那老夫妻的女婿、那女兒的丈夫、那 小孩的父親。有一次我似乎聽我老婆說, 那個女婿、丈夫和父親是個當兵的。但當 時我沒深究,現在我忘了我老婆是否說過 這樣的話了。確實的一點是,常到隔壁那 家來的男人,是小孩的舅舅。一般到了星 期天,小孩的舅舅就提著一捆菜鑽進隔壁 的門洞。
我們住老式樓房的2樓,東西向,緊 挨漢西門大街。街道兩邊開著一間間小飯 館。大清早炸油條、中午和晚上炒菜的油 煙,飄向我家門口。單是油煙倒也罷了, 有時飄過來污濁的臭味,我的眉頭不由得 皺上老半天。小孩的舅舅在樓梯口出現, 迅速穿過走廊上的濃油,逼近我。這是他 的休息日,也是隔壁一家歡樂的時刻。那 小孩從黑暗的門洞裡跳出,撲向他舅舅。
一天朋友小顧來訪,我趿拉著拖鞋, 和他去不遠的漢西門廣場喝啤酒。我們坐 在一截半塌的城牆下,背對陽光,向散布 廣場的女人們身上掃視,無聊地談論著她 們誰看上去像雞。一個騎童車的小孩晃過 我們眼前,車後跟著兩個婦女。我一愣, 這不是我家隔壁的女人嗎。她個頭矮小, 臉微微發紅。和她並排的那個婦女也很面 熟。他們三個迎著下午的陽光,從我們眼 前晃過。
隔壁淌口水的老頭總是給我孩子糖吃 。遇到這種情形,我便對我老婆說:“快 把糖還給人家!”我老婆一把搶走孩子手 中的糖袋--“還給人家”--“我家有 糖”--“你們留著吃”--“謝謝”- -“不用,我家有糖”。早晨,我推開家 門,門前的走廊上擺滿了破破爛爛的床架 。老頭正給床架塗上暗紅色的油漆,他臉 上洋溢幸福的波瀾。“嘿,你早!”老頭 對我說。
一只東張西望的鳥,在城市中不斷遷 徙、築巢,過一陣子把舊巢扔掉,築一個 新巢。我就是這只鳥。我的家當在一次次 遷徙中損壞,或失去了原有的面貌。我老 婆在遷徙途中養成了“抹”的習慣,她每 天下班回家,就從廁所的門後取下一塊抹 布,在家具表面抹來抹去,在冰箱、洗衣 機和電視機的外殼上抹來抹去。她通常的 形像是:右手抓著抹布,站在房間中央, 警惕的眼神注視著房間裡的每樣東西。而 這勤勞的人對於做飯卻無興趣。
我做夢,夢見過各種場景和各種人, 夢見殺戮和性交。殺……性交:我將精液 射在一個女人肉體上,醒來發現我的短褲 潮了。我的夢境純情而傷感。夢中的那些 人頭腦簡單,只按自身邏輯行事,都穿著 藍衣服,是皮影人。
近來,我很少做夢了,過度的疲倦和 家庭的喧囂,擠壓了夢境的疆域。當我麻 木地仰視天空時,夢境也向銀灰色的天空 中飛去。從鄉村到城市,我不自覺地放棄 了貧窮和落後,接受了富足。可幾年之後 我又自覺地放棄了富足,自覺地接受了貧 窮。在城市中做一個窮人,最大的不便來 自心理。那些高樓,那些報紙,那些行人 ,都暗示著貧窮是一種罪過。當我貧窮的 時候,我無法忘記我曾經富足的過去。
錢……死神擁有的最銳利的匕首。自 尊、人格、閑暇、平靜和坦盪,這些都是 錢的別名。“會有錢的,”這是友人所能 給我的最好的祝詞。這是錢的世界,這是 錢左右的世界。我之所以思想,是因為我 要用思想換錢。我之所以沒有錢,是因為 我藐視錢,而非因為我不思想。
在城市邊緣的樹林中,我捕捉到一只 蝴蝶。蝴蝶在樹枝上一動不動,像死了一 般。我想把它送人,但它死了。我用手指 彈煙灰似地把它彈落在樹下的草叢裡。落 地之前,它蘇醒了,拍打了兩下翅膀,仿 佛落花,在空氣的浮力中翻了翻花瓣。
我們一行十人沿早已存在的小路,從 山腳往上爬。我們踩著石塊,攀援著樹枝 ,吃力地爬山。途中我們沒有遇見一只野 獸。這就是自然景物了嗎?原本豺狼虎豹 出沒的山丘和叢林,現在都屬於了人。我 們除了看見自己,再看不到野獸。在野獸 與人的對峙中,最終人掠奪了野獸的權利 。到處是人造的自然,人偽造的自然。難 道我們不應對地球上聳立起的摩天大樓心 存疑慮?
那條既已存在的、積滿了黃葉的小路 ,在植物園附近。初秋樹林彌漫著午後的 光線,顯得蒼老和憂鬱。進入樹林不久, 小顧突兀地招呼蹲在矮樹叢中的一對陌生 男女。--那男的是我過去的同事。小顧 解釋道。來自山石上的細塵,裹在風中, 摩擦我們過於嬌嫩的皮膚。我們故意喧嘩 ,裝出童心未泯、肆無忌憚的樣子,在整 個爬山途中不斷褻瀆著被逐出山林的野獸 們的魂靈。
不停地拍照,不停地變換姿勢和角度 ,仿佛我們登山只為了拍照,仿佛我們熱 愛這些斑駁的樹皮、醜陋的山石和粗糙的 地貌。“越過山崗,前面就是紫霞湖了。 ”誰嘟囔了一句。我想象著紫霞湖的湖水 ,碧綠、清澈,照見天空和大山。我們蹲 在水邊,湖水也會照見我們的臉。現在, 去紫霞湖成了登山的目的之一。我從小路 邊揀起一根斷木,揮舞著,或在地面搗幾 下。
我緊隨前面的同伴,上到山腰,樹木 越來越密集。小路這時不再向上,而是漸 漸下行。透過枝葉的縫隙,我看到遠處山 下閃爍的白點,那是紫霞湖的反光。有一 陣白點消失了,因為我們改變了行走的方 向。當我們重新拐到這一方向時,白點就 又出現在枝葉之間。下山的過程中,我一 直在搜尋那些白點,直到我們到達山腳的 瓦房邊。“這裡是什麼地方?”我們問瓦 房前洗衣服的老頭。“植物園。”老頭說 。我們在山上兜了一圈,結果翻進了植物 園裡面。我們越過植物園的大門,進入了 植物園。
我曾經在南湖小區租房子,進入市區 的途中,要經過朝天宮。朝天宮,明朝在 南京建都時,作為朝廷舉行盛典前練習朝 廷禮儀的場所,也是官僚子弟襲封和文武 官員學習朝見天子的地方。現在這裡有兩 個民間市場:舊書市場和古玩市場。古玩 市場在朝天宮的院子裡,舊書市場則在院 子外面靠河的角落。我的藏書大都是從這 個舊書市場買的。這裡的舊書,相對新書 價格很便宜,最高賣到4、5元錢,一般 在2至3元。舊書攤的攤主基本是些無業 人員,有中年、青年和老年人。我為一本 書和他們還價時,他們總是說:“沒看到 嗎?這是名著!”
我的藏書全是破破爛爛的書,但都是 名著,有海明威、福克納,有《古斯泰﹒ 貝林的故事》和《春琴傳》,有車爾尼雪 夫斯基和契訶夫,有米斯特拉爾的詩集和 塞拉的《蜂房》,有《地理學詞典》和《 小兒病的診斷和治療》,有辛格、三島由 紀夫和斯坦培克,有司格特和帕特裡克﹒ 懷特,有赫胥黎的《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 》。
寄信從郵局出來,我蹬著自行車滑到 不遠的朝天宮。我沿河邊搜索書攤。在一 堆亂糟糟的書前,我停下腳步,目光落在 一本書上。庫柏的《航海家》。我想買下 它。正在我猶豫間,攤主老頭看看天色, 然後開始把一本本書放進麻袋。“我要回 家了,”他對旁邊的小伙子說。我的決定 還未明確,他已經把手伸向庫柏,緩緩將 庫柏放進麻袋。第二天、第三天、從此以 後,我在朝天宮再沒遇到那個攤主老頭, 他生病或是死了,或是別的原因,我一概 不知。
多少年前,我孓然一身,在大學校園 裡穿行。我走出校園門口,進入傍晚飢餓 的城市,進入夜間吃飽喝足的城市。我從 一戶戶人家亮著燈的窗前走過。窗戶裡的 人在吃飯、看書、打毛衣,低著頭從一個 房間隱沒,又現身另一房間的窗裡。他們 對房屋外面樹蔭中的我渾然不覺。在燈光 中,他們幹著、想著、談論著他們家裡的 事情,他們完全忽略了黑暗樹蔭中站著的 我。
我被拒絕在近在咫尺的親密氣氛之外 。那氣氛是黃色的,來自燈光。我匆匆行 走在校園附近的林蔭道上。我路過林蔭道 邊一棟二層樓房。我從樓房拐角的窗戶看 進去。一個戴眼鏡的老太伏在紅漆的方桌 上寫字。窗戶裡的燈光是黃色的,牆壁是 白色的。我停下腳步,探頭俯在窗紗上盯 著老太。我全神貫注盯著老太,老太在全 神貫注地寫字。我想這老太對我來說是一 個“別人”,而我對於這老太則不存在。 我不是老太,也不是黑夜,我是虛無。我 是在虛無中彌散的虛無。
哦,我的家。什麼時候我才會有我的 家。那時我發誓我也要有個家。我在自己 的家中忽略家之外的一切--忽略喧鬧的 城市,忽略肉欲沸騰的人群,同時無意之 中也忽略了窺視著我家窗戶的孤獨者。
我的家,現在位於漢西門大街的路邊 ,東西向。東面被高樓擋住,唯有下午才 有陽光從西邊的陽台照進來。 10月份我接 收陽光的時間是下午3點半。這時我一般 坐在電腦前。陽光爬進了門檻……爬到我 腳邊……爬上我的後背。陽光用微微的熱 量撫摸我,將刺眼的雪白的光線舖在我的 鍵盤上。而3點半之前,屋子裡陰陰的, 灰色的情緒蒙著黑頭巾,在屋子裡跳舞。 陽光一進來,就徹底趕走了它們。陽光統 治了我的房屋,使我得到清潔,使我的皮 膚更加伏貼,使身體裡的血液變得新鮮。 這是最美好的時刻,從下午3點半開始, 延續到5點。然後夜晚來臨,我打開台燈 ……
假如一天全都這樣陽光明媚,假如我 有一處新房子,假如我的房子四面用玻璃 做成,我就可以像一棵飽滿的、翠綠的青 菜,充份得到光照,吸進二氧化碳,吐出 氧氣,在凳子上長胖,長高。我就可以健 康,不受細菌的幹擾。
上午我在廚房刷牙時,聽到窗外隔壁 老頭說:“不要好事變壞事,適得其反呀 。”我輕輕推開窗戶,朝外看,隔壁老頭 在清掃門前的走廊。他說的“好事”是什 麼呢?我把牙刷在嘴裡搗了搗,心裡嘀咕 ,莫非他說自己在做好事?掃走廊也該算 個好事了,可是這怎麼會變成壞事呢?讓 人費解。他掃地的聲音“沙沙”的,很響 。他移動笤帚時,走廊裡揚起陣陣灰塵, 把他包裹。
一張俏麗的臉,轉眼又顯得很平庸。 俏麗的臉來自電視機屏幕,而平庸的臉則 和我的臉相像。我以最簡單的方式(類似 動物的方式)去愛慕那張俏麗和動人的臉 。我這樣做的後果是徒增失落和傷感。那 張俏麗的臉本是另一具人體的抽象的符號 ,我卻要真實地去靠近它。我卻要讓那符 號在我內心生根,在我的肉體中長芽。我 卻要讓那符號吞噬我,在夏天的夜晚。
我站在一座橋上。橋在湖泊的中央。 遠處是高樓的燈火,湖水和黑夜連成一片 。我穿一件很長的襯衫,襯衫的下擺拖到 膝蓋,像個印度人。我依在橋欄上,面對 一張模糊不清的臉。那臉偶爾看我,多數 時候看著茫茫黑夜。它與黑夜,由同樣的 物質組成。它們彼此交流,無限親密。
水泥橋欄粗糙的顆粒深陷我的掌心。 我對那俏麗的臉說:“哦,湖水。”臉也 說:“湖水。”我黝黑的目光穿透黑夜中 的光年,直達那張臉。臉說:“我們回去 吧。”我的身子慢慢疏遠了橋欄,但仍停 留在橋上。“那我們就回去吧,”我剛說 完,身子就猛然越過橋欄,朝湖水中栽去 ,一開始像海豚,然後像一截圓木,靜靜 躺在湖底。水流的蕭聲纏繞著我--一艘 長滿水草的沉船。
我的下沉,打攪了一群小魚的安睡。 魚兒們喧鬧著,從湖底的淤泥中飛起,倉 惶逃躥,無能地刺進黑暗的水域。慌亂中 的碰擦,增加了無謂的恐懼。我正面朝上 ,看那些高樓折射水中的燈光,像天上繁 星。久遠恬靜的景象在我心中泛濫,我手 執蒲扇,躺在散發著麥芒氣味的打谷場上 ,辨認北鬥七星的形狀。我對星星的迷惑 不解,使我心地純潔。而那俏麗的臉,卻 使我感到自己很臟。湖底的我,斷絕了對 臉的向往的我,是質朴無瑕的我。湖水刮 過我的皮膚。鄉村靜躺在城市的湖底。我 是鄉村的化身。
(1998.11.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