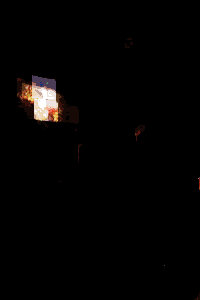
﹒金海曙﹒
鼾 聲 如 雷
今天我被一陣鼾聲操了一頓。這話說 得有點粗,但實際上我就是被它操了一頓 。鼾聲一點道理不講,一點不客氣地擠進 門來,象一大早來了一個大塊頭的修自來 水管的工人,穿著工裝褲。我在想,一開 始這個人接到通知說樓上的水管壞了,向 下滲水。正好他今天心裡不痛快,今天是 周末,他不願意一大早出門去修水管。於 是他就勉勉強強出了門。我繼續想,忽然 他發現帶來的配件也有問題,全是小號的 ,和下水道漏水的彎頭尺寸不對。水漏得 實在太厲害了,真是樣樣事情不稱心啊。 我幾乎看到,他開始的時候還在水管上裝 模作樣地敲敲打打,結果一使勁就把我摁 在床上一聲不吭操了起來。我這樣一想, 就加深了我受迫害的感覺。我是一個受害 者,這沒有問題,許多人都是受害者。我 雖然這樣想,卻並不能恢復我心情的平靜 。老頭的鼾聲正象是一根憤怒的生殖器 ,直挺挺地豎在我的頭腦裡。我無話可說 。沒有我發表意見的余地。這是沒有辦法 的事。我們每個人因時因地都會偶然地處 在被強奸的位置上。這種事情一點辦法都 沒有。本來我不會對沒有辦法的事情隨便 發表意見。既然一件事情已經沒有辦法了 、不可挽救了,那麼我們只有承認它的合 理性,只有承認它是沒有辦法的、不可挽 救的。這是一種比較正常的人生觀,起碼 我認為它是比較正常的。可是不久前發生 了一次不甚嚴重的交通事故,一輛自行車 在我的尾骨附近撞了一下子。我當時以為 沒有什麼事,不久後我發現這次偶然的小 事故讓我整個人變得相當的神經質。也可 能我原來就比較神經質,神經質的因素潛 伏著,均勻地分布在我的神經網絡裡。自 行車輪胎撞在我的尾骨上,就像我們無意 中撳下了一個開關,神經質就開始在我的 體內亂串起來。我的神經系統現在很混亂 ,植物神經、動物神經還有神經末梢都很 混亂,處於系統崩潰的前夜。
系統崩潰是從植物神經開始的。先是 失眠,接著就是亢奮、不停地亢奮。很多 平常的事情,我不明白有什麼可亢奮的, 但我就是抑制不住地亢奮起來。換一個說 法就是我變得非常敏感,極其敏感,神經 末梢很活躍。我不喜歡活躍。神經末梢一 活躍,就降低了我的忍耐力。本來我的忍 耐力還行,默默無聲,辛勤工作,現在我 的忍耐力已經很稀薄了,有點象牛奶裡面 摻了很多水,又有點象城市裡的空氣污染 。這些情況綜合起來,就使得今晚的鼾聲 變得難以容忍。
隔壁的老頭每天晚上八時四十五到九 時之間,必然地、準確地開始打鼾。我不 反對打鼾。但是有個人每天都在你隔壁準 時開始打鼾,這就對生活造成了影響。至 少這讓人有點迷惑,到底有什麼事讓他每 天在這個時候打鼾?雖然我知道這是生理 原因導致的呼吸不暢,我可以從病理學、 生物學、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打 鼾,可我還是有點迷惑不解。特別是今天 晚上的鼾聲實在是太過份了,它那樣肆無 忌憚,那樣隨隨便便、毫無章法,以致於 讓我產生了一種錯亂,除了一種被強暴的 感覺外,還有一種被劁掉的感覺。我這樣 說,就顯得我更加錯亂了。但感覺不是思 想,我允許了它的錯亂。一般來說,思想 的錯亂才是真正的錯亂,而感覺的錯亂則 是暫時的、有限度的、在思想的幹預下是 可調控的。再說,反正現在事情已經糟透 啦,反正我已經忍無可忍準備反擊啦。我 想得很清楚,可以說已經想透了。
我只是一時還沒有找到下手的地方。 老頭的鼾聲很有特點。它一開始是逐漸地 、有節奏地展開的,由低向高,然後由高 向低。不急不緩,帶有很大的欺騙性,讓 你覺得他控制得很好。讓你覺得洪水是一 點一點漲起來的,又讓你錯誤地覺得洪水 一點都沒有往上漲。這個欺騙性的過程大 概會持續十五到二十分鐘。接著會有一個 猛然的停頓。這是一個真正突如其來的停 頓,一個空白,仿佛一本情節緊張的小說 裡夾進了幾張沒有字的紙,這幾張紙是在 告訴你情節已經緊張到了無可描述的地步 。隨之就是一陣強烈的咯咯咯咯的搖門板 的聲音,把情節往高潮推動。我猜測是有 痰在他的喉嚨裡卡住了。老頭開始掙紮, 氣氛極度緊張。我是說我極度緊張,並有 一種不祥的預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 口,等這個關口跨過去了,老頭的鼾聲就 一如洪水出閘,洶湧澎湃。
現在是晚上九時半。老頭的掙紮很快 就會過去。如潮的鼾聲就要來了。我今天 不準備被迫地、靜悄悄地等待這陣無理的 鼾聲。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把我劁掉的。 我可以被劁掉,我只是說不是隨便什麼人 都能來劁一下子。一個老頭的鼾聲就把我 劁掉這個想法是不現實的。我堅定地打開 門,而恰好這時鼾聲的高潮來臨了,一個 響亮的鼻音哄然而起。我確實象被人劁了 一記,真正感受到了命運的不可抗拒和悲 劇性。鼾聲漫過我的身體,塞滿了我的房 間。它象一個勝利的宣告,看吧,我來了 。我是強大的、不可戰勝的、永遠正確的 ,你狗日的就站在那裡被劁掉算了吧。鼾 聲發出了一陣歡快的大笑,縱情的大笑, 笑得十分舒服。我在門口站了將近一分鐘 ,啼笑皆非。鼾聲是不講道理的、非理性 的、瘋狂的,那種身處其中的無能為力十 分巨大,我仿佛經歷著一場無能為力的風 暴,它一下子就把我象一張小紙條那樣吹 了起來。
我走到廳裡。廳,一套體面住宅的門 面,就是這個鼾聲的發源地。我住在我們 單位的單身宿舍裡,它是一套帶著一個小 廳的小房間。我們單位在蓋房子的時候, 把這套小房間設想成某對年青夫婦溫暖的 小窩。現在,我被安排住在這裡,住在一 對假想的年青夫婦的小窩裡。這讓單位感 到有點不合適。原來這套房間預定是兩個 人住的,現在只住了一個人,這就不合適 了。而且單位有明確的規定,為了防止年 青人亂搞男女關系,每套屋子裡必須住進 兩個以上的單身男人。這個規定有點象一 個諷刺,同目前浮躁亢奮的生活環境不相 適應。目前這個規定顯然是跟不上形勢了 ,它面臨著被淘汰的危險。但我們單位的 主要業務是對全城下水道進行管理,業務 的性質決定了規定的性質是保守的、向下 兼容的、不太靈活的。我的具體問題是單 位裡已經沒有什麼其他的單身男人了。於 是單位就安排了一個看門的老頭住進來。 就住在廳裡。老頭很和氣。剛住進來的時 候我沒注意到老頭的鼻子。現在我注意到 了,它是巨大的、醜陋的,卻有著帕瓦羅 蒂胸腔的共鳴,表現出了一種不可抗拒的 內在力量。
我凝視著這個難看的鼻子,這個鬆鬆 垮垮的鼻子上記載了一個男人卑微的毫無 意義的生活經歷。我情不自禁地感到疑惑 。就是這樣一個醜陋的東西想要把我劁掉 嗎?這樣一個東西就簡單地把我操了一頓 嗎?在凝視中,我覺得自己變得有點虛脫 ,無論在體質上還是精神上我都有點虛脫 。我知道在這樣的場合下虛脫是很丟人的 。被一個難看的鼻子就搞得虛脫了?沒有 發生什麼實際的事情嘛,為什麼就輕而易 舉地虛脫起來?日子真是沒法過下去了。 我希望自己好好地過日子,我希望建立一 個幸福的家庭,床上躺著一個勻稱的和氣 的太太,而不是一個什麼看門的老頭。
這些胡思亂想讓我變得很輕,我很快 就覺得自己變成了一股煙霧飄了起來,從 窗口冒出去。我越飛越高,飄到了一定的 高度後,煙霧團聚起來成了一只氣球。不 由自主的力量把我托起來送走。我覺得自 己終於浮到了鼾聲的上面,我可以在空中 凝視這個鼾聲如雷的老頭,凝視我屋子亮 著燈的窗口,凝視這個夜晚覆蓋的城市。 它象一只巨大的永遠不會開走的船,停泊 在黑暗裡,卻帶著一副隨時都要離我遠去 的神氣。我越過了無數根電線、眾多的高 樓,它們有些亮著燈有些沒亮。人們住在 各自的匣子裡,關上了幸福的小門,關上 了小門外的鐵柵欄。門上安裝了各種各樣 的保險設備,物理的電子的激光的數字的 ,幸福被關在裡面萬無一失。只有他們自 己才能把幸福打開。沒有人會想到有只被 鼾聲托起來的氣球此刻正從他們的窗外經 過。我飄過一扇亮著燈的窗戶時看到,一 個丈夫正把自己的腳浸在腳盆裡燙腳,同 時閱讀著一本《家庭與健康》。他的妻子 正在安排兒子睡覺。我要巧克力,兒子說 。不行,妻子嚴肅地說,睡覺前不能吃巧 克力,睡覺前吃了巧克力就會長不大了。 此刻丈夫則平靜地把雜志翻過了一頁。我 不知道他正在看什麼欄目,他看得津津有 味。膽囊炎、艾滋病和保持家庭中愛情的 秘訣都讓他津津有味。
這個場面在一個鼾聲如雷的晚上十分 無聊又感人至深。我很想停下來看一看, 但是我控制不住風的方向。講得抒情一點 ,那麼就是我在一陣鼾聲中無可奈何地飄 了起來。飄啊,飄啊,飄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