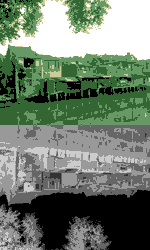
﹒楚 塵﹒
路 過 黃 村
……就這樣我們到處晃盪, 一個冒牌者和一個僅僅的一半:既沒有達 到存在,也沒有成為演員。
--引自裡爾克《馬爾特札 記》
一
黃村是一個地名。雖然我們可以在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中國地圖上找出若
幹個與此同名的地方來,但我心裡其實很
清楚,我去過的這個叫黃村的地方大概只
有一個,而且也只有這麼一個地方,跟我
的一位叫李德成的朋友能夠扯上關系。李
德成是我在大學期間唯一的一位不是在本
校認識的朋友,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正在南京的一個叫奧傑的酒吧裡拿著一
把吉它自彈自唱,他的聲音有點渾厚,但
不夠圓潤,大概是唱得不多的緣故,他的
演唱遠不如他彈奏的指法那麼嫻熟。當時,
李德成的身邊還站著幾個黑人,他們手中
都拿著一把吉它,李德成後來告訴我,他
正準備與他們組建一個樂隊,這是組建前
的一次友情演出。幾個黑人朋友來自沙特
阿拉伯和阿聯酋,他們在南京大學留學,
學習古代文學,李德成當時與他們一起討
論給樂隊取名的時候,他們一致想到了“
唐朝”,可惜,好事多磨,由於種種原因,
他們組建樂隊的事後來不了了之。幾年之
後,中國的北京也出現了一支叫“唐朝”的
樂隊,我知道的時候,心裡頗有些不是滋
味,我想,要是當時李德成他們如願的話,
恐怕幾年之後的這個叫“唐朝”的樂隊只
能另改名稱了。我之所以對此事感到有些
遺憾,是因為組建樂隊的事如果能夠實現
的話,我大概也是“唐朝”樂隊的一員了。
不過,這倒沒有影響我們以後的交往,我
後來經常背著在大學裡靠省吃儉用攢錢買
下來的吉它,去與他們交流,演奏我們自
己作詞譜曲的歌。黑人朋友後來臨走的時
候,我們還一起在北園的緊挨教學樓的那
個草坪上搞了一次小型的告別演出,我就
是在那一天認識李尤的。那是六月的一個
晚上,原計劃本來是在我們幾個人當中搞
一次自娛自樂的演唱,由於吸引了更多的
北園的朋友們,這次告別的聚會倒成了一
次不大不小的演唱會,我記得後來草坪上
的同學越聚越多,那個場面到現在仍讓我
激動不已,我們唱了很多歌,到最後似乎
整個兒成了一個大合唱,那些圍攏過來的
校友們情不自禁地與我們一起唱起來。後
來有很多校友碰到我的時候,仍對那一晚
記憶猶新,都向我聲稱那是他們大學期間
在北園度過的一個最美好的夜晚。
過了一個月,黑人朋友薩姆鬆等人和
李德成先後離校,我們再也沒有機會見面。
想起他們的時候,我就會懷念那次告別的
聚會。雖然黑人朋友與我分手的時候一再
囑咐我以後有機會去他們的國家聚聚,但
到現在我仍感希望渺茫,也不知要等到什
麼時候才能碰面。見不到黑人朋友倒在常
理之中,可是畢業以後,我與李德成見面
的機會也一直是一個零,我時常跟李尤感
嘆自己身不由已,按理說,如果真正想見
朋友的話,還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問題
是我總是抽不出時間來,總是把希望寄托
在下一次。我記得我和李德成最後一次見
面的時候是在那年七月底,當時我和李尤
已談了一個月的戀愛。我們分手之前在儒
林酒家吃了一頓飯,在座的有我與李尤,
還有李德成與他的女朋友張小雅,張小雅
是商院的,念大二。李德成把他的那把吉
它送給了我,他說留給我做個紀念,而且
他認為把它帶回黃村也不方便,行李已經
夠多的了。李德成和張小雅與我們後來在
漢口路分了手,我記得他當時跟我與李尤
揮手時說了一句:“希望你們以後有機會
去黃村找我。”我到現在仍記得李德成向
我們揮手告別的姿勢和表情。
遺憾的是,雖然黃村這個地名對我來
說耳熟目詳,李德成在校時不知跟我說過
它多少次,但是至今我也搞不清黃村到底
在一個什麼地方。我想,我總有一天會弄
清楚的。
二
這是一九八七年夏天的事情。時間
又過了八年。八年的時間足夠使人忘掉很
多從前的事情。大學畢業後我感覺自己再
也沒有輕鬆過,為了努力地活下去並且盡
量活得快活一些,我先是被一些單位選擇,
然後自己又不停地選擇其它單位,我一直
想找一個能夠使我遊刃有余地大幹一番的
地方。然而,遺憾的是,盡管我南來北往地
去過許多城市,在那些城市我留下過一些
痕跡,但我總是未能如願以償。至今我仍
在馬不停蹄地尋找著,我頑固得還沒有喪
失掉希望。
在大學畢業後最初兩年的時光裡,我
多少還有一些閑情逸致去撥弄撥弄自己的
吉它,李德成的那把吉它我也一直放在身
邊,當時在單位,像我這樣擁有兩把吉它
的年輕大學生絕對是一個有頭有面的人物,
我在單位同齡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很高,
那幫朋友居然很少有懂音樂的;由於他們
對音樂的無知,我順理成章地令他們感到
敬佩,當時的團委還打過我的主意,單位
的頭兒認為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可能更利於
做好年輕人的工作,他找我談話想讓我去
幹團委書記。當時,我對那個單位有些失
望,一直在暗暗地等待機會逃走,所以我
回絕了那個頭兒的好意。兩年之後,我再
也沒有機會去彈奏我的吉它,我終於跳了
糟。由於經常搬家,那兩把吉它就慢慢地
被弄丟了,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它們是在什
麼時候被我遺棄的。
這八年的時間除了更換工作,就是與
李尤折騰愛情,李尤大學畢業後並沒有與
我分在同一個城市,有一段時間,為了我
們的愛情,我與她來來去去花了不少冤枉
錢。我們離了又合,合了又分,到最後彼此
累得直想放棄這令人勞筋傷骨的愛情。也
不知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反正後來李尤也
來到了南京,我們終於又走到了一起。
我們現在已經同居兩年多了,像一對
小夫妻那樣在南京生活,只是至今還沒有
領結婚証。在下雨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
麼總是在下雨的時候),我和李尤都不想
出門,兩個人只好呆呆地在房間對坐著,
總是忍不住在雨聲中感嘆時光有如白駒過
隙。我們倆似乎已漸漸地遠離了從前的生
活。我隱隱地感到這是一個無法拒絕的事
實,時光催人老啊,我已經看到了李尤眼
角上的魚尾紋,八年前,她是多麼年輕,青
春,美麗;想起她以後還會老下去的模樣,
我總是在心裡感到無奈和傷感。
吉它…大學時光…李德成……。我幾乎再
也難以想象它們曾經屬於過我,曾經與我
有過關系。八年的時間,我幾乎已經忘記
了李德成,還有那個與他有所關聯的叫黃
村的地方。如果不是由於一次偶然,他和
那個叫黃村的地方大概再也不會從我的記
憶深處浮現出來了。
三
有時候,我不能不感嘆生活的確是
如此荒誕,充滿了偶然與必然的扯不清的
關聯,我萬萬沒有料到,我在八年以後的
一天,居然稀裡糊塗地路過一次黃村,並
且在那個叫黃村的地方尋找我在大學時的
好友李德成。
好了,我不想再拐什麼彎了,還是讓我
們去黃村看看吧。我要讓你們知道,那些
在黃村發生的與我或者與李德成有關的事
情,為什麼是那麼令我莫名其妙,那些令
我焦頭爛額的事情到現在仍讓我心有余悸
。
因為我沒有想要去黃村,所以我覺得
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我是如何偶然路過黃村
的:
那也許是一個與昨天和未來沒有什麼
兩樣的一天。那天傍晚下班後,我沒有像
以前那樣買好菜後等李尤回來做飯。我回
家後把公文包放在桌上,點燃了一支煙,
我坐了下來,突然感到自己再也不想動了。
我陷入到沉思之中,把頭和身子埋在沙發
裡一口一口悶悶地抽煙。我模模糊糊感到
自己忽然對此刻面對的生活有一種厭倦之
情,房間裡的氣息熟悉得讓我憋悶,我在
心裡不禁對自己與李尤這幾年來的生活感
到懷疑--這難道就是我們當初追求的生
活嗎?我越想越提不起精神,我感到我與
李尤之間的生活已經出現了一道罅隙,但
毛病到底顯現在哪裡?我尚不能明細地察
覺。我也相信不久的將來這種狀態會慢慢
地有所改善或者漸趨更好(但只有鬼知道
什麼時候!);問題是現實是一回事,未來
又是一回事,麻煩的事情在此時很容易在
我身上出現--我這個人向來對一切沒有
足夠的耐性。所以,在那一刻,當一種絕望
的情緒籠罩我的時候,我一剎那間感到自
己有點心灰意冷,我沒有讓自己去菜場,
雖然我的肚子已經餓了,我感到自己根本
不想動彈。我在那裡吞雲吐霧,破天荒的。
當我聽到李尤把她的鑰匙插向鎖孔的時候,
我發現黃昏已經過去,夜晚早已降臨,我
手中煙頭的微光把房間裡的黑暗照得更黑。
李尤把門推進來的時候,大概從走廊上透
出的微光中看出了一個笨拙的身影,她嚇
得一聲驚叫,慌忙中拉開電燈(她把開關
線拽斷了),她從來沒有看到我在這樣的
時刻獨自一人呆在房間裡,她沒有料到我
會這樣。她哭了。她看上去顯得很累,單位
離家很遠,每天早出晚歸地趕路是很辛苦
的。
我一向受不了女人的哭聲,我只要一
聽到她們的哭聲,心裡就會緊張得發慌。
我開始心煩意亂,我感到房間裡突然生長
著一種與我對抗的東西,我根本無法招架。
李尤還在輕輕地抽泣著,仿佛受到無窮的
委屈,她把自己擺在房間的正中央,她的
包還掛在肩上,身體在抽泣中微微地搖晃
著。我再也不能與她這樣對峙下去了,我
難受極了。我突然在房間裡吼了聲:“我再
也不希望這樣生活了,我已經煩透了!”我
的聲音使李尤嚇了一跳,皮包從她的肩上
捷速地滑了下來。她大概沒有料到我會這
樣。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我感到自己快
要瘋了。我開始在房間裡砸東西,那些平
時靠我們省吃儉用買下來的東西一件一件
地被我拋向了地面,頓時,房間裡充滿了
各種怪音,連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刺耳。李
尤被我的行為驚呆了,她開始放聲號啕大
哭,她很快地過來抱住我的胳膊,拚命想
擋住我的雙手,她沒有說一句話,她只是
想使我停止動作。我砸了一陣,慢慢地沒
有了力氣,就停了下來。這時候,我突然聽
不到李尤的哭聲了,我抬起頭看她,但見
她眼角上的淚水還在不停地往下淌。不知
為什麼,我感到自己的鼻子也微微地有些
酸澀,我在那一瞬間感到有些傷心。我把
視線伸向了窗外,外面已是萬家燈火,一
些人家已經關門睡覺了,而我和李尤尚無
一滴水一粒米下肚。然而,我們都不想吃
任何東西。
也不知過了多久,李尤已經在收拾這
個被我破壞得亂七八糟的房間,那些玻璃
的碎片和被我搞壞的一些物件,在李尤的
清理中,發出了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聲響,
我不禁皺緊了眉頭。我們一起精疲力竭地
坐在房間裡,呆呆地望著房間那些少了東
西的地方或者互望著對方。我看見李尤右
手的大拇指頭還在流血,那可能是剛才劃
破的,可她還渾然不覺。我不禁心頭一陣
緊縮,一絲淡淡的感傷再次油然而生。
我說:“李尤,對不起,我不是故意這
樣的。”
李尤聽了我的話,竟然忍不住又流下
淚來,身體劇烈地顫抖著。她說:“你以為
我不感到累嗎?只是我說不出口。我不知
道我們怎麼了。這麼多年來,為什麼沒有
像當初希望的那樣?”
我無言以對。過了一會才說出一句:“
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李尤有些警覺地問我:“那麼,我們怎
樣才能下去呢?”
我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已經是深夜了。我們仍沒有吃什麼東
西,我們不感到飢餓,飢餓感仿佛早已被
我們糟糕的心情抽空了。我和李尤從來沒
有像今天這樣如此尷尬地坐在自己的房子
裡,莫名的無聊和空洞。
“你真的想這麼做嗎?”李尤又開始流
淚了。
“我沒有辦法。”我說。
“我們走到今天很不容易。難道你不想
珍惜嗎?我們還可以好好調整的。”李尤
懇切地望著我。我不能看李尤的眼睛,看
了我的心就軟了下來。我怎麼跟她說呢。
我低下頭,一聲不吭地想把自己凌亂的思
緒好好理清。李尤從廚房裡拿了一點吃的
東西,我這才覺得肚子空空的。
“李尤,我們出去一趟吧。”
“到哪裡?”
“外面。”
“什麼時候?”
“現在!”
……
四
就這樣在那天吵架的當天夜裡,大
概快凌晨三點了吧,我和李尤匆匆地收拾
了行裝,然後趕往火車站。當時,我們都有
一種盡快逃離南京的沖動。我們隨便地爬
上了一列火車,我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也不知道自己搭乘的這列火車駛往何處。
車廂裡的燈光有些暗淡,人們已經安然入
睡,誰還會在意這兩個狼狽不堪的年輕人
呢,上半夜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情,全世
界大概不會有第三個人知道了。幸好是夏
天,臥舖車廂還有座,乘務員給我們辦完
手續後,我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列
車當當地運行著,車窗外一片漆黑,
一屁股坐下來,我才感到自己已經很累,
李尤也是哈欠連天。我們躺下來,很快進
入了夢鄉。
這一覺睡得真是太沉了,等我醒來的
時候已是第二天黃昏,我睜開眼睛,好像
還沒有睡夠,李尤仍在夢裡。窗外的風景
太令我陌生了,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這列火
車要把我們帶向何處,我迷迷糊糊地倚在
那裡,我想我們總得要選擇一個地方下車,
等李尤醒來後再商量吧。我決定再躺一會
兒,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在蒙朧中忽
然聽到列車播音員的聲音響在耳邊:“旅
客們請注意了,前方到站--黃村,請需要
下車的旅客提前做好準備。”我吃了一驚,
從上舖上跳了下來,搖了搖頭,以為我聽
錯了,但播音員很快又把剛才的聲音重復
了一遍。黃村?黃村!我的記憶頓時好像翻
滾起來,這難道是李德成說的那個黃村?
這麼說,我們可以下車去看看他了?我有
些猶疑,但還是趕緊把李尤弄醒,我對她
說,快起來吧,快到黃村了,我們下車去看
看李德成吧。黃村?李尤聽了我的話,非常
驚訝,她大概一下子還沒有反應過來:“黃
村?什麼黃村?”她納悶地問我。我說怎麼
黃村你都不知道啦,它是李德成的家鄉啊,
我們正好可以去看看他了。李尤一下子回
過神來,她甚至露出一點興奮的表情來,
不過,她很快地又問了我一句:“你能肯定
這個黃村就是李德成說的那個黃村嗎?”
我一下子愣住了,是啊,我怎麼能夠肯定
呢?我想了想,對李尤說,不管怎麼樣,我
們還是先下車吧,反正我們總要下車的。
李尤同意了。
黃村很快就到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