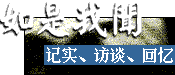﹒王一樑﹒
八十年代的青 春:人和詩
◆我可以放棄詩歌寫作(孟浪)
從人的熱情洋溢程度上講,他們同
樣都是把嶄新的感覺和思想帶給了我們,
在這裡,天才和革命者的確沒有任何區別。
因為這種界限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真正的
藝術家必然是一個革命者,革命者必然是
一切腐朽事物的顛覆者,因此,當1986
春天,這塊土地上慣於滋生出來的古老的
瘟疫,突然降臨到默默身上的時候,朋友
們沒有驚訝得目瞪口呆。
其實,只要我們的政治格局沒有變化,
國家總是大於社會,政治總是大於藝術,
那麼,默默的遭遇事實上也會是我們這裡
的每個人遲早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命運。而
這場瘟疫之所以最先光顧了默默,因為在
當時,默默是我們這群人中,一個成熟得
最早的詩人。
而朋友當中,一個最早從行動上明確
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則是孟浪。
1984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和默
默正坐在他的違章建築物中聊天,突然,
從窗洞裡鑽進來了(這間房子的結構就是
這樣的,窗子當門使用)一個眉清目秀、
穿著一件汗衫的人。他自我介紹說,他叫
孟浪。
哦,孟浪!我們差不多是一起喊了出來。
作為一個強者詩人,這個名字我們早就聽
說過了,而這些日子裡,默默和我也正在
四處尋找著他。
從孟浪口中聽到的相信,的確令人興
奮。全國到處有年輕人聚集在一處從事藝
術、寫作活動。他在外地已經跑了半年多,
不僅見到了許多正活躍著的詩人,而且還
見到了食指,可惜的是,他是在一家精神
病院中見到這位新中國詩歌聖徒的。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天才的寫作常常
伴隨著不幸。”
那麼,就讓我們這一代人去親手把這
個不幸的寫作者故事結束吧,讓我們現在
就去從事對整個社會的啟蒙:藝術無罪,
藝術永遠不會是災難的同義詞,就算藝術
的力量足以毀掉一個國家,可藝術還是人
類最好、最可靠的朋友。藝術獨立,這是任
何人、任何政治權力都無法奪去的生存權
利,柏拉圖的理想國無權這樣做,斯大林
的極權社會更沒有這樣做的權利。藝術家
自有藝術家的尊嚴,這種尊嚴遠比國家的
尊嚴更加值得尊重,因為正是他們,表達
了一個民族的最高聲音。
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動核的念頭
手指按著自己上衣的某一顆鈕扣
那個人對面前赤裸裸的果實
動核的念頭
“如果需要,我可以放棄詩歌寫作,
去做一個藝術活動家。”孟浪微笑著說。八
年之後,“我們這裡的每一個人,遲早都有
可能遭遇到的命運”降臨到了孟浪的身上。
不幸的寫作者的故事並沒有在這塊古
老的土地上結束。
那個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他在一片空白裡
上衣象一束枯萎的花朵
在他無力的臂彎裡
--摘自孟浪《那個
人站在一個國家的對面》
〔附一〕
天空中的飛鳥﹒田野上的百合花
--默默、孟浪印象記
創作《城市的孩子》、《我們的自白》
的時候,也正是默默最渴望去遠方流浪的
日子。
當時,默默的作品,其風格類似編年史。
他象說話一樣,象講故事一樣地寫作。
在1983年的寫作札記上,他寫出了“桃
花源裡正走著一個偵探”、“沒有嘴唇的歌
女在歌唱”、“斷臂的維納斯拎起了一挺馬
克辛機關槍”。在這些斷章裡,講故事的才
能,優雅的幽默感以及對理念世界中秩序
的感覺力,開始放射異彩。
我們這一代人躬逢盛世。在那些日子
裡,默默本人的生活方式也象古老的行吟
詩人一樣。他在這座城市裡到處為家,崇
拜遙遠,尋找人群,誦頌他的作品。
懷著天真的執拗,認為這個世界需要
啟蒙,人性需要新的解放。這樣,在1984
年,便有了《城市的孩子》、《我們的自白》
這兩部傑作。那時,他才二十歲。
作為一個早熟的天才,默默的文學之
夢是要將整個世界和人生都寫進作品之中,
這是特別讓人感動的地方。如果一個藝術
家正被這種意志所震撼所控制,那麼在這
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不可以去寫呢?哪怕是
司空見慣的東西,哪怕是已被一再重復的
古老思想,再寫一次又有什麼關系?只要
寫作帶來了啟蒙,只要寫作帶來了進一步
的自由和解放!
生活在這樣一個大無畏的世界裡的藝
術家,應該是幸福的。因為,它必然要求作
者將他的一生本身作為一部作品去塑造,
從而真正實現其作為人的全面自由。然而,
更多的地方卻有可能只是失敗,因為,象
這樣的寫作同時也必然會要求作者與那些
為文學而文學的觀念徹底決裂,尤其是在
中國文化進入了消費時期,越來越具有第
三世界性的時候。
命運看來注定就是失敗,必與寂寞和
勇氣為伍,卻也因此為我們帶來了人性高
原上的一派風光。
在這一派風光裡,就有一群人的流浪;
一群任何名字都沒有留下的少年英雄,他
們最後在大象的遺像裡找到了最終的歸宿。
總歸會有一天會有人理解我們
理解我們為什麼把大象的臉裝進黑
框子裡
總歸有一天會有人相信我們
相信我們就是她死去的哥哥
她沖進編鐘裡
向那時的世界發出摹仿我們的哭聲
她仰臉問媽媽我們的名字
媽媽將突然放聲大哭
--摘自《我們的自
白》
田野上的百合花無力選擇自己的生
存空間,她只能在山嶺和田野上滿山遍野
地盛開,這是其生存性的致命悲劇。如果
一旦離開了泥土,成為了擺設,那麼也就
只能是異彩沉淪。然而,飛鳥呢?
認識孟浪,是在84年的一個夏天。他
剛結束了半年外地的漫遊生活,他帶來的
消息是令人振奮的,全國各地這一代詩人
正在迅速崛起。象我們一樣,整個世界都
渴望新的童話、新的神話。這個世界正需
要更多的新實驗,更加大膽的行動。
心靈既然燃燒了起來,那麼便不會熄
滅。幾個月後,孟浪繼續從這座城市裡消
失了。那時候,他微笑著,說他可以放棄詩
歌寫作;只要需要,他寧願去成為一個藝
術活動家。就象蘭波能夠放棄詩歌,托爾
斯泰放棄寫作,維特根斯坦放棄哲學。
“如果我還不是一個人,我又怎麼能夠
成為哲學家呢?”(維特根斯坦語)
當整個世界和人生都不值得去體驗了,
寫作還會有什麼意義呢?如果行動比寫作
更加壯美,那麼,為何不立即去行動?
飛鳥也許飛得太高,飛往的地方太多,
因此,他必須格外注意路標的誘惑。1984
年,孟浪警告人們:“必須警惕形式的誘惑
”。但是,孟浪自己最後卻建立起了一種
詩歌形式。
本來嘛,飛行著的飛鳥,其飛行的形式
本身就在於創造著一種飛行的美。在它掠
過名山大川的時候,旨在嘗試飛翔那些雲
層不到的時候;在陽光最燦爛的地方,或
者空氣最稀薄的地方,飛鳥便敏捷地變換
著姿勢。
大地上的觀察者也許弄不明白,為什
麼飛鳥盡管千姿百態,卻仍然擺脫不了它
的流線簡單。這時候,也只有最懂行的觀
察者才會真正地告訴你:飛鳥的本性其實
追求的仍然是飛得最高,而直線就是飛得
最快的道路。
默默與孟浪,一個揮霍文字如土,一個
惜墨如金。但是,同樣寫下了他們的青春
故事。作為一個啟蒙者、解放者的形象,這
一部值得我們去寫的編年史裡,留下了不
可磨滅的腳印。(1989年)
◆既然相聚了,就會有一番轟轟烈烈的
事業(劉漫流)
暑熱難熬的白天終於結束,躺在籐
椅上昏睡了整個下午的我們醒來。從長江
入海口處吹來的晚風,使我們重又變得精
神抖擻。劉漫流站起來,用手指著籐椅,
張開嘴,朝我笑著說:“這兩張籐椅其實就
是你和我。那張黑一些的是你,白一些的
是我,一陰一陽。《易經》上說,一陰一陽
謂之道,我們其實是互補的。”
1984年我的學生時代結束了,有意味
的巧合在我的命運中再次扮演起了任何東
西都無法替代的角色。
當我和劉漫流在卡欣家裡第三次巧遇
的時候,我們便決定另找一個地方,一起
去酒館喝酒。
面對這幾個月裡接二連三地發生的巧
遇--他和我,一個去了卡欣家裡三次,另
一個去了四次,可偏偏就三次相互遇上--
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都猜想這裡面或許
就存在著一個類似斯芬克斯之謎的東西。
上海的亞文化到了1985年,該遇見的
人大都相遇了。
“既然相聚了,就會有一番轟轟烈烈的
事業”。這在當時的朋友們的心中已變成
一種非常普遍、強烈的預感和心願。
這樣,到了1986年的夏天,當劉漫流
在密山新村有了兩間空房子,聽到他邀請
我和他一起搬去同住的消息時,我也就立
刻想到了這個斯芬克斯之謎。
那時候,我已失去工作,正可以象一個
流浪漢一樣在這個世界上到處住來住去呢。
劉漫流是詩人、學者,還是朋友之中的
一個類似蘇格拉底式的談話哲學家。與他
談話無疑就象是在經歷一次神奇的催眠術。
太陽在照耀著,熱浪灼烤著新村的水
泥建築物。日子在一天天地過去,一天,學
識淵博的劉漫流翻開了一本厚厚的書,指
著上面的字這樣對我說道:“阿修羅居於
海上,與諸天鬥法。只要發出an音,諸天
便不鬥自敗。由此可見,阿修羅實際上是
一個藝術家。”
《阿修羅家族》是我在85年底根據三
句格言創作出的一篇寓言小說:“天下越
亂越好,反潮流總是對的,老子就是不信
邪。”那時候,我除了記一些思想片斷之
外,什麼都不寫,《阿修羅家族》實際上就
是當時我唯一的一篇可以算得上是藝術類
的文章。
而我的這群朋友卻都是詩人。
於是,我懂得他的意思了,因為在那些
日子裡,劉漫流正把他自己以及默默、孟
浪等朋友們的詩歌創作活動稱為“海上詩
群”。而創立一種“流派”和“主義”,也正
是我青春年代最大的夢想。
那麼,我的青春、我的文學生涯,我的
名字是否能夠和這些朋友們聯系在一起呢?
在往後漫長的人生旅程中,我們是否始終
都能夠相濡以沫、榮辱與共呢?
現在,既然一種“虛構的產物”竟然還
有一種“歷史的確証”--“阿修羅居於海
上”,這種巧合的發生使我確實應該好好
想一想未來的道路了。
那一天感覺起初象平常一樣
白天也沒有出現任何奇異的跡象
夜晚來臨了
靈魂總是伴隨著夜晚到來
我們談話時,他保持沉默
而當我們沉默時,他說出了第一句
話
正如歌中唱道
“我記住了他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我們將記住他們說過的每一句話
--摘自劉漫流《通
靈之夜》
〔附二〕
密山的一天
| 阿修羅拯救人的方式,就是什麼也
不做;於是,他做了一件頂頂無用的事情。
--題記 |
阿修羅小時候常常對人說:不要講,
不要講。
青年阿修羅常常用眼睛瞪著人,沉默
不言。晚年阿修羅才逐漸領悟到了沉默對
於他人拯救的道理。
但當阿弟問起阿修羅什麼是沉默時,
阿修羅搖著頭說這是思考的前提,說出來
就不是沉默了。
A:阿修羅的奇跡
| 眼睛是看到的東西,耳朵是聽到的
東西,鼻子是聞到的東西。阿修羅是不聽,
不看,不聞,人們以為這就是沉默的阿修
羅的狀態。 於是,阿修羅離開了這個世界。 --阿修羅與世界 |
這時候,阿修羅摳著腳丫,談論痛
痒辨別之艱難,悲喜交加,從他坐著的椅
子上偏過臉來望著阿弟說:“痛或痒才是
唯一的人的感覺。牛津學派說的都是不關
痛痒,不痛不痒的事情。”
阿弟聽到這裡,內心一陣激動,他關心
語義學問題已經有數年了。他這才明白過
來,休息是需要的,阿修羅確實並不需要
睡眠。
阿弟在大白天也連續性地看見夢。
B:阿修羅家族的生活方式
| 阿修羅說:星期三、星期四通宵寫
作。 本世紀人太懶惰,無法完成巨作。人們 必須付出雙倍的時間工作,必須有一天夜 晚不熄燈。 這時候,他們說你的腦子壞了。 --日記 |
京不特已經將一只香蕉吃完了,他
用洗腳布抹了抹嘴,接著又拿了一只蘋果。
他說今天不是日子。
聽見這句話,阿弟一點思路也沒有了。
語言也開始露出它猙獰的牙齒。
我們要用思想踐踏語言。
這時候,天大亮了。
京不特躺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這一
夜,他們枕一個枕頭,蓋一床被子,據說那
條洗腳布是女人用過了送來的。不流說,
明天,他要好好洗一洗了。
京不特還沒有醒來,他在不停地夢囈
著。
馮阿修羅說,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
刷刷牙。
!!!!!!!! !!打倒衣服!! !!!!!!!!阿修羅每次從海邊回來,心裡完全想 著的就是京不特的腳是否幹淨。
京不特高呼完口號之後,就醒來。他堅 決要讓世界看見他已經洗過澡了。
阿修羅想到,已經到了應該堅決地不 見外人的時候了。
C:阿修羅如是說奇跡
| 過去的宗教,就是鄉下人讀了點書。
--日記 |
阿修羅的眼睛,看人非人,非人是
人。阿修羅從來都是兩句話一起說的。對
他說過的話,阿修羅應負全部責任。只有
人才不配為自己負責,請看看,他們什麼
時候負過責。
阿修羅說:“好久沒有聽見人說賊是賊
骨頭了。”
阿修羅搖著椅子,抬起右腿,想到時代
的變遷,於是仰天大笑起來。
阿弟為大師的喜悅感到內心奔放。幾
天後,阿修羅以如此的評價作為酬答:阿
弟不聲不響,最近常在我面前,走來走去,
有苗頭呵。(1987年)
■